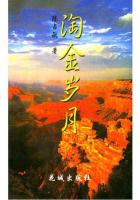34.又进活佛家
局势不断发生微妙的变化,马家人也没有闲着,到处游说:“共产党要来了,他们实行的是共产共妻。”
老百姓对这些宣传无动于衷,充耳不闻。马步芳的酷政使人们生活在人间地狱,这种煎熬已经到了极限,难道还有比这更黑暗的地狱吗?残酷的剥削和血腥的镇压早把人们铸成了钢,对这些煽动没有表现出惊惶,也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只是静静观望等待。
这年秋天来得很迟,空气里充满暖暖的气息,一切显得平和、安详,平时蛮横的警察不上街搜刮钱财了,夜里很少看见有他们私闯民宅,扰民的行为收敛了许多。他们走在街上像丧家的狗,曾经那么盛气凌人傲慢的神态大打折扣了,高人一等的优越姿态没有了,倒像是白天出游的老鼠,萎萎缩缩,老百姓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大家见面互相说的话就是:“他们快完蛋了!”
常年在大户人家打工的阿妈经常带回来一些路途新闻,她告诉阿爸:
“马家军的下级军官起内讧,专员公署后的那座碉楼里的人跟共党的三个特派员来往密切。像兄弟一样出出进进在一块。”
父亲提醒阿妈:
“女人的缺点就是管不住那张嘴,少说为好。”
阿妈反讥说:
“是啊,男人的优点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事情的轻重,一派胡言语后,祸从口出。惹火烧身,变成了现在的‘扎劳’(堕为俗人)。”
父亲一下沉默不语,噤若寒蝉。我知道,这是说到父亲的痛楚,变成俗人是他一生的隐痛,这话就像是往他心上戳了一刀一样。
学校从今天开始宣布不举行升旗仪式,学生们欢呼雀跃,故意对着刘英的背影喊叫:
“嗷!你们完蛋了!嗷!你们的人快滚蛋!”
王权挥舞着拳头也在高声喊,有挑衅之意,只是这时的刘英像个聋子傻瓜。直愣愣往前走,不敢回身,王权觉得挑衅没有结果,又对大家说:
“昔日他是一条多凶的恶狗,现在他变成了温顺的绵羊,反而让人不习惯。原来他是个懦夫,真想揍他。”
大家望着刘英的背影蹩进了办公室。
学校也暂时放了假。
昂旺活佛派人来接父亲,我也一同去了。
一进昂旺活佛的庄园,扑面而来的是桃红色一片的“张大人”肆意开放,“张大人”是这波斯菊的名字,内地有的地方把这花又叫芫荽梅。
原来,这张大人是指清朝末年驻藏大臣张荫棠,是他把芫荽梅带进拉萨种植,再由商队传播到康巴,康巴人到现在还把此花称作“张大人”。
这次除了见到他家的那个活佛大儿子以外,没看见小儿子生格和那个小尼姑,庄园里显得冷清。
我从父亲和活佛的谈论中,才知道小尼姑名字叫卓玛,比我大几岁。只因她从小体弱多病,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父母娇生了她,可不惯养她。由于周围和家庭环境的影响,自幼就浸淫在浓浓的佛教氛围中,从小跟母亲习经。就在家里削发为尼,两年前有远见的昂旺活佛让女儿还俗了。他认为以后的社会。讲求的是人人劳动才有饭吃,不劳而获的现象慢慢会被取缔的,社会将会来一次大变革,几千年来的规矩会打破,他认为自食其力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把女儿寄养在部落里最穷的属民家里,起初她阿妈不忍心也不赞同这个决定。
昂旺活佛劝解说:
“你现在让她吃苦,意味着将来享福。现在让她受点委屈,以后就是应付生活的能手,这是让她锻炼意志,学习生活技能的机会,现在女儿衣食无忧,可谁能保证你我不在世了,女儿还能过无忧无虑的生活。世道会如何变,难可预料。既是留有万贯家产,也会坐吃山空。”
她妈妈觉得这番话有理,没再阻拦。
其实,昂旺活佛已经预料到儿女们今后所处的时代环境。
寄养的那家穷得连糌粑吃不起,管家听说后要去送吃的,被活佛制止了。卓玛实在受不了,几次带话要回家,她爸爸没有答应。
一次,也就是卓玛离家三个月后,她被那家的女主人送回来了,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她阿妈看她这幅模样出现在面前,一把把女儿搂在怀里就哭。女儿的委屈就是母亲的伤痛,母女深情就在搂抱的哭声里宣泄。
昂旺活佛只是答应擅自跑回家的女儿在家吃顿饭马上回去。当然管家和阿妈给她俩招待了一顿丰盛的饭。吃完后由管家把她们送出了庄园,并告诉说:
“仁波切不召唤你回来,千万别擅自跑回来。”
并交给卓玛一个包袱说:
“这是你母亲给你的一个包袱,里面有贴身换的衬衣和商队从印度带过来的大英帝国的糖果,你母亲在屋里伤心落泪,她不忍心出来送你,小姐,多体谅你父母的一片苦心吧!”
老管家摆摆手示意她们走。这时候已经到了黄昏,被寄养的那家女主人满脸狐疑。她一生不是这次机会,进不了百户庄园,她心里想:富人家应有尽有,不让女儿好好享福,偏让她过填不饱肚子的日子,穷人和富人对子女的态度都不一样,狠心的富人,石头一样冰冷的心肠。她怜悯起身边这个小姑娘,善良的她心里暗暗想,我一定疼爱她胜过她的父母。
她们连夜赶路,管家还是派家丁护送到目的地。
从此,卓玛像一个地道的牧姑,穿着褐子袍,干着挤奶、打酥油、放牧的活儿。一年半后,昂王活佛又把她送到了农区,锻炼了一年。部落的人们很不理解。
其他部落的百户吓唬不争气的子女就会说:
“像昂旺百户一样狠心,赶你们去过苦日子。”
但没有听说哪家的少爷和小姐真的像卓玛去过苦日子的。
最后一年昂旺活佛又把卓玛交给了一个手艺不错的裁缝做学徒。在藏区坐在家里干细活做针线是男人的专利,女人只有干重活、粗活的份儿,卓玛成了我们这里的第一个女裁缝。
生格被认定为一座有名的大寺庙的活佛,去了寺院。这一次父亲和活佛谈的尽是些人间烟火的事,特别是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
一天中午,家丁带进来一个老头,耷拉着脑袋,只见花白的头发劈头盖脸,尽管是康巴汉子那种发式,但是看样子好长时间没梳洗过,像架在树上的喜鹊窝,毛毛草草一团。大儿子索南也跟着进来了,向他父亲汇报,说这就是抢了他家商队的强盗,他们送来被劫的货物,并来谢罪。
这人走到昂旺活佛跟前。“扑通”一声双膝落地说:
“仁波切,手下人无知才抢的,您仁慈又大量,请宽恕我们的罪过。”
说完他抬起头的瞬间,吓我一跳,天哪!这肯定就是父亲常说的那个“那囊”,让我梦魇的人。鼻子大而奇丑,鼻头黑黑的有我的拳头那么大,鼻头上还疙疙瘩瘩的,疙瘩还开花了,像草地上干裂的蘑菇。
“我是从箱子里的文件才知道是您家的货物,速带手下来赎罪,随您处置发落。”
当看见了昂旺活佛身边的父亲,他定眼仔细打量一番。忙说:
“这不是嘉喇嘛吗?我今天真走运,您也在这里,替我向仁波切求求情,我从来不抢穷人、好人,常抢马步芳的商队和坏人的东西,现在马家的商队很少了。听说马步芳和共产党打起来了,兄弟们饥不择食碰上了就抢,真是有眼无珠,偏偏抢了您家的商队,这是我行抢生涯中的耻辱,所以我前来谢罪。”
昂汪活佛走上前,扶起了“那囊”说:
“世道不同了,共产党就要来了,共产党把马家军都收拾了,还能让你们这些小毛贼搅得草原不得安宁吗?靠抢劫为生的日子不会有了,看你一把年纪,我给你一笔养老的钱,回家颐养天年吧!该念经赎罪的时候了,念佛一声福增无量,礼佛一拜罪灭沙河。愿你下辈子还能转世为人。”
那囊感激涕零,一再说:
“愿佛祖保佑你们平安、长寿,我真是三生有幸,碰到您这样广施善事的活佛。”
还说了一些他再不行抢的话,临走时,磕了三个长头。
索南带他下去处理此事,砸了强盗的刀和枪,归还了马,赏赐了一些东西,并给那囊一笔钱打发他们走了。
父亲对昂旺活佛说起了他与那囊的两次相遇。父亲说:
“这那囊是有善心的强盗,听说抢了牛羊分给穷人,常教诲草原上的孩子们,‘你们长大后做什么都好,甚至去乞讨,打旱獭也可以(在藏区打旱獭是最底贱的一种职业,只有贱民才从事这种职业),就是不能做强盗’。汉地把这种劫富济贫仗义施财的强盗叫侠客,和强盗是两种人,老百姓对待这两种人态度截然相反,对强盗既恨又恐惧,但对侠客既向往又充满敬意。那囊的本性是善良的。”
因为没有玩伴,我感到无聊,这儿是大人的世界,好动的我处于好奇。东转转、西窜窜,转遍了他们家的旮旯。这天转到后院,正赶上他家商队从银库提银元,让我大开眼界。
银库是单独修建的三层碉楼,前不靠墙,后不连房。第三层住看护人,第二层是银库,墙体是用厚木版箍架,中间是用土夯成的墙,足有一米厚,第三层地板中央有木框洞,银元入库时经清点,从这洞口倒下去,木框盖板上锁,贴上封条烙上树脂胶印。银元出库时,第一层天花板处有一个机关,把楔子栓一拉开,银元顺着这木槽倾泻而下,白花花的银子带着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哗哗地流出了,七八个和尚点数装箱。木头钱箱用生牛皮包裹。牛驮带的是五百元的钱箱,骆驼驮的是一千元的钱箱,每隔半月从银库提一次钱,商队也是每隔半月启程到西藏和印度,同时西宁和印度的商队也回来了,就这样交替穿行,商贸活动一片繁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