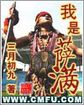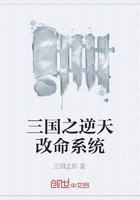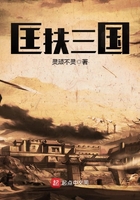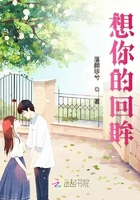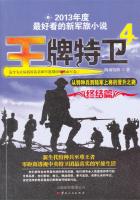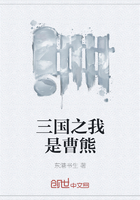我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我说,贵部孙蔚如先生同我红四方面军有来往,我们是知道的。贵部派的张含辉,到过通、南、巴苏区,我红四方面军保证了安全,取得了谅解,因而贵我两军在两年中,没有大的摩擦,孙部得以安驻汉中,兵员有了很大的发展,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来中央军第1师胡宗南部,依靠天水地区,积极向南扩展,势力伸张四川西部,不仅我们侧面受到威胁,同时孙部也受到威胁,但孙部对胡宗南部不加抗拒,特别是当中央红军到达川西时,胡部已深入到嘉陵江西岸一带,阻碍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了顺利地同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必须安全地渡过嘉陵江,要安全渡江,必须设法调离沿江驻守的胡宗南军队。所以才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明攻汉中,威胁天水(胡军后方),调动胡军返回天水,胡部果然以为我军攻打汉中、天水,撤回了川西部队,集中天水,防我进攻,给了我红四方面军回师西进的良好机会,安全地抢渡嘉陵江,完成了与中央红军会师的任务。这种军事行动,说清楚了,先生是会谅解的。杨先生知道,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果决定消灭孙部,就可以依靠川北苏区,三路出击,东路依万源、城口进攻镇巴、西乡;中路依通、南、巴翻越巴山进攻南郑;西路依广元进攻宁强、沔县。东、南、西合围南郑,汉中地区腹背受敌,不是更容易得手吗?何必单从西路一线进攻呢?这点也正充分说明了我军攻击汉中地区,只是调动胡军之手段,并不是以歼灭孙部为目的的。
红军25军,从鄂豫皖苏区突围后,长期行动,得不到补充和休整,有困难。该部到达陕甘边地区后,是准备休整的,可是贵部柳彦彪旅,天天尾追,逼得红25军不得不自卫,山阳一战该旅溃败,而贵部警备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并且张部尾随比柳更为接近。红25军误认该部要乘机攻击,遂于柞水之九阎房接火战斗。在战斗中,张旅长被俘,由于红25军自鄂豫皖突围开始即和上级失掉联系,不了解张汉民同志的情况,所以误杀了他。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因为张汉民确是我党党员,现在我党中央已追认张汉民同志为革命烈士。这个事件,对于17路军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沉痛的损失,但却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有力材料,以张汉民同志被杀来反击国民党的指责,说明17路军并没有什么共产党,打掉蒋介石削弱17路军的借口。
至于红军的态度,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主席给杨先生也写了信,想必杨先生是清楚的,今后贵我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就会互不伤亡。这对17路军之发展壮大和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我们认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之发展,也就是反动卖国势力的削弱,所以我们只有帮助成长,防止损失,这就是我们对17路军和东北军的态度。(27)应当说,汪锋的上述解释对消除杨虎城顾虑直到了重要作用。但还不能说完全消除了杨的思想顾虑。因为,在此之前,汪锋本人与杨虎城并不熟悉。杨虎城在与共产党的交往中也没有听说过汪锋这样一个人,加之蒋介石派往西安监视杨虎城的特务多如牛毛,杨虎城也顾虑这万一是蒋介石设下的圈套,是蒋介石为试探他的态度而制造的假信,因而没有同汪锋进行深入交谈,双方也未就中共中央提出的4条建议形成什么共识。但汪锋之行至少产生了这样的效应,即它向杨虎城传递了共产党愿意与他合作抗日的信息。于是,在与汪锋会见之后,杨虎城很快即派人到天津核实汪锋的情况并表示希望南汉宸最好能来参加在西安的谈判。南汉宸派来的代表是曾经在17路军工作过的中共北方局联络处长王世英。
王的到来,不仅向杨虎城证明了汪锋确是中共的代表,而且带来了南汉宸代表中共北方局提出的关于合作抗日的六项建议:
一、在联合抗日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二、在现有的防区内(可商定)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退进,或放空枪,打假仗;三、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四、甲方(17路军)在可能条件下,掩护乙方(共产党)往来人员的交通进出:五、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他物资;六、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以加强联络和便利往来交通。
杨虎城对以上六点表示基本同意,但他也提出3条意见:一、联络东北军中上层将领,要求南京抗日,先作合法运动,到适当时机再变为不合法运动;二、整顿内部;三、与红军的关系是:1.维持原防,互不侵犯;2.交通运输上在可能的范围内予以帮助;3.不要策动他的部队哗变;4.绝对保守秘密,可建立电台联系,但以后不要给他写信或随便派人来,以防泄露;5、希望陕北红军对井岳秀保持与他同样的关系。于是,王世英便和杨虎城以此为基础进行协商,并顺利达成了4点协议:
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17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三、17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四、双方同时做抗日预备工作,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28)为了落实双方达成的合作协定,杨虎城旋即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主要是:
一、实现17路军和红军问的休战状态。杨虎城派他的秘书和一些亲信向前线的旅、团长分头作了暗示,有些是杨亲自授意,以确保不再发生战事。自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7路军就未再与红军发生冲突。
二、准备了与中共联系的秘密电台,中共中央委派张文彬出任中共驻17路军常驻代表后,杨虎城委以上校参议衔的公开身份。
三、在17路军设立了交通站。
四、杨虎城亲自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在1936年元旦对连以上军官的训话中,杨虎城公开抨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他说:过去对敌人,我们还敢指名道姓,而今天却用××来代表日本,这是我们最大的耻辱。今后我们部队的训练再不能按打内战那一套搞了,不管别人抗日不抗日,17路军是坚决要抗日的。
五、成立特别稽查组,加强情报收集和对付国民党的特务活动。
六、确立了17路军与红军合作的准则。内容包括:双方消除一切敌对行动,互不侵犯,发生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双方交换情报,遇有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消息;由17路军负责制止一些地方民团的反动活动,不破坏革命组织;保证群众的自由通商及双方地区的贸易往来等。
杨虎城虽然在履行协议上作出了努力,但他与共产党合作的一些疑虑还没有完全消除。在8月下旬中共派潘汉年去西安与杨虎城会谈时,就反映了杨的犹豫和戒备。杨向潘汉年谈了三个问题:“一是17路军不能一下子转变为红军,目前只能从政治上加紧准备。二是合作途径如跟张某(张学良)走,须另起炉灶。三是军事上先打通国际路线。”(29)杨虎城的这番话表明,他在政治上还有进一步观望的念头,在军事上也还有对红军和东北军的力量是否足以抵抗蒋介石中央系国民党军队压迫的担心。于是,中共中央急调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前往西安与杨虎城进行谈判。1936年9月6日,杨虎城在与张文彬谈判中,表示同意中共提出的各点意见,但提出5点希望:1.17路军目前尚不能离开南京国民政府,不能与红军立即走一条路,愿走“人”字路,将来再会合;2.张学良部复杂,西北由他领导恐有不可取之处,建议成立三方面会议,合组各方面参加的抗日核心组织;3.希望红军有一定的根据地,不继续游击战争,根据地最好在陕、甘、宁;4.担心目前得不到国际援助;5.准备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妥善答复了杨虎城提出的5点希望之后,红军与17路军于9月7日正式达成了合作协定。至此,中共与17路军联合的障碍终于消除,联合的局面开始形成。
接受张学良“联蒋抗日”的主张,弥合蒋介石离间挑拨所造成的张、杨分歧,中共的政策调整和有效运作。使西北的抗日大联合终获成功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工作,到1936年上半年,中国工农红军分别与张学良领率的东北军和杨虎城指挥的17路军结束敌对状态,开始成为共同抗日的友军。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的重大突破。但是,这与实现西北“三位一体”,即达成红军与东北军、17路军三方面联合抗日局面的既定方针,尚有一定距离。
此时,三方联合还存在两大障碍。
其一,是如何对待张学良提出的“联蒋抗日”的主张。在1935年底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针时,虽然改变了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并称为卖国贼的提法,此后再提卖国贼时也是只提蒋介石,不提张学良,但并没有改变“抗日反蒋”的政策。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秘密会谈时,虽然对改变这一政策有所松动,但周恩来明确表示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需要中共中央集体研究作出决定。熟悉中国共产党决策程序的人一定明白,实行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的共产党,如此重大的政策变动,必须在中央决策层形成共识,当时还要得到共产国际的首肯,而这一决策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其二,是如何弥合东北军与17路军的矛盾。张学良与杨虎城在1935年之前没有发生过直接联系,历史上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军阀派系,张属奉系,杨属冯(玉祥)系。而当他们各自附蒋后,张先后活动于东北、华北和鄂豫皖地区,杨则在河南、西北(主要是陕西)地区活动。这在注重渊源的旧军队,其合作的感情基础是薄弱的。蒋介石正是抓住这一点,不断地离间张、杨及其所分别领率的东、西北军。
张学良来西北前,杨虎城身为17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是西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首领。张到西北后,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这就是说杨在军事上要受到张的节制,进一步扩大地盘已不可能。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人陕本来是奉蒋之命主持“剿共”,但也不能不使西北方面有人担心东北军是乘机抢夺地盘。对此,杨虎城存有戒心是自然的。张学良也不是没有想法。他感到,初来西北,人地两生,想在西北站住脚,实非易事。
两位主帅的心思,在两支军队中亦有反应。东北军自恃兵力强,装备好,看不起17路军。17路军感到东北军丢了东北的家乡还盛气凌人,遂讽刺说:“人数那么多,装备那样好,为什么丢掉自己的家乡,跑到西北来?有本事上去和红军较量,别对我们耀武扬威!”这样一来,两支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在戏院看戏为争座,在饭馆吃饭为争先后,在街上相逢为争路避路,经常吵架打架,甚至发展到互相开枪的地步。另外,东北军入陕带着大批随军眷属,不仅基层以上军官,甚或普通的伙食兵和司机也带来了眷属和子女,这既引来17路军一些官兵的嫉妒,也因吃住困难、强用民房,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17路军对东北军这种做法看不顺眼,东北军也觉得陕西人有排外思想。因此,两支军队之间、东北军与当地居民之间也不断发生冲突。
蒋介石看准两军的矛盾后,开始了他早已准备好的离间战术。他对张学良说:“汉卿,你要好好地干,只要东北军‘剿共’成功,将来可以把杨虎城调离陕西,西北归你。”同时,蒋又散布张学良想“失之东北,收之西北”,并派人向杨虎城说:“张学良有大西北主义野心,你要提防,可别让他们把你的地盘吃掉。”(30)蒋介石的目的,显然是通过利用和制造矛盾,使张、杨互相牵制,从而加以操纵。
安插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也借机制造张、杨不和的谣言。不是说东北军要解决17路军,就是说17路军要驱逐东北军。日子长了,这些影响必然扩散到两军的中上层军官中去,使两支军队的关系一度颇为紧张。
为了实现西北的抗日大联合,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发挥中坚和政治领导作用,当然这首先需要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政策做出调整,也需要切实解决一些棘手的实际问题。
中国共产党调整政策的第一个大的举措是将“抗日反蒋”的口号调整为“逼蒋抗日”。实际上,这一转变的过程甚至在1936年2月即已开始了,就在这一年的2月27日,经宋庆龄介绍充当国共之间联络“信使”的董健吾到达瓦窑堡。此时,张闻天和毛泽东正在山西前线指挥东征作战。董健吾就将宋庆龄的密信交给了留守后方的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博古。并向中共方面透露:国民党内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蒋嫡系中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的主张联红反日,有的主张联日反红;蒋介石本人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
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在山西前线致电博古转董健吾,明确表示:中共为了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并提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的五项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抗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31)这份电文首次没提“反蒋”,而强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国民党及所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公开表示,在“抗日”的前提下,“反蒋”的方针并不是不可改变的。
也就在这一天,中共谈判代表李克农在洛川与张学良进行了秘密会谈。张学良除了不同意李提出的“反蒋抗日”之外,在其他方面都表示了赞同的意见。李克农把这一谈判结果很快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对张学良的这一态度十分重视,他把张学良的意见与此前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联系起来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发生分化。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应当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反革命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对张学良要实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直接谈判。
同月,刘长胜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全部文件带到山西东征前线,周恩来、博古也很快赶到前线,中共中央随即于3月20日到27日在山西孝义、石楼一带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由于战事频繁,会址几次变动)。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发、博古、王稼祥、张浩、洛甫、林伯渠、彭德怀、杨尚昆、凯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