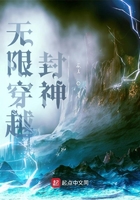纳兰王府内张灯结彩,大红的喜字,贴在门楣两侧。
红灯笼一路的挂到府中去。
来来往往的仆役,都笑逐颜开的,今天是他们的王爷纳兰澈的大喜日子。
老福晋在前厅里高兴的张罗着,纳兰澈是独子,他的父亲,老纳兰王爷去得早,这些年来,老福晋终于看到儿子这一天,心上很高兴。
娶的是城南陈家的大小姐,陈端华。
城南陈家,以经商发家,这些年来,宫里的丝绸绫缎,都是他们陈家供给的。连老佛家也对着陈家有着耳闻,一听此姻缘就准了。
纳兰姓是世袭王爷。
纳兰澈,长得俊雅迷人,又因着被老福晋宠着,家里的丫环仆人爱着,所以,极为自负与骄傲。
此时已到了吉时,他的贴身仆人常发,却找不见了他,又怕被老福晋骂,只得一个人在纳兰府内轻轻的唤着他的主子。
“王爷,王爷!”常发一边的喊,一边的走着。
就这时,听到一丛的花树后,有王爷贴身近婢紫萝的声音:“王爷,您喝得多了,快些的去吧,今天是您的好日子呢?”
常发探出身子去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原是,王爷正坐在凝碧湖的亭子上,怀中抱着那丫环紫萝,兀自的亲着,那丫环紫萝,只一边的推拒着,一边的求饶:“王爷,奴婢为着您好呢,一会儿,老夫人看不到人,就要骂了,您也为着我想一想,您说要封我做侧福晋,也不想我为难吧!”
常发知道自己的主子,不是个消停的主,这紫萝,早就是他的人了,老夫人于此事上,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要是往日里,常发也只有当做看不到,偷偷的溜走了,可是今天不行,前厅里的宾客已经迎门,老福晋一个人在那里支撑着,再找不到人,怕就要发怒了。
常发咳了一声,给亭子里那两个人整理好了衣裳,坐得端正了,他才慢腾腾的走过去。
“王爷,吉时就要到了,老夫人叫我来找您,要去接花轿了!”常发不敢抬头,只听得那纳兰澈在轻笑,还有紫萝的强自抑制的笑声。
常发等了半晌,也不见主子回答,只偷眼去看,却见到纳兰澈正抱着那紫萝在怀中,紫萝一边的受窘,一边的半推半就,纳兰澈的一只手,就伸在紫萝的衫裙里,常发见此忙低下头去,再不敢去看,只是,他还得说道:“王爷,错过了吉时,就不好了!”
这一次,纳兰澈终于听到了,他说道:“好的,去更衣,接我的新娘子去!”
常发这才松了口气。
纳兰澈走在前边,常发跟在后面。两个人向着纳兰澈的住所走去。
紫萝私自的理着自己的衣裳,抬起头来,眼中闪过一丝的狡黠,与她刚刚的面相极为的不称。
纳兰澈走了几步,见紫萝并没有跟上来,就回头叫道:“紫萝,还不快些,误了我的吉时,拿你算账!”
紫萝听了,就一路小跑的赶了过来。
城南陈家,亦是张灯结彩,陈老爷在前厅上,高兴的与亲戚朋友寒喧着。
都说这陈老爷有些的惧内,所以,就算是已近知天命之年,却无有一子,也不见他纳妾,却把全部的精力投到了夫人为他生的两个女儿身上。
陈家有二个女儿,大女儿陈端华今年十八岁,小女儿陈端玉,十五岁,因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以,具体的样貌,外人不得知,只有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言。
都说是绝代双娇,人比花美,但传言多数也都当不得真的。
但听闻陈老爷为她们两个请了西席,又请了舞师乐师,据说是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这一次,陈端华与纳兰澈的联姻,便成了世人眼中的好姻缘,因为,那纳兰澈,也有着当世风 流才子的雅号的。
陈家的后花园,亦有湖有亭,此时,那陈家二小姐,立在湖心亭上。
清晨,她苗条的身子,在蔼蔼的雾气中,显得纤细得如弱柳扶风般,一副细腰,只不盈一握。
慢慢的转回身来,一双眼中,光华灿灿如星,只一张一合间,敛了这湖面所有的光泽般。
姐姐今天就要嫁人了呢,她心中有些不舍,清晨起,有丫环为她洗了头发,此时的发上,犹带着水珠般。
一早上,母亲就在姐姐的房里忙着,又有着众多的丫环婆娘的,挤了一屋子,她无奈的,挤不上去,只有出来透气。
昨夜里,她与姐姐挤在一张床上,她知道姐姐一直的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她便问:“姐姐,怎么还不睡?”
陈端华反问她:“端玉,你怎的还不睡?”
“我想你,睡不着!”陈端玉道,她说的是真心话,这十几年来,她一直与姐姐形影不离,突然的,姐姐要嫁人,要去了另一个府中,她无法排解的,胸中一阵的郁闷。
“恩,我也会想你的!”陈端华说道,两个人的手,就握到了一起。
陈端华叹了口气,被妹妹听到了,陈端玉问她:“都说纳兰王爷,人才风 流,一表堂堂,姐姐为何还要叹气?”
“说不上,只是很怕!”陈端华道,她捏紧了妹妹的手。
“我连见都不曾见过他,想到明天,就要与他成为夫妻,我……”陈端华一张圆润的脸颊,于月光中,泛着玉色的光。
陈端玉无法理解姐姐的恐慌,只是,她真的舍不得,她的头靠到姐姐的肩上,只跟着长吁短叹,就这样,竟也睡着了。
陈端玉竟做了个梦。梦中,她看到自己的床上,搭着一件漂亮的裙子,拿起来看,绣了大大小小的蝴蝶,很美很漂亮,她欣喜的穿到了身上,裙子好美,她刚学会的一曲百蝶舞,便兀自的跳了起来。
正在这时,听到有人在拍手,她扭回头去,见不真切,却是个男人,她吓了一跳,就急着躲开了。
可是,躲起来后,她却发现,裙子的下摆开始着起火来,小小的火苗一点点的上涨,她很害怕,就叫了出来。
“端玉,端玉!”姐姐在叫她,还摇着她。
原来是一场梦呢。陈端玉出了一身的汗,但看到天色微亮,一夜竟已过去,再看姐姐,眼睛略为虚浮,竟是一夜未眠般。
正在这时,听到外面的老仆人张妈的话语声:“大小姐,起了吧,要开脸了!”
她们姐妹刚起床,就进来了一屋子的人,陈端玉还被自己的梦惊着,本想和姐姐说说,解了胸中那一口闷气,可是,姐姐却开始忙了起来,洗脸,看到刘妈拿着红线,在姐姐的脸上绞着脸,然后,又是上头。
听着好命婆一边的梳,一边的念着:“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梳到儿孙满地”。
陈端玉见到姐姐的头发好长好密,光油油的,只梳成平平板板的髻,再也不是做小姐的发式了。她看到母亲站在姐姐身后抹着眼泪,姐姐也要掉泪,那好命婆则说道:“陈大小姐,您可别哭了,一会上妆,要花了脸了!”
明明是好事,可是,陈端玉感觉到心中烦忧,想到姐姐这一去,自己少了说知心话的人。她也落下了泪来,那好命婆见了,就笑道:“哟,我说二小姐,您哭得太早了点,等你出嫁,才要好好的哭一场呢,呵呵……”
陈端玉虽然不太懂,但也知道她是在取笑自己,便在一屋子的笑声中,跑了出来。
府中挂着红灯笼,各外的廊下,都结着喜绸,隐隐听到前厅里传来的贺喜声,陈端玉拐过长廊,来了了后花园里。
一直的站在亭子里,直到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她才转过头来。
西席江泊清,自陈老爷请了来,就一直的住在后花园的一个闲置的仓房里。
江泊清是个屦试不第的落榜秀才,他的父亲当年就是闻名一方的名儒,但也是空有才华,做了一辈子的私塾先生,娶妻生子后,将满腔的报负,倾注在儿子身上,不想儿子连考了三年,也是名落孙山,如此一来,气恼伤身,几年前,终于含恨西去。
陈老爷见江泊清为人诚恳,又满腹经纶,便请了来府上,让他教自己的两个女儿。
江泊清有一个老母,此时,也寄住于陈府上。
江泊清见陈端玉转过身子来,这是他头一次于私塾之外见到她,于这个弥漫着轻涩草香的清晨,他见到陈端玉一脸凝重的回眸,她清澈的眼眸,如一汪秋水,他发现,自己的心跳停止了。
只这一瞬间,他发现,他一直教授的陈二小姐,已经长大了,他记得初次见她时,她只有十三岁,站在姐姐身后,怯怯的看着他。
而此时,她的目光在见到他后,显出些错乱来,想必她也没有料到,会见到他,也有些意外,听到她柔柔的道了句:“先生早!”
“二小姐早!”江泊清道,略低了下头。
如江泊清所想,陈端玉没料到会遇到他,此时四处寂静,她不好就这样单独站在这里与他会面,她向着江泊清福了下身子,便走了过去。
但错身而过时,她想起了自己刚刚郁闷的,就回首问道:“先生可会解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