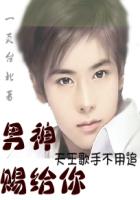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先转回去说说阿仁。
阿仁是私坊的打杂小伙计,据说,是我娘当年还当花魁时好心收留的弃婴,后来我娘生了我,丢了客缘,被妈妈赶到杂院,阿仁便也跟了过来,所以,我和阿仁是打小一处长大的,按读书人那文绉绉的说法,叫作“青梅竹马”,按师父那古怪说法,叫作“幼驯染”。
对于“幼驯染”三个字,师父是这样解释的:从幼小的时候开始就驯服他感染他让他听见你喊他就屁颠屁颠撒小腿儿奔过来见不着你就蹲门口呜呜地不肯吃饭进门替你铺床出门替你开道你指哪儿他打哪儿——总结一下就是一只从小被驯服的忠诚的旺财。我觉得很有道理,虽然念起来有点儿喘不上气。
阿仁比我大三岁,就叫阿仁,坊里都不知他姓什么,阿仁自己也说不知道。自打娘被赶到杂院,往来客人便尽是些三教九流的浑汉子,嘴巴从没干净过,院中杂役与龟奴当然更牛气,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常拿阿仁来打骂出气。每次,阿仁都护住脑袋一动不动地任由他们揍,不理不睬地仿似他们不存在。但若是那些混帐东西辱及了他的父母祖上,他一定会跳起来咬人。那时候,小小的一个人,除了牙齿,哪里都是柔弱的,很轻易就会被一巴掌打翻在地,老半天都爬不起来。但他总还是会顽强地爬起来,再扑上去,哪怕是鸡蛋磕石头,也要死磕到石头厌烦了住口罢手为止。几乎人人都嘲笑他,骂他是没爹没姓的小杂种,他从不还嘴,不争口舌之快,可是他眼里的火光从不曾熄灭过。那些跳动的火焰,从幼小的微星一点燃起,渐渐成了熊熊不息的茁壮,无论是在被人欺凌的时候,还是拭去血汗的时候,我都看到了。阿仁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坚韧的男人,比任何美服华冠光彩照人的纨绔公子都更像个男人。
阿仁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便渐渐显出英俊模样来,什么“皓齿如贝,薄唇如脂”那是酸秀才说的,及不上他的万一。他的眼睛尤其好看,狭长着在眼尾向上挑起,乌黑而剔透,我看着他的眼睛时,常错觉能看见太阳,就算是夜里也一样。曾有个讨水喝的道士称赞他“龙眉凤目,是落难的贵人,日后必有腾达”,阿仁随口道个谢,给完水就把人打发走了,啥别的也没说。“龙眉凤目”这个说法我很喜欢。这才是阿仁。
但不论再如何“龙眉凤目”,阿仁首先还是个人。
这人么,据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我们这儿年过十五便算是成年男丁,就该娶媳妇了,否则据说就会出“乱子”——虽然,对于一个靠色相苟合吃饭的地方,和从小耳濡目染在这地方长大的我,这种“乱子”已经稀松平常到见怪不怪了。
我们这个杂院在坊里也是最末流,妈妈恨我娘砍了她的摇钱树才把娘踹来这里。在这里呆的,全是年老色衰或是病入膏肓的老妓。阿仁当然不可能对她们发生任何兴趣,我绝对相信他从审美到心理都是正常的!别院的姑娘们偶尔会来勾搭,阿仁也从不理睬,常是嗅着味儿就先逃得无影无踪。我也并不相信阿仁会翻谁家院墙与谁作怪,所以,若说阿仁会闹出什么“乱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身为一个善(xian)良(zhe)天(mei)真(shi)有(zuo)爱(da)心(si)的青梅,我很关心阿仁的身心健康。
于是,某年某月某日,我自以为很忧心很严肃地在饭桌上问他:“阿仁啦,你为啥都不想讨媳妇哩?你看阿黄一岁就知道跑出去会雌儿了。”当着我娘的面。
阿仁一口青菜汤喷出来,直接摔桌子底下了,差点没给窝头噎死。爬起来之后他都没看我,直接对我娘说了:“婉姨,想法子送小甜走吧。”
我娘很哀怨,默不作声,最终只叹了一口气。
娘当然是想让我走的,如有可能,走得越远越好,但关键却在于,我们没法子走。或者说,娘她不愿意跟我走,而我,也不能丢下娘。我们都被绊住了。
“什么时候娘肯走了,我才走。”我把这决定告诉阿仁。
阿仁沉默良久什么也没再多说。
但那之后,阿仁便神出鬼没起来,常整夜整夜的行迹无踪,白日里也总显得疲惫,再很少有工夫陪我玩了。
我也没打听阿仁究竟干什么去了。反正我知道,多半是为了赚钱。阿仁他觉得我娘不肯走一定是因为没钱不愿拖累我。而我却觉得,或许不是。阿仁是男人。娘和我是女人。女人的心思有时是很奇妙的,男人懂不了。
当然,我这绝不是吹嘘自己就懂得很多,我的确有许多事都还懂得不怎么透彻。譬如说,即便有这十几年私坊生涯的耳濡目染,我对“男人那些事儿”的事实了解仍然是一知半解的——这就是我不明白为啥阿黄要去找雌儿而阿仁不去讨媳妇儿的原因所在,直到十五岁那年,我意外撞破了阿仁一个小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