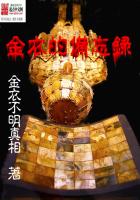导读:
......林大哥道,“可是求功名?那你可是来得晚了一步,别等了!葛半仙昨天夜里病死了,这不,我正要过去帮帮忙,将人收敛了,可怜,孤零零一个人,无儿无女的,也就靠着这些街坊啦!”
孙儒听得一头雾水,不由拦住了林大哥流水账本般的唠叨,“林大哥,你说笑了吧!我刚还让葛仙人解梦了,他还坐在这里,你好端端的,咒人家做什么?”说完回头一指,却见方桌空空,只有落叶纷纷落在上面,签筒、纸笔、幌子,葛半仙......似乎方才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
山路崎岖,落叶纷纷不断从树顶落下,怪鸟的鸣叫幽深刺耳。孙母在轿子里坐不安稳,有些头晕。毕竟上了年纪,七十多岁的人了。今日,儿子孙儒说要送她去新宅子看看,她心里自然喜欢。尽管这一个月来,儿子做出许多让她惊异的事,但他对自己倒是孝顺。想他从一个穷秀才,变成如今的光景也不容易,却不知这新宅为何建在这荒凉之地,听着怪瘆人的。孙母不由从轿子里向外问道,“儒儿,到底还有多远啊?”
孙儒的声音从外面进来道,“您老不要着急,没多远了,再走一段就到了。”
孙母大口喘了口气,闭上了眼歇着,心里盼着快些到了才好,真受不了这一路的颠簸。轿子咕咚一声落地,孙母险些栽倒,孙儒从外面掀起轿帘道,“母亲,到了。”
孙母颤巍巍地从轿子里探出身来,却见林深树密,遮天蔽日,落叶成堆,野兽足迹遍布,哪里有什么宅子?
孙母不由奇道,“儒儿,这是什么地方,你说的宅子在哪里?”
此时,四个轿夫面无表情地开始挖土。
孙母疑惑不已,看着负手而立,一言不发的儿子,心里七上八下。
“母亲,您养育儿子一场,儿子不能忘了,如今就给母亲找了个好去处,还望母亲不要嫌弃。宅子,就在这里。母亲看是不是风水宝地?”孙儒终于开口了,笑容可掬的模样,眼神却是狼一样。
孙母忽然明白,想起孙孙失踪,儿媳惨死,不由颤抖着用手指着孙儒骂道,“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难道要活埋了你的亲娘?!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怎么生出你这么个畜生,我这条老命,如今就和你拼了!”
说完一头撞过去,孙儒却伸手将孙母抱住,拖到了那已挖得不浅的坑洞前,挥手推了进去。
孙母摔在里面,一时难以动弹。孙儒立在坑边上,冷笑道,“母亲,你看这里山大林密,不埋了您,您还不是要被野兽吃了、连个囫囵尸首都落不下?那么不孝的事我可做不出。也罢,这手帕你拿了盖住脸,不要迷了眼睛吧!”
随即将一块手帕扔了进去,对四个轿夫喝道,“埋土!”
四个大汉立刻向坑内埋土,孙母失声大哭,试图从坑里爬出来却是无力起身,不一刻,就被土埋住了半个身子。孙母边哭边骂,孙儒却是立在一旁如释重负地浅笑,心道,“如今娇娇便不会给我脸色看了。”
忽然亮光乍起,一声惊雷炸响头顶。
四个轿夫全吓住了,惊惶惶对视道,“这个时节打什么雷?莫不是天谴来了?!”一时不敢动手。
孙儒见状,心一横,伸出带着金戒指的手,接过一个轿夫手里的家伙道,“看什么看?!我雇你们来这里站着么?还不动手?!快埋!什么天谴,我才不怕!”那四人才动手,七手八脚将那坑填平了。孙儒还怕不结实,上前踩了几脚才作罢,见天雷滚滚,冷笑一声挥手道,“回去。”带着死人扬长而去。
却说这孙儒,便是如此活埋了自己的亲娘,但在一个多月前,这孙儒还是个恭顺良善的孝子,满腹诗书的秀才。一切的起始缘由,皆因他的怪梦。
那晚,夜风习习,月凉如水。看书好几个时辰的孙儒,已然觉得眼前发花时,已是三更过了。
他揉揉眼睛,掩卷起身。先到里间看过,自己的妻子宁氏此时早已睡熟,姜黄的脸色透着久病不愈的凄楚。儿子睡在一旁,不安分地磨着牙,已经十来岁的孩子,还如幼童一般,整天傻呵呵地光着脚满地跑。孙儒又到了灶间,将明日里宁氏要喝的药泡好,等一早起来煎药。再回到屋里,见四壁清冷不由叹气,心中暗道:想我十七岁中了秀才,却自此屡试不第,如今年近而立之年,还一事无成,靠在书馆教书、当街卖字画为生。妻子与自己自幼结发,却是个多病的身子,生不得气、拈不得重。母亲年事已高,傻儿子也是只长食量不长心。这般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只指望着明年赴考,上天保佑能考取功名,也不枉费寒窗十几年的功夫。
心下憋闷,孙儒和衣躺在床上,傻儿见爹爹躺下来,便将胳膊搭了过来,孙儒抱着傻儿的胳膊渐渐睡着了。
梦里,孙儒恍惚走进了一片迷雾森森的旷野,零星的鬼火此起彼伏,四下却看不清道路,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迈着步子,一不小心被绊倒,眼前赫然是块横倒墓碑。孙儒吓了一跳忙向后退,却又踩到个骷髅骨,对着他嘎嘎地咬着牙,仿佛是活了一般。孙儒魂飞魄散地爬起身就跑,跑了半天却还在原地。墓碑遍地、枯骨纵横,这里仿佛一片荒废的墓地,常年无人打理,有的塌陷了,棺椁被侵蚀,野兽挖开吃了尸骨,却将零碎的骨头扔了一地。
孙儒磕磕绊绊地奔逃,满头冷汗,见前面有两盏亮光,便甩开步子跑过去,近了才看清,竟然是座大坟,上面一块墓碑,有三个血色大字:黄金屋。
孙儒正在吃惊,忽然那亮光近了,看去却是只硕大的黄毛狐狸正蹲在那墓碑上瞪着自己。孙儒吓得倒退一步,那狐狸此时张开嘴,不是鸣叫,却是和人一样嘿嘿的冷笑起来,听得孙儒头皮发炸,那狐狸笑了一阵,却张开大嘴哈哈笑了,声音也如人一般无二,神情满是戏谑与嘲弄。这景象将孙儒吓得魂不附体,惊坐而起,却听窗外雨声淋漓,是下雨了。傻儿还在睡着,宁氏倒是翻了个身,被他惊醒了。
“官人,你这是怎么了?”宁氏起身,披了件衣服问道。
“我,我方才做了个噩梦,我梦见在一片坟地里出不来,还梦见一只狐狸对着我笑,和人的声音一样......吓死我了。”孙儒喘着气,用袖子擦冷汗。
宁氏道,“怕是你平日读书太辛苦,有些累了。想我这病也不见好,拖累了官人了。”
孙儒急忙道,“娘子想多了,你我本是夫妻,自当如此的。看天色快亮了,我去给你煎药,你再睡一会儿。”
宁氏欣慰点头,却又对起身穿靴的孙儒道,“官人,你既不能心安,不如白天去寻算命的葛半仙看看,你这个梦到底是何吉凶。”
孙儒点头,随即便起身出去了。
次日天明,孙儒喂傻儿吃过饭了,又到正屋向母亲问了安,这才红着眼圈出来。他浑浑噩噩地到了镇东的小学馆。推开竹门一进院落,便听见里面炸开了锅似的吵嚷。原来是学童又在闹学了。他进门劈头被一本字帖打得眼冒金星,屋子里顽童闹得不可开交,任他放开喉咙喊,这些孩子没人听他说,跳来跳去,翻桌倒凳,将笔扔的满屋子飞,墨泼洒的一片狼藉。孙儒头疼不已,急忙上前拉,可拉住了这个,又爬了那个。最后这些孩子一窝蜂似的,借着打架的缘由,冲出了学馆,将孙儒撞翻在地,额头破了个口子,血流不住。
“董宝,钱小禄,又是你们带头闹,快些回来!”孙儒歪歪斜斜立在门口,对着那些孩子喊。
被喊的董宝和钱小禄回过头来,董宝满脸是汗地对着孙儒笑骂道,“孙秀才,你考了十多年,也不见中,还在这里给我们讲圣贤之道?.....我爹是可是举人老爷,见了县官大人都不用跪的,我干嘛要听你的?!”
钱小禄也嗤笑道,“我们都知道,你娶个老婆是病娘子,生个儿子是傻子,家里都穷得揭不开锅了,靠着我们吃饭,还有脸和我们装大?!.....走走,不理他!”随即哄笑着,这群孩子都跑了。
孙儒气得脸色发青,但头痛欲裂,到屋后的溪水洗了额头,找了块布按着伤口,就赶紧去收拾学馆,还未收拾好,好几个大人闯了进来,劈头就骂道,
“孙秀才,你怎么回事?我们掏了银子让你教我们的孩子念书,你让他们跑出去玩?你这先生怎么当的?”
“就是,能干就干,不能干我们换人。如今寻饭碗的穷秀才多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