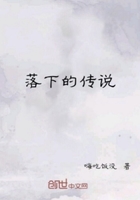刀疤脸极不耐烦地摆摆手,“够了,王魁,你说得太多了。”
王魁楞了会神,缓缓坐下,望着身前的篝火陷入沉思。
这时,散去的四名瓦剌武士陆续返回,手中提着獐子、野兔等猎物,收获颇丰。
不一会,火堆上传来烤肉的味道。
朱祁铭对这种野蛮的杀戮、粗鄙的取食方式很不适应,尽管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但他还是没有太强的食欲。
见王魁不愿再理会自己,他索性重新躺在雪地上,神思远游。
父王、母妃,还有皇祖母等至亲的形象一一浮现在脑海中,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可他拼命克制着,没让泪珠掉下来。
他想起了父王的教诲:在这世上,皇室宗亲得到的最多,所以秉持的戒律也应最为严苛,须时时不忘皇室宗亲应有的风范。
在贼人面前不落泪示弱,也是一种风范。
刀疤脸将一串烤肉递过来,朱祁铭再次扭头不受,他分不清那是出于对粗鄙的不屑,还是出于对强横的抗拒。
“你的命并不是非得留着不可,饿成了病秧子,只能把你扔给饿狼!”话音一落,烤肉便落入了刀疤脸口中。”
王魁闷着头,在篝火旁扫去一片积雪,露出枯草,覆上大衫,然后将朱祁铭提起来扔在了上面。
朱祁铭狠瞪了王魁一眼,暗道:逆贼!别指望我感激你。
他侧转身子,默默催促自己快快睡去,否则,饥饿的感觉将让他忍受彻夜的痛苦。
可是,堂堂皇室宗亲,沦落到与贼人为伍的地步,从天堂到地狱一般的落差,这样的境遇让他如何能够安然入睡?
更何况,此地离瓦剌远隔千山万水,不知这东躲西藏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他又怎能泰然处之?
也许永无尽头,明早醒来走出这片森林,只为下一程漂流;傍晚钻入另一片森林,只为下一顿烤肉。
他胡思乱想着,渐渐有了睡意,方阖上眼,却被一阵骚动惊醒了。
五名瓦剌武士手提着刀,直直地站在那里,篝火映出他们眼中浓浓的杀意。顺着他们的目光望去,丈远处赫然站着十多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男子。
这十多人对寒光闪闪的弯刀视若无睹,只是死死地盯着火堆上的烤肉,纷纷咽着口水,眼中闪出贪婪的光芒。
一声呼啸,十多条人影如饿兽般疯狂扑向火堆。
杀戮发生在短短一瞬间,当瓦剌武士在积雪上擦拭刀上血渍的时候,朱祁铭缓缓爬起身来,望着地上十多具尸体,他没有恐惧,没有导致恶心呕吐的不适,有的只是震惊。
“唉!他们是附近的饥民,沿途山林中会有成千上万饥民。”王魁眼中隐隐露出恻隐之情。
原来他们是大明的子民,因饿极夺食而丧命!朱祁铭觉得心酸,心酸过后则是迷茫。
他长这么大,离开越王府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出府活动范围仅限于皇城之内,所见所闻无不是一派富足的升平景象,何曾见过眼前这样的人伦惨剧?
看来,繁华的京城、王公勋戚云集的皇城掩盖了天下太多的苦难!
“这群男人的身后必有一大群妇孺,不行,不可留活口!”刀疤脸扬起刀,杀气腾腾道。
朱祁铭扑上前去,死死抓住刀疤脸的衣摆,“不要杀他们!”
刀疤脸将朱祁铭推倒在地,怔怔地看着他,似乎在分辨这声喊叫到底是怒吼,还是哀求。
“没了男人,那帮妇孺走不出这片山林,让他们自生自灭吧,若多事,恐惊动其他饥民。”王魁道。
刀疤脸収起刀,显然认同了王魁的建议。“把火灭了!”
众人连忙取下烤肉,将三堆篝火扑灭,掀起积雪覆住炭火,一时间,雪火相激的滋滋声响个不停。
四周一片漆黑,朔风钻衣入裤,寒意刺骨。
“这老天爷,昨日还是晴空万里,今日便翻了脸,伸手不见五指,真不给面子!”王魁哆嗦道。
这时,前方忽明忽暗似有火光闪动,目测一下距离,应在不足一里远的地方。
刀疤脸命令大家伏下身子,不准出声。
火光越来越近,终于看得清了,原来是一队披坚执锐的士兵手执火把朝这边走来,点点人数,不下于二十人。
可是,令他失望的是,这队士兵在离他们三、四丈远的地方向右拐去。
“盛千户酒量真吓人!都亥初时分了,还不肯散席,这不,寻常菜肴吃腻了,点着要咱们上野味,害得咱们在这深山老林里喝冷风。”一名士兵抱怨道。
“你知道什么!今日酒宴上的贵客大有来头,据说是京城锦衣卫千户。”另一人道。
“管他千户百户,今夜逮不住獐子野兔的,大家都别想回去!”又一人道。
眼看那队士兵就要走远了,朱祁铭可不想让大好求助机会白白溜走,他来不及细想,匆匆摸出身下的一块石头,用力扔了出去。
“谁?”众士兵齐齐转过身来,摆好阵势,凝神以待。
随着轻细的破空声响起,两名瓦剌武士飞身扑上前去。
那群士兵反应极快,就在电闪雷鸣之间,十副强弓硬弩便撒出了一片箭雨。
有戏!朱祁铭兴奋得几乎要大叫起来。
论迎敌应战经验,这群士兵可比那些锦衣卫校尉强多了。
两名瓦剌武士飞快地退回原地,其中一人借着火把照来的微光,拧眉看向自己的右臂。
方才他拨开了几支飞矢,可还是被后发但力道最大的那支箭擦伤了。
一名顶尖高手被士兵所伤,可见所谓练功能练到刀枪不入地步的传言,纯粹是鬼话!现实中武功再高,也得有肉身承载,铁甲也有被射穿的时候,何况是皮肉之躯!只不过武功高的人身形快、力道大、技法巧,一般人很难伤到他而已。
这里的关键是数量与质量之间的换算关系,武功低,但人数多,且彼此之间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自然能形成杀伤力呈几何数倍增的效应。
刀疤脸见同伴受了伤,低声道:“遇到硬茬了,他们是什么人?”
“这里距镇边城不远,肯定是城里的守军。”王魁道。
“从没见过如此强悍的明军。”
“这里的守军是募军,远非那些屯田的世兵能比。”
明代实行世兵制,所谓世兵制,顾名思义便是家中男丁世世代代当兵屯田的军户制度,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军户主要来自当年随朱元璋起义的“从征军”、故元和元末割据势力降明后的“归附军”、因犯罪而被发配的“恩军”、抑配民户入伍的“垛集军”。这些士兵以卫所为单位,平日里三分时间守城,七分时间屯田,加上兵源无选择性,所以战斗力不强。
镇边城是北境通往京师的门户,为防鞑靼人深寇,三年前,五军都督府力主招募民壮,在镇边城驻扎一支人数过万的精兵。但募军所费军需甚巨,宣德皇帝只准招募三千民壮,这三千民壮便是时下大明唯一一支募军。
募军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且无须屯田,可日日训练,所以武功和战术素养远胜于世兵。
这时,一名士兵叫道:“是鞑贼!大家小心,不可放走他们,否则,会有许多无辜百姓名丧其手。”
望着这群骁勇的士兵,朱祁铭由衷地感到自豪,一扫锦衣卫给他带来的挫败感。
刀疤脸召集同伴耳语一番,然后自己带着两人飞身绕向明军侧后,另二人则迎面扑上前去。
王魁拔剑踌躇不前。
朱祁铭只觉得心头一紧,正要开口报讯,战斗已然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一切都来不及了。
正面进攻的两名瓦剌武士一人中箭落地,一人被长戟撩伤了左臂。可是,侧后的三人使暗器放倒了过半士兵,瓦剌武士乘机欺上前去,余下的士兵立马落了下风。
眼看最后一名士兵死在刀疤脸刀下,朱祁铭心在滴血,一名稚子竟然感受到了悲壮与自责交织而成的滋味。
瓦剌人回来了,五人都挂了彩,其中一人左胸中箭,伤得不轻。他们脸上不可一世的神色不见了,代之以深深的落寞。
一名瓦剌武士扬刀扑向朱祁铭,王魁立马仗剑挡在他身前。
王魁瞪着刀疤脸,沉声道:“你得信守你的承诺!”
刀疤脸恶狠狠地瞪了朱祁铭一眼,然后挥手示意那名瓦剌武士退后。
“王魁老兄,镇边城明军强悍,而且锦衣卫也到了这里,你得把咱们带到安全的地方。”
“此地不宜久留,咱们应远离镇边城,藏入涿鹿山。”王魁道。
当下瓦剌人花了半个时辰分头疗伤。那个中箭的瓦剌人经同伴好一阵忙活,方能随队行走。
黎明时分,一行人来到涿鹿山。上山时,刀疤脸十分谨慎,喝令大家不得留下任何痕迹。
众人潜入一个山包上的凹坑中。
这处凹坑处于密林深处,四周雪树环绕,是个绝佳的隐蔽地点。
朱祁铭躺在王魁身边,只觉得饥寒交迫,全身虚弱无力。
他双手撑地,想坐起身来,却力不从心,一阵天旋地转之后,颓然扑倒在地。
这时,远方隐隐传来呼唤声,众人竖起耳朵,凝神静听。
“王子殿下!”
朱祁铭艰难地撑起身子,透过雪树的缝隙,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渐渐地,对面山头上现出十多个人影。
“王子殿下!”
多么熟悉的声音,多么熟悉的身影!
是越王府护卫!
短暂的兴奋之后,朱祁铭默默垂下头。他真的不愿发出求助声,害得这些护卫白白丢掉性命。
“王子殿下!”
这声呼唤内力充沛,震得树上的覆雪簌簌坠落。
师傅!朱祁铭再次举目望去。
果然是梁岗!
有师傅在,还怕这帮贼人做什么!
朱祁铭血脉贲张,浑身颤栗,兴奋地张大了嘴巴,就在他方要开口回应的时候,忽觉身子一麻,整个人立马瘫软了下来。
倒地前的一瞬间,他瞥一眼刀疤脸狰狞的面目,卡在喉中的那声叫唤化作一口悠悠长气,徐徐吐了出来。
“你们发现可疑痕迹了么?”梁岗的询问声飘了过来。
“没有。”不远处响起杂乱的回应声。
脚步声响起,紧接着呼声大作,只是呼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朱祁铭的心似乎紧随梁岗而去,他已神智不清,很快便昏睡过去。
当他悠悠醒转时,发觉被制的穴道已被解开,可他无力活动身子。
冷,无比的寒冷!一阵剧烈的抖动之后,他归于平静。
身体似乎与大地融在一起,血液快要凝固了。迷蒙中,那二十多个殉职的勇士仿佛向他缓缓走来。
“这小子不行了,活不过今晚。”刀疤脸冷冷地摇着头。
王魁蹲下身子,将一块干肉递到朱祁铭手边。
生存还是毁灭,或许只取决于一块干肉,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
他用尽全身力气,终于抓住了那块干肉,然后哆嗦着把它送到嘴边。
屈辱撕扯着心灵,片刻间,他已泪落如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