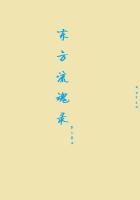唐戟提刀护在朱祁铭身侧,身后旋即响起梁岗的叫声。
“殿下不可走远!”
梁岗纵身而来,警惕的双眼飞速扫向街面。
“梁师傅!”朱祁铭回望梁岗后,再看街面时,那二人已不知所踪。
“咦,看花眼了?”唐戟挠头自问,一副恍然如梦的样子。
“街面上鱼龙混杂,殿下快回端礼门内。”梁岗的表情显得很是不安。
方到照壁前,内侍的通传声惊动了空中的鸽群,也留住了三人的脚步。转眼间人影一晃,卫王俊美的面容、健朗的身材呈现在了他们眼前。
“侄儿祁铭见过十叔王!”朱祁铭笑嘻嘻地上前见礼。
“祁铭!”卫王双目一亮,脸上那道亲切感仿佛是从骨子里渗出来的一般,令见者无不动容。伸手就要抱起朱祁铭,后者闪身一避。
“行行行,你是小大人了,都不好意思让十叔抱了。”言毕,卫王拉住朱祁铭的手,向府中走去。
“十叔王为何许久都不过来看祁铭呀?”朱祁铭兴奋的小脸上透着些许的埋怨。
“才三个月而已,皇上、太皇太后不首肯,十叔可不敢擅来。”卫王似有些伤感,随即展颜一笑,“祁铭长进真快!都能谈史了,还能过太皇太后这一关,嗯,日后必是皇室宗亲里的芝兰玉树!”
朱祁铭满含期待地仰视卫王,“十叔王,皇祖母夸我了吗?”
卫王大笑欲言,突然一顿,笑色微敛,“太皇太后岂会轻易给人好评?下次吧,太皇太后每月都会考你,总有一天会夸你的。”
朱祁铭有些失望,转念一想,这便是了,昨日谈史自己心虚得差点尿遁,怎会赢得皇祖母好评?下次可不能这样了!
说话间,二人已到存心殿前。
年轻貌俊的朱瞻埏甫一现身,便在存心殿门外引发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几个年长的丫鬟搔首弄姿,以求引来美男一顾,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朱瞻埏的身影云淡风轻般飘过长廊,转眼便没入了存心殿。
越王快步迎上前,双方寒暄后,卫王拉住朱祁铭深深看了一会。“三兄啊,我觉得祁铭长得像我。”他与朱瞻墉的关系最密,所以说话时少了许多忌讳。
“诶,不对呀,你该不会是来夺我儿子的吧?要知道,祁铭出生时,你身上的乳臭还未干呢。”
一阵轻松的畅笑过后,宾主分头入座。
两名丫鬟进来奉上茶,出门时偷偷瞧了朱瞻埏几眼。
屋中已无旁人,卫王的脸色立马变得异常冷峻。
瞧这情形,十叔王肯定有正事要谈,朱祁铭料父王会劝自己回避,便不太情愿地转过身去。犹豫片刻,觉得父王并无撵自己的意思,便择个偏座,小心翼翼地坐下。
“三兄,朝中情势甚是诡异,我在御前的数番谏言不知为何竟传入了一些藩王耳中,肯定有人在紫禁城安插了耳目!最近不知从何处传出一堆谤诬之言,明对我,暗指你。”卫王的神色显得十分悲愤。
越王面色虽显平静,但心中也是不安,说到底,根基浅的十弟是他的一道外屏,他不能不担心十弟的处境。“十弟须得万分留意,近来你风头正劲,当心惹人嫉恨。宁王、周王的志趣可资借鉴。”
宁王是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周王是朱元璋第六孙朱有炖,二人都是自幼聪慧过人,成年后才识出众,深得朱元璋赏识。
可是,明代宗藩仍然没能跳出“劣胜优汰”这种逆向淘汰的历史窠臼,承平之时容不下贤王,到了天下大乱时,皇室宗亲里便尽是废材。
正统之前,明代宗藩不乏出类拔萃者,但一旦冒尖,就极易引来天子的猜疑,好事之徒会乘机散布谤诬之言,这个时候,摆在冒尖者面前的路不外乎三条:被皇帝“定点”清除;起兵谋反;韬光养晦。
宁王、周王与大多数宗藩一样,选择的是韬光养晦。别人韬光养晦大多是把自己的名声搞得污秽不堪,虽遭天子申斥,却能平安终老。宁、周二王则是舞文弄墨,才情它用。
宁王著书无数,其音乐典籍《神奇秘谱》、可与陆羽《茶经》媲美的《茶谱》这两部大作对后世与周边国家影响极大,堪称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周王则是明初著名的剧作家,是元明两代剧作家中,至今存世作品最多的一位,有人说他不逊于关汉卿。
默然良久,卫王幽然道:“如今宁王、周王都已年近六十,得享天年,又有传世宏著,的确令人羡慕,可眼下时移势易,社稷堪忧,我岂能袖手旁观!”顿了顿,脸上浮起激愤之色,“王振不过是天子家奴而已,却权势熏天,俨然一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做派,连皇室宗亲都不放在眼里!而朝中重臣呢,广召门生故吏,暗中培植势力,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还有瓦剌,于塞外虎视眈眈,尚未制服鞑靼,便敢纵贼滋扰我大明,真是欺人太甚!当此之时,我又怎能以宁王、周王的志趣为鉴?”
朱祁铭今日被十叔王的情绪深深感染,当他听见王振这个人名时,好一阵咬牙切齿,而听见“瓦剌”二字时,更是热血直涌。
“祖宗留下的基业如此雄厚,也不是那么容易败得了的,十弟须为自己着想,凡事留有余地。”
卫王双眉一展,眼中闪过两道光芒。“我与社稷荣辱与共,生死同命,岂能趋利避害!”
越王凝目沉思,良久后缓缓道:“天子年幼,宗室不宁,引得外敌窥伺,还让内外臣失了分寸,这个时候,太皇太后着实不易啊!”旋即眉头一皱,沉声道:“真到了社稷根基被人动摇之时,我绝不会坐视!”
在朱祁铭听来,父王的声音甚轻,却似有千钧之力。
惊人的信息点滴成流,在心田上轻淌,捡拾童趣的乐园似在隐去,而一片崭新的天空被徐徐托起,如此惊悚,又如此让人痴迷。
异样的感觉令朱祁铭神思恍惚,以至于十叔王、父王接下来的对话成了他的耳旁风。
“襄王改封襄阳府,此事已定,只待明年改元后颁旨。”
“亲王改封何其艰难!但愿此举能让五弟心安。”
送走卫王后,越王一只手抚着儿子的头道:“太皇太后以为,你若仅习武,来日不过是多了分匹夫之勇罢了。太皇太后想让你自幼熟悉兵法阵仗,所以,下月初,将有近千名幼军入府,另有谙韬略者随行,教你兵事,助你调教幼军。”
千名幼军入府,声势极小,不足以引起外界的过度解读。但一名王子受命练兵,这在大明对皇室宗亲禁锢颇严的大气候下,显得极不寻常。
朱祁铭无暇揣度皇祖母此举隐含的深意,一听说自己即将成为千名幼军的孩子王,不禁沾沾自喜,他甚至已经想好了设个幼军首领,唐戟自然是他心目中的不二人选。
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父王接下来的一番话让他的心立马凉了半截。
“下月初吕先生登门,你将行拜师礼。”
传言终于成了真,一想到欧阳仝教导自己两年,如今却要黯然离场,朱祁铭心中突然多了道莫名的伤感。
比伤感更强烈的,是一阵阵的头皮发紧:寒窗苦读出来的饱学之士极爱较真,吕希必是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