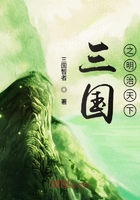轻灵的舞姿如仙子在山水间写意,不过,大明顶级舞者的舞姿不仅未能引发朱祁铭的共鸣,而且还遭到了他的漠视。
淡然扭头看向皇上那边,见皇上一副兴味索然的样子。朱祁铭的目光再往侧后延伸,见到了郕王兴奋得有点夸张的表情。
大凡才子士人都有自认为最完美的、理想化的女神形象,从屈原,到宋玉、司马相如,再到曹植,他们心目中的女神各不相同,而曹植的梦中情人或许有生活原型,所谓距离产生美感,可望不可即者就是女神。
这样的艺术熏陶对皇上的****启蒙并无太多示范意义,他是世间至尊,哪会让情人停留于梦中?
郕王倒似能从中找到灵感,就怕他的审美取向流于表面,不知舞只知人,日后对风华绝代的舞娘情有独钟那就麻烦了。
你还别说,若干年后,这样的事竟真的发生在了郕王身上!
皇上望了一眼如痴如醉的郕王,缓缓站起身来,朝后殿走去,途中回首冲朱祁铭使个眼色。
朱祁铭稍停片刻,起身从内侍、女官的人堆里钻过去,再与数名凝神戒备的禁卫插肩而过,这才进入了后殿。
禁卫就想入内近侍,被皇上挥退。
“杨溥将详情都禀报给了朕,你可别让朕失望!”皇上的目光透过殿外的人缝,落在舞台上人影绰约处。
看来,皇上还是忌惮杨荣!想皇上盼望有人以杨荣引以为傲的智谋,将杨荣那个心高气傲的老头给压下去,让他在政治舞台上黯然谢幕,这一结果或许不一定是各方都乐意见到的,但这样的手段一定是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朱祁铭顿时觉得那日在杨溥府上发出的挑战是多么的拿捏得当,恰到好处!
这是一场和平的较量,无需腥风血雨。可是,要赢得这场较量,很难!
“陛下,臣须查阅相关文书。”这些年大明在内政外交上到底做了些什么,朱祁铭知之甚少,他不想两眼一抹黑。
“文渊阁有往来文书的副本,此事你去找杨溥,他既然认同了你的挑战,哪有无故阻拦之理!”
“可是,臣身为亲王,公然索取朝廷文书,恐怕会引起举朝哗然,落个谤诬之言纷至的下场!”
皇上将目光移至朱祁铭脸上,“你不是还有个先生么?朕调吕希入翰林院,他奉旨查阅相关文书以备咨询,有何不可!”
让吕先生牵涉其中,这令朱祁铭稍感不安,但既然是奉旨行事,就显示皇上决意为此背书,于是,朱祁铭很快就将那丝顾虑打消掉了。“臣遵旨。臣告退。”
“等等!”皇上牵住朱祁铭的衣袖,缓声道:“三弟,你在越府练兵,何时能开赴战场?”
碰见皇上满含期待的目光,朱祁铭立马意识到皇上多么渴望用一场胜利来为他的成年亲政重新加冕,可自己一个亲王怎能率自己的护卫军擅离京城,奔赴北境?“陛皇兄,臣弟对杨溥说过,今日的练兵,只为他日赴藩后与入寇的鞑贼血战。”
“不行!鞑贼年年入寇,大明的九边对鞑贼而言,似乎并未设防,朕想调京军进剿,但百官必定掣肘,算来算去,唯有你越府的精壮护卫不在百官掣肘之列。你应该知道,宣德十年,皇祖母说你想训练幼军,是朕下旨挑选出千余最强壮的幼军入越府的。”
不在掣肘之列?未必如此吧?朱祁铭大感头疼,皇上显然不想也无合适的办法为越府护卫出战背书,就把天大的难题扔给了他这个亲王,朱祁铭很无奈,他不能抗旨。“臣弟一定想方设法率越府护卫军出战!”
朱祁铭悄悄出了后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不经意地扭头四顾,发现内侍、女官的注意力全被舞台上的表演牢牢吸引住了,只有御前侍卫在心无旁骛地全神戒备。
舞者迎来了曲终谢幕的时刻,但闻“哗”的一声,她的完美演出博得了满堂彩。这个时候,皇上回到了御座上。
“赏!”
一队宫女捧着宝钞、彩衣,还有若干珠宝步态端雅地走向舞者。
“多谢陛下厚赏!”舞者躬身谢恩。
顶级舞者总是善于以华丽开场,在华丽中谢幕,永远把最美的一面留在观众心目中。政治舞台则不比艺术舞台,许多人曾经一度华丽,却每每在落魄与不堪中谢幕,甚至数十年、数百年、数千年之后,还会被后人拉出来鞭尸,皆因私欲与贪念彻底毁坏了政治的艺术效果,而让政治成为一门艺术,这似乎只能永远停留在理想化的教科书中。
想想即将到来的那场挑战,朱祁铭心中半是期待,半是惴惴。
这时,皇上瞟一眼尚未醒神的郕王,微皱眉头,“郕王!”
郕王悠悠然举目四顾,片刻后打了个激灵。
“朕有些不适,你们各自回去吧。”
“老朽没记错的话,殿下只想获得一次议政机会,此后殿下是殿下,杨荣是杨荣,从此各不相干,是吗?”
杨溥眼中有分忧虑,但很快就被亲和的笑意所遮掩。他没有食言,果真第二次请旨将朱祁铭邀入府中,或许是为了彻底释疑吧。
吕希去文渊阁借阅相关文书副本,虽是奉旨行事,但此事毕竟与一个亲王相关,皇上的背书不一定保险,一旦事后被人察觉乘机大做文章,那也是极难收场的,故而杨溥为吕希留了一条后门,一切都在暗中进行,杨溥因此而担上了天大的责任。
“小王决不食言,小王不敢负杨阁老的一片苦心。”念及杨溥的豁达与担当,朱祁铭心存感激,但一想到常有阁臣随时查阅文书,吕先生不可将文书留在手上太久,若想不为人知,大概只有匆匆浏览一遍的时间,对此,杨溥也是爱莫能助,朱祁铭不禁暗自担忧。
唉,只能寄望于吕夕谣超强的速记能力了!
那边杨溥哈哈一笑,随即脸色一凛,“看来,对这些年来杨士奇、杨荣治国理政的所思所想,殿下甚是不以为然。”
这是试探么?是试探本王的议政能力么?朱祁铭把这样的试探归之于杨溥的好意,或许杨溥是担心自己届时露怯,导致一场破例邀亲王参议的廷议事后被证明完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吧。
“在小王看来,对如何化解大明的内忧外患,杨士奇、杨荣无所思无所想,一切都是在按部就班,应付而已!他们长于做事,短于远谋。”
杨溥微微一震,“愿闻其详。”
“杨阁老博学,小王不敢班门弄斧。当年,商鞅被秦孝公一纸《求贤令》引入秦国,先以无为而治的帝道相游说,次说以仁德治天下的王道,秦孝公均不为所动。最后,商鞅说以霸道,秦孝公大悦。在秦孝公看来,帝道、王道都不足取,唯有霸道可强秦。”
“商鞅变法?”杨溥凝目而思,“贵室受损,小民受益,这样的变法只有一次,后世不会再有了。想想唐代王丕、王叔文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不过是触动了一点小利而已,士大夫与勋戚便群起而攻之,变法或不了了之,或半途而废,殷鉴不远啊!”
这就对了,化解内忧与外患,并非无路可走,而是鲜有人甘愿自己的利益受损,去走真正的强国之路!
“不对!”杨溥猛然站起身来,“战国之时,大争之世,秦国有亡国之虞,不得不行霸道,而如今天下已是华夏大一统,今非昔比!”
“杨阁老,外有虎狼,把大明放在四海来看,如今依然是战国之时,大争之世!”朱祁铭知道,如今大明的处境与当年的秦国不同,大明毕竟没有多个足够强大的敌邦,若是被瓦剌这样的蕞尔小邦给玩残了,那就太悲催了!
“可是,天下大定之后,以法家的术治国,难以持久。”
“霸道难以持久,王道亦难以持久,好在儒家与法家有个共同的祖先,那便是春秋时郑国的子产!”
“宽猛相济?”杨溥落座,随即缓缓摇头,“殿下是想以此议政么?”
“不!明知不可为,小王何必虚议!”
“殿下想议何事?”
朱祁铭淡然一笑,“自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杨荣不是擅长边务么?”
杨溥眼中掠过一丝疑惑,或许在他看来,一个少年亲王根本就不可能在杨荣擅长的边务上击败杨荣。殊不知杨荣若在他擅长的边务上输给了一个少年亲王,那他还有何颜面呆在庙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