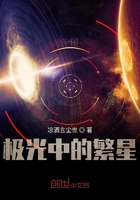精神上的创伤,终究需要精神来治疗。
海子的诗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我特意跑到书店想买一本他的诗集,很不好找,最后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来到了一个不起眼的旧书店。
“海子的诗集,有么?”我见到这个不起眼的书店,破旧不堪,老板坐在门口,一口接一口地吮着茶。
老板抬头看我一眼,笑了笑说:“有,自己找吧。”
我走进漆黑的书店,在破旧杂乱之中找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了那本诗集,很破,很旧,散发着霉味。
“多少钱?”我问道。
老板摇了摇头笑道:“拿走吧,很少有人来找海子了。拿去吧。”
我反倒不好意思了,坐在了老板一旁的椅子上,看着山海关湛蓝的天。
“这个季节,很少有游客来的。”老板说道。
我点了点头,笑了笑,没有搭话。其实我哪里算什么游客,我是一个病人,奔向大海只是想让那广阔无垠的海治愈我的心伤。
“是来看海子的么?”老板问道。
“不,我来看海的,昨天在沙滩上偶然听到了海子的诗,所以过来找找。”我答道。
老板不再说话,眯着眼,望着天,继续吮着手中的茶。
沉寂了许久,我有些坐不住了,站起来对老板道:“谢谢你的书。”
老板笑了笑,摆摆手说:“谢谢你陪我坐这么久。”
“你不要钱么?你开店也不容易。”我抚摸着手里的诗集,破旧的封面,透着八十年代的气息。
“这本书本来也不是我的,或许它就等着你呢。拿去吧。欢迎再来山海关。下次夏天来吧,夏天的海,很热闹的。”
我谢过了书店老板,转到了火车站,目的很简单,回家过年。
一路上翻看着海子的诗集,并不是每首诗都写完了,他仓促的离去留下了许多缺憾的诗篇,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读懂他。
或许他是我的前世,在今生指引我。
但是我读不懂海子的落寞,我只能听出他内心的嘶喊,那高贵魂灵渴望自由的喊叫,夹杂在八十年代禁锢的时空之中。
最终他突破了一切的禁锢,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
合上了书,闭上了眼,一觉醒来已经到了东北。
那冰与雪的世界。
在哈尔滨见了一年未见的朋友,去年回到这里,带着徐晴,为了照顾我的自尊心,徐晴和我演着情侣,引来朋友们的嫉妒。
今年再到这里,朋友还是朋友,哈尔滨还是哈尔滨,唯一的不同是我孤身一人,身旁缺少了那个俏丽的身影。
而那个名字,我甚至不敢提起。
海子的诗给了我莫大的勇气,我想要追求属于我的幸福,属于我的爱。
但是我的内心还是放不下许愿,依然对徐晴的最后一击感到耿耿于怀。
或者说,我是在惧怕着什么,惧怕一种我现在无法言明的情感。
我心里很清楚这种感觉,我也知道其他的可能都是借口,那种我无法捕捉到的情感才是阻碍我与徐晴真正的原因。
但是现在的我无法分辨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也无法明了我在逃避什么,我在惧怕什么。
朋友们追问我徐晴的下落,说那一见这一年都忘不了,早知道我没带回来都不招待我了,看我还不够恶心的。
我无力抗争他们的玩笑,唯有以酒谢罪,一杯接一杯,直到大家都喝多了。
这一年来,不光是我,所有人都成熟了很多,仿佛这一年是成熟的季节,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经历了一些“大事”,每个人都有满肚子的话想要说出来。
喝光了酒,说够了话,我离开了哈尔滨,坐着火车回家过年。
回到家里,父母依然健旺,但是两鬓依然多了许多的白发。
岁月不饶人啊。
母亲追问我的恋爱情况,父亲追问我的房子如何。
我疲于应对,唯有以一个有一个的谎言来应付他们。告诉他们我很好,在外面真的很好,不用为我担心。
在家住了几日,母亲忽然说道:“去看看你二哥吧,他过得不太好。”
二哥是我的远房亲戚,跟我年龄相仿,上初中的时候天天在一起,他比较厉害,很多人都不敢惹他,也捎带着不敢惹我,算是我的保护者。后来我外出求学,他初中之后就辍学在家,实在是提不起精神上学了,早早地结婚生子,开始了如同上一代的生活。
去年回来我见了他一面,还给孩子点压岁钱。他那个时候生活很好,嫂子体贴,孩子乖巧,跟我说话会不时地露出幸福的笑意。告诉我,他的地收成不错,黄豆今年涨价了。告诉我明年打算买一台车,不忙的时候可以出去拉些活。
我本来以为他可以生活得很好,倒是母亲这一番话,让我感到很意外。
在父母的零言片语之下,我听出了个大概。
孩子生病,农场的孩子都比较野,也没有人当个大事,弄点感冒药吃了就算。
但是愈发的严重,最后半夜都能咳出血来,二哥着急了找车去了哈尔滨,一检查是肺炎,感染面很大,伴随着高烧,已经有了合并症状,总之非常严重。
住了二十天的重症监护室,一天最便宜也要几千块钱,二哥把楼和地都卖了,又欠了一屁股的债,才算从哈尔滨领回了孩子。
对于农场的人,没有工作,地就是他们的生意,现在地卖了,为了还钱二哥在农忙的时候早上三点起来给别人铲地,一天五十,不算少,也不算多。
后来二嫂子带着孩子走了,说出去打工,不过有很多人都说就是嫌二哥没出息,跟别人跑了。
二哥依旧在家里,帮别人种着地,偶尔看到我的父母,会后悔一下当初没有上学。
“看病不能报销么?”我问道。
老爸笑了,狠狠地吸了一口烟道:“农民,靠天吃饭,谁管啊。吃吃喝喝都穷不了,就是别有病,有病要人命啊。”
我叹了口气,反倒是感到了上学的好来。
去看了二哥,跟着他喝了一瓶白酒,很便宜的白酒,十块钱一瓶。
辛辣之中带着苦涩,仿佛二哥的生活。
那一天他说了很多,大多是羡慕我的城市生活,后悔自己没有读书。
“那个时候我数学挺好啊,我记得有一次,就我作出了那道大题,唉。喝酒吧。”二哥狠狠地喝了半杯酒,却对自己的苦痛只字不提。
他不说,我也不好说,我知道男人终究是好面子的生物,现在这点薄面是他在我这个一年也不一定见得到一次的朋友面前唯一的保护,我不能残忍地捅破。
喝到最后,我起身告辞,二哥终究是心里难受,拉着我的手,几乎是咬着牙说道:“记住,男人不能没有钱,记住了。二哥跟你说,男人不能没有钱,否则你会一无所有。”
我的心里一翻腾,我仿佛找到了我最惧怕的那样东西,我仿佛看到了那丝一直晃荡在我的内心深处,阻碍我去原谅徐晴的幽灵。
离开了二哥家,冷风吹痛了面庞,我记得东北的雪,东北的寒冷,却忘记了这冰冷打在身体上是什么样的感觉。
小的时候,我上学要走十五分钟,每到冬天的时候,雪会没了我的大腿。农场的孩子都是野生的,父母只管给我一条棉裤,一个棉鞋,然后我便踏着半米深的雪,一点点丈量这十五分钟的路程。
而这一走,似乎走了二十年,今天大雪已经没在了我的胸口,我却不敢告诉别人,告诉他们我很冷,透不过气来。
夜晚睡觉的时候,恍惚间见到一个白色的身影,飘忽在我的面前,传来了二哥的声音。
男人不能没有钱,否则你一无所有。
然后又是许愿的声音。
你能给我什么?
然后是玛丽的声音。
难怪徐晴养着你。
然后……
我猛然惊醒,冷汗浸透了全身,我知道我最惧怕的是什么了。
我惧怕的是我的一无所有。
与徐晴无关,与任何人都无关,我不敢再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是因为我惧怕自己的一无所有。
我爱她,但是我能给她什么?
我让她养着我么?
自己的贫穷与对方的富足,恐怕是任何一个男人的噩梦,更何况她花的钱,曾经属于我最恨的那个男人。
我终于想明白了,但是我却颓然地倒在床上。
我无力改变这一切,无论是我的一无所有还是徐晴花着那个男人的钱,我都无力改变。
难道我要屈从下去么?屈从于这个冰冷的世界?
假装自己不在乎这一切,假装自己可以心安理得的让徐晴养着我,与她一起花着仇人的钱?
可是我在乎,我真的在乎。
我想嘶喊,用自己的声音冲破这个黑冷的夜。
终究还是无声地坐在黑暗里,如同一个陌生人一般看着自己的人生。
耳边传来了海子的声音。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