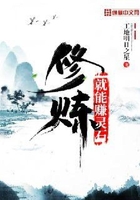今年的冬来的晚了些,却也仿佛带着彻骨的凉意,大臣们天天跪在殿外阻止这场典礼,可是白景亭的意愿似乎十分坚决,双方便是这般僵持着。百无聊赖,却怎么又被困在了这里,望着窗外纷飞的大雪,梨末心中不自觉有些心凉,信步走出庭院,只见一群婢子端着一篮子一篮子的梨花花瓣,便问道:“请问这是作甚?”
其中一个领头的婢子答道:“回姑娘的话,这些花本是苍落殿种下的,只苍落殿的梨花树凋谢了,便拾掇了这些梨花花瓣打算去丢了的。”
梨末见这些花瓣通体雪白,丢了着实可惜,便对那些婢子道:“这些花丢了着实可惜,若是姑娘们用不着,便给了我吧。”
领头的婢子瞧了瞧梨末,心觉这些花也无甚作用,这姑娘又是平阳国君身旁的,毕竟也算得上是贵客,便将那篮子递到了梨末的手中道:“既然姑娘需要,那便都给了姑娘。”说罢,对着身后的婢子示意了下,那些婢子便自觉放下了手中的花篮。“姑娘花瓣便给您放这了是否需要奴帮忙?”
梨末摇了摇手,便从自个儿屋子里唤了一个婢子,将这些梨花花瓣尽数拿到了厨房,又命人取了一个酒坛子来,便开始着手酿制醉梨酒酿,先将梨花花瓣一瓣一瓣清洗干净,将高粱谷子磨碎,蒸煮再与梨花一道埋入坛子里,随后再细细盖上一层梨花花瓣,密封,这一道道程序惊得厨房里的婢子侍从皆是瞪大了眼睛,这酿酒是自古便有的,可这般古怪的方法却是从未见过的。见梨花花瓣还剩了许多,她又将花瓣细细碾碎,部分带着一些羊奶上锅蒸煮,一部分和入了面粉里,准备完这些,她总觉得缺了一些什么,馅料,对,猛然想到了什么,便拿着那一坛子梨花酒往外跑。身后的婢子和侍从纷纷议论着这姑娘究竟是要作什么吃食,但是瞧着模样,还未成型,却已然令人垂涎三尺了呢。可当她跑出去的时候却被来御膳房取饭食的林嬷嬷撞了个正着,心觉好奇,便去回禀了苏浅落。
而白景亭在朝阳殿却异常的坐立难安,眼前竟不自觉浮现出他掐着那女子脖颈时,她微微闭起的双眼,以及她眼角那一滴缓缓滑落他掌心的泪滴,那温热却令他的心仿佛利剑刺穿一般疼痛,可究竟是为什么,即便是她,他也不该,绝对不该有的心思,可那脚步却怎么也管不住,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她住的小院,他想确定那女子究竟是否他想的那个人?却遍寻不见,便询问了殿中的一婢子,婢子道姑娘去了御膳房,他的心拂过一阵失望却又顿生了几分好奇,便朝着御膳房而去。
而此时苍落殿内一直盯着白景亭的侍从来报说是王上去寻了平阳国君带来的那个姑娘,扑了个空,现如今朝着御膳房的方向去了。
苏浅落听闻,一阵阵妒火在心底冉冉升起,握成的双拳能清晰听见骨节作响,却生出了一计,“去让婢子盯着她,再去瞧瞧王上到哪了?”林嬷嬷得了令,便派了墨瞳去跟着,只见梨末跑到了一座偏殿旁,在杂草从生的地上寻找着什么。
苏浅落听闻便换了衣衫去了御膳房,瞧了瞧锅子里蒸煮的白嫩嫩的豆腐一般剔透的吃食,再瞧着和了一半的面粉,嘴角不禁扬起了一阵笑意,林嬷嬷一个眼神,御膳房的人哪里再敢逾越半分,纷纷退了去,“郡主,已经准备好了,王上正朝着这里来。”苏浅落点点头,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却掏出腰间的小刀,一刀划破了自个儿的手指,殷红的鲜血顺着她白皙的皮肤一滴滴往下流,林嬷嬷看的直揪心,可那苏浅落面上却不曾有半丝苦色,像是没事人一般。
她细长白皙的手指开始揉捏那一团面粉,因着伤口,额间渗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瞧着有些痛苦的模样,林嬷嬷是自小瞧着苏浅落长大,知晓这孩子如今的不易,必须倚靠如今帝王才能在这宫中有一席之地,便自然是一心向着她的。
“落儿,你这是在做什么?”见到苏浅落这副楚楚的模样,面粉上还沾着她殷红的鲜血,发白的嘴唇格外憔悴,他的心顿时纠了起来,哪里还能想的起来方才来这里的目的,他握着她受伤的手,轻轻在上面呵着气,眼底尽是道不出的柔情和心疼。
“无妨的,毁了你苦心栽种的梨花,我心底很是愧疚,便想着为你做几道吃食的,怎么料到竟是这般笨手笨脚的,病了这许久,这般小事竟也做不好了。”说着,她竟流了两行清泪,而她的泪显然还留在了白景亭的心中,他一把拥过了苏浅落,将她紧紧护在了怀中,不断重复着,“对不起,对不起。”他的心在那一刻似乎完全消除了那些犹豫与徘徊,那些不确定,眼前的人是他的落儿啊,是他发誓呵护一世的落儿啊,他怎能再起旁的心思呢?是的,他要迎娶他的落儿做他唯一的王后,只有她才配与他并肩天下,他的心狠狠抽搐了下,暗自下了决定。
苏浅落哭得梨花带雨,好一会终究止住了哭泣,算算时间大约差不多了,便轻轻推开了他的怀抱,“我做了梨花酪,应是好了,便取了给你尝尝。”说罢,便伸手去取那滚烫的梨花酪,却不曾碰到便惊叫着缩回了手,倒是让白景亭的心再一次纠了起来,很是心疼。
“傻瓜,以后你想要的再不用你亲自动手,知道吗?”他体贴的言语,温柔的眉眼让人如沐春风,包括门外的人儿,他拿出了那碗梨花酪,微笑的嘴角恰似最月儿一般,舀了一勺,“很好吃,我的落儿做的什么都好吃。”四目相对的一对璧人,对着彼此笑得那般耀眼,仿佛身旁的人不存在一般,眼底只容得下彼此,只有彼此。
门外的红豆散落了一地,可散落的岂止是红豆呢,还有梨末那颗千疮百孔的心,她一路狂奔回了小院,跌跌撞撞,如同醉酒了一般,她将自己关在了房里,只有在黑暗里她才能够放肆的哭泣,原来那么久的坚强在见到他的一刻竟会土崩瓦解的这般彻底,怎么到了如今她才看清了呢?她的手心里还攥着那最后一颗红豆,曾经寻遍天涯想寻找一颗能够代替红豆的宝石,可是到了最后才发现怎么也替代不了,因为只有相思才是这个世上最入骨的。她将那一坛子醉梨酒酿埋在了枯树下,还有那一粒红豆,她嘴角挂着笑意,因为她知道再做什么都无用了。
沉沉地睡了过去,不知多久,多久,当她再次醒过来才发现自己居然被悬空挂在了悬崖璧上,这是怎么回事,疑问与恐惧瞬间充满了他的大脑,崖上却传来了对话声。
“你好歹也是一国之君,竟然以一个女子的性命相威胁,不觉得太过卑鄙了吗?”萧风绪眼中磅礴的怒气,若是此时手中有一把剑,他定然要一剑杀了白景亭,昨晚他接到一封密信和一根珠钗,才知道白景亭竟然抓了梨末要用她的性命来威胁他交出兵备图,他虽是又急又恼,但依旧是做了打算,悄悄叮嘱了池墨。
来到了崖边,瞧见昏迷的梨末只被一根细细的绳子那般悬空吊在了悬崖上,整个身子都已经脱离了崖壁,他几乎想要一剑杀了白景亭,可是此时他若是轻举妄动,梨末的性命定然是不保的。
“卑鄙?你偷取我国军备图,我能有你卑鄙?如今不过是物归原主,怎么你难道还要舔着脸霸占着那张图,却置那女子的生死于不顾吗?”白景亭并不想致那女子于死地,仿佛料定了萧风绪定然会为了她交出图纸的。
瞧着那越来越细的麻绳,萧风绪的心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悬在半空中,在火焰上被蒸煮一般的,“好,我交给你,你放她下来。”他从怀中掏出那张图纸,在空中抛出一个利落的弧度,便到了白景亭的手中,白景亭接过图纸,细细瞧了一番,脸上终究展开了释怀的笑意。
二人的对话一字一句皆是落在了梨末的耳中,这世上若是有比绝望更加深刻的,一定是生不如死。
“落儿,你的追光者是在唱给谁听呢?”“落儿,不论何时,记得我爱你。”纷飞的梨花似雪一般轻盈,在指尖旋转蜿蜒过岁月悠远的情意,最后落进了彼此的心底,依偎着两颗心忽远忽近的距离,温度却那般炽热,树下的他一袭素色的蓝衫,徐徐的花瓣自在零落他恍若仙境中的使者,一支白玉的笛子,一曲相思的词赋,眉眼间的愁绪尽数落在了她的眼底。自此她便再无法自拔,为他一次次飞蛾扑火,作茧自缚,悬崖下的风凌厉地吹着,几乎将她身体中的最后一丝温度尽数抽干和她那卑微到底的爱情。听着那绳子一点一滴断裂的声音,她终究缓缓闭上了双眼,一滴冰冷的泪划过脸颊,在风中消散和着她的心一道在风中消散,终于终于那绳子在空中发出一声清脆的撕裂,她的身子沉沉的开始下坠,终于解脱了,她的嘴角依旧带着苦涩绝望的笑意。
“末儿。”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划破了天际,下一秒她却感觉自个儿的腰间被一双大手环住,她猛地睁开了双眼,却对上了萧风绪那一双俊秀的眉目中道不尽的担忧,他抱着梨末的力道那般紧,那般紧,仿佛要将她融入自个儿的骨血里。
梨末的心仿佛再次开始跳动,为眼前的男子而跳动,“别怕,抓住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出事。”望着他的眼眸,她竟在那一瞬间想活下去,为了他而活下去,萧风绪一手抱着梨末,一手去抓崖壁上的藤条,不住下降地藤条和环抱住梨末的力道,几乎让他用尽了全身的内力,直到快到悬崖底部的时候,他终究支撑不住,摔了下去,可身子却还替梨末挡着撞击的伤害。
悬崖上的白景亭望着那一根断裂的绳子和萧风绪跳下去那一瞬间,若是仅仅用后悔两个字断然无法形容,为何,为何他的心在她掉落的那一瞬间仿佛跟着她一块掉落了下去,他的心好痛,仿佛那些经年深埋的痛楚被连根拔起,他的眼前再次浮现苏浅落中箭身亡的场景,他怀抱着苏浅落竟流不下一滴泪水,因为心空了,死了。如今当她下坠的瞬间,他竟会有了相同的感受,为什么,为什么?他的心不断在质问着自己。他嘶吼着对身旁的路随风吩咐道:“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萧风绪,你醒醒,你这个笨蛋,你这个无赖,你是要我对你的死心怀愧疚吗?告诉你我天生心狠,绝不会的,你给我醒过来听见没?”望着萧风绪那张英俊的面庞上划破的血痕,她的心狠狠抽搐着,只剩下唯一的一个念头,那就是不能让他死去,决定不能。
她环顾着四周,费劲了气力将他挪进了一处山洞中,当机立断便去寻了几味治疗外伤的草药,撕破了外衫细细替他包扎着伤口,她眼底噙着泪水,那般苦涩的泪水滴落到他干裂的唇瓣上,他竟仿佛有了知觉,“水,水…。”梨末凑近听着,见他要水,便四处望了一遍,最后在一处崖壁的角落,用叶子接了一些水,可他根本喝不进啊。
梨末将水一口饮下含在嘴里,对上他凉薄的唇瓣,清凉甘冽的水顺着萧风绪的喉头一点一滴往下渗,他似乎感觉到了唇瓣处的柔软和温度,缓缓睁开了双眼,却见那女子正对着他的嘴喂他,他的嘴角缓缓咧开,竟不舍得让她离开,他一用力将她拥入怀中,让她柔软的唇瓣更加亲密地贴着他的唇形,梨末的眼睛顿时睁得老大,几乎被惊吓到,她一把用力推开了萧风绪,才发现萧风绪吃痛的表情,又生了些悔意,可谁让他这般无赖呢?
“醒了还占我便宜,你是觉得你现在还有气力吗?是觉得你这般样子我便不忍心吗?”梨末瞪着双眼道。
萧风绪委屈巴巴地睁着双眼,压着嗓音,像是一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我救了你呀,你不应该以身相许的吗?”这受了伤竟然还没脸没皮的样子,梨末竟是又好气又好笑。
“许你个大头鬼,我又没让你救我,死了倒是清净。”她转过身子,瞧着那高耸的崖壁,一阵酸涩划过胸口,萧风绪艰难撑起身子,挤出了一阵笑意,“丫头,跟我走吧,让我护你一世周全。”他的脸那般贴近,几乎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声,梨末的心突然跳的那般快速,这是怎么了?“一世周全”多么嘲讽的四个字啊,这话曾经那个人也这么说过,可最后呢?
他的表情那般严肃,他,他是认真的吗?“你又在说什么胡话了,受了伤还不安分躺着。”梨末躲避着他炽热的目光。
他却强掰过她的身子,让她面对着他,“丫头,我是认真的。”
梨末笑了,徐徐推开他的手,轻声道:“莫要轻易许诺因为这世间所有的诺言都不会成真的,我也是认真的。”她嘴角扬起苦涩的笑意,“躺着吧,莫要为了无谓的事而浪费了你的气力。”她承认,他为她跳下来的那一刻她的心再次为他跳动了,可是她的心已然如枯木一般死去,再不会发芽结果,又何苦给他无用的期望呢?
“我,我知道你现在还无法接受,无妨,我会等你的。”还不曾等到她开口拒绝,他便快速转移了话题,“今晚吃什么?我可是个病人呢?”一脸无辜的表情,还真是让梨末哭笑不得,又拿他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