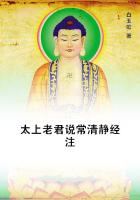导演在研读剧本的过程中,可能在某个地方,或者在某场戏、某个段落、某个细节上,触发或引起自己的创作冲动,产生许多有关创作的联想,这是极其可贵的。它有利于将来对剧本的丰富和加工,应随时记录下来,以帮助和推动对未来影片的创作构思。
毋庸讳言,许多剧本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即使是根据名著改编的剧本,也会存在这样或那样不尽如人意的问题。这都要导演在分析研究剧本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加工和改造。即使到了拍摄阶段,甚至是后期阶段,这项工作还要不断地进行。因此,导演对剧作的主观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导演要把自己的个性、喜好、兴趣、情绪渗入到剧本中去。导演可以通过对剧本的感性认识和理性分析,不断丰富和改进剧本,以期达到精益求精,为未来的影片奠定良好的基础。
导演在研究和分析剧本时,切忌搞学究式的评论,搞繁琐的考证,这对导演创作毫无用处。
导演如何分析剧本,虽无一定之规,但要从实际出发。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把焦点对准人物
在银幕和屏幕上塑造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向来是导演关注的焦点和苦苦追求艺术的理想境界。剧本必须为导演提供人物形象的基础。
历史的经验证明,凡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名著,能够传世的佳作,无不和作品中塑造的那些熠熠闪光的人物形象有关。假如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苍白无力的,是焦点不实、模糊不清的,其作品也将如过眼云烟,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不下任何痕迹。
经典作品之所以能够传世和不朽,就在于它能让人记住作品中的人物。例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贾宝玉,鲁迅笔下的阿Q和祥林嫂,莎士比亚剧中的哈姆雷特和奥瑟罗,巴尔扎克书中的高老头等都给读者和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甚至是难以抹去的记忆。
电影亦是如此,例如卓别林塑造的那个既可笑又可怜的小流浪汉,至今仍然被人所称道,其原因就是功在人物。
电影《秋菊打官司》能为国人接受和称赞,并在国际上获奖,就在于秋菊这个人物是个性化的人物。她为了讨个说法,不怕辛苦,不畏权势,从乡告到县,又从县告到市,在农村妇女中,这种精神是非常少见的。由此,才使观众对这个人物产生了兴趣,并被这个人物所吸引。
法国电影《杀手里昂》之所以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就在于它揭示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杀手给人的直觉就是冷血、残酷无情、心狠手辣。但杀手里昂不一样,他除了以杀人谋生之外,还有人性的另一面:他爱花,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爱孩子,甚至舍命相救,让人看到他胸腔里还有一股热血。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人,也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能感染人、打动人,不会在观众的头脑里迅速消失。
关于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性,就连一贯注重惊险场面和华丽包装的好莱坞电影也懂得这个道理。《阿甘正传》这部电影就是以写人为主的,而且是写一个弱智人的生活与经历,并一举战胜了《真实的谎言》,夺得了1995年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六项大奖,而且在美国1994年电影票房排行榜上雄踞首位。可见观众并不只是要刺激,看传奇故事,看枪战打斗,看华丽包装,而是要看你的影片能不能塑造出一个真实可信的人物,并能从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一些对人生的启迪和感悟,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阿甘正传》的成功秘诀正在于此,它既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又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尽管它的投资低于《真实的谎言》,但收益却高于它。可见塑造人物形象对于影片的成功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关于塑造人物形象的问题,从理论探讨到创作实践呈现出多种趋向:有的因循传统观念,有的开拓现代意识;有的主张浓缩,有的倡导淡化;有的强调直观,有的探索折射;有的采取塑造,有的运用剖析。尽管各自的观念不同,方法各异,但还是围绕人物进行的。虽有争论,但焦点还是集中在人物身上。
可是近年来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银幕和屏幕上,人的形象越来越淡化,越来越朦胧。有些人物常常被刀光剑影、硝烟血迹遮住了;有些人物则在珠光宝气和华丽的包装中被湮没。人物仿佛被蒙上了一层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让观众看不清楚。
诚然,过去那种把人浓缩成人干、人精,把正常的人提纯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圣人,以及“高、大、全”式的非同寻常的人,显然是不妥的;然而极力淡化人物、稀释人物,把人抽象得没有了血肉和筋骨,飘忽不定,如在云里雾里,仿佛丢了魂儿的人,也是不可取的。
从电影的历史来考察,人物形象被冲击也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他曾经先后受过三次大的浪潮的冲刷。
第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先锋派。他们只注重影像造型,不要故事和人物。影像造型便是一切,于是机械舞蹈、线条运动充斥画面,成了主体,而人物却被挤出了银幕。
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出现。它强调纪实性和纪录性,否定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并大量选用非职业演员扮演人物。人物成了演绎故事的陪衬和符号。
第三次则是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的兴起。意识流和生活流现代派小说入侵电影,于是非情节化、非人物化,成为现代派电影的主流。例如法国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影片中的人物甚至连姓名也没有,只用X、Y来代表。尽管这部影片在艺术领域做了大胆的探索,但人物却被淡化了,都像是一些虚拟的人,模糊、朦胧,让观众难以理解和接受。
这类影片之所以不能为广大观众所接受,就因为它忽视了人物在影片中的重要作用。人物淡了,情节自然也就淡了。因为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历史,这一艺术创作规律还是在起作用的。我国导演谢晋曾经说:“我觉得对电影来讲,只是画面好、音乐好,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看它对人物刻画得怎么样。人物留在观众心里,这是对一部影片的最高评价。”因此,在剧作中观照人物,无论对初学者,还是对卓有成就的导演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现实生活中,人最常见,也最难写。人际交流最频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复杂。每个人几乎每天都要接触许多人,办事,谈话,争执,动感情,互相帮助,关怀,又互相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其中有熟人,也有陌生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职业和长相,也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和脾气。在接触中,我们似乎从没有放过对人的观察和体验,比如审视对方的外貌,捉摸对方的心理,体察对方感情的细微变化等。即使这样,真正能把人写好、表现好的作品仍然不多见。
因此,导演在分析剧本中的人物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要关注剧中的人物形象是立体的还是平面的
在银幕和屏幕上塑造人物形象,不能单线平涂,只画个平面。观众希望看到的是立体化的人,所以剧中的人物形象应该是从多个侧面来描绘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形象才会显得血肉丰满,具有立体感。
关于这种多侧面描绘人物的方法,早在我国传统文学及理论中即有所运用和论述。如《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六十九回开始总批中写道:“写凤姐写不尽,却从上下左右写。”即属此种论点。所谓“从上下左右写”的方法,也就是多侧面描写人物的方法。
王熙凤是曹雪芹笔下刻画得一个个性十分鲜明的人物形象。她之所以被描写得非常成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在于作者把她放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处在各种矛盾冲突的浪尖上,从“上下左右”去刻画她的性格,她的为人处世的各个侧面,所以才显示出人物形象的立体感。例如,她对上,在贾母跟前,她想方设法讨老太太的欢心,投其所好,百依百顺,由此成为贾母的宠儿;她对王夫人,则是信得过的当家人和帮手。她对下,对弱者,如林黛玉、尤二姐等,则是笑里藏刀,用软刀子杀人,让人难以觉察,又无从挑剔。她对左右,如对和她争权的邢夫人、赵姨娘等,则是玩弄权术,决不手软;对于贾琏、贾芹等,则是控制和利用。总之,透过她和上下左右人物的交流、对比、衬托,把一个年轻漂亮、富有才干,且左右逢源、利欲熏心的凤姐写得玲珑剔透,令人叫绝而又铭记不忘。
在“脂砚斋”点评中还指出:“写秋桐极淫邪,正写凤姐极淫邪;写平儿极义气,正写凤姐极不义气;写使女欺压二姐,正写凤姐欺压二姐;写下人感戴二姐,正写下人不感戴凤姐。史公用意非念死书子之所知。”
上面提到的秋桐与平儿都是贾琏的侍妾,写秋桐与凤姐争风吃醋的“极淫邪”,正是烘托凤姐的“极淫邪”,写平儿息事宁人的“极义气”,正是衬托凤姐的“极不义气”。凤姐智赚尤二姐到贾府之后,就派了心腹使女去侍候二姐,实际上她是凤姐派去的坐探,监视二姐的一举一动,所以说“写使女欺压二姐,正写凤姐欺压二姐”;反之,“写下人感戴二姐”,也正好反衬出下人不感戴凤姐。以上许多互相对比、互相衬托的写法,也就是从各个侧面来写凤姐,以便把人物表现得更具立体感。
以上“脂砚斋”对《红楼梦》的点评,也可以作为我们对电影剧作中人物分析的借鉴。
这种多侧面、立体化的塑造人物的方法,在电影中也曾多次运用过。早在1941年美国电影导演奥逊·威尔斯在拍摄影片《公民凯恩》时,就运用了这种方法。
《公民凯恩》是威尔斯自编、自导、自演的代表作。自1952年以来,在国际历次评选电影诞生后最佳影片中,它均列10名之内。可见它在影坛上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该片无论在内容的表述上,还是在叙事结构以及电影语言的运用上,都具有创新、实验的独特性。
就塑造人物而言,导演对主人公凯恩的描绘,采用了多侧面、多视角的表现技巧。即同一段经历由不同的人回忆、叙述来展现。在影片中,通过记者汤姆逊以凯恩临终时的遗言“玫瑰花蕾”为线索,对凯恩其人做深入查访。经过他对与凯恩关系非常亲密的人物,如凯恩财产的监护人、银行老板兼国会议员赛切尔,凯恩报社的董事长伯恩斯坦,报社的专栏记者李兰,凯恩的第二任妻子苏珊,凯恩的老管家雷蒙特等的访问,通过他们讲述对凯恩不同阶段的回忆,展示了凯恩性格的各个侧面,表现了一个性格复杂、多层面的,具有立体感的人物形象。这不仅为这部影片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也为在电影中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开辟了一条新路。
描绘人物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塑造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让人物在银幕或屏幕上活起来,也在观众的心中活起来。
2.要关注人物动作
电影和电视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表现运动,要求人物富于动作性,要求将人物放在动作中展示其思想、情感、心理和性格特征,以增强人物的鲜明性和生动性。
前苏联著名导演和教育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在舞台上需要动作。动作、活动——这就是戏剧艺术、演员艺术的基础。‘戏剧’一词在古希腊文字里的意思是‘完成着的动作’。”随后他对动作又做了补充阐释,把动作分为外部动作和内部动作。他认为一个人在舞台上坐着不动,还不能确认他就是没有动作。他说:“有时候形体之所以不动,是由于强烈的内部动作所造成的,这种强烈的内部动作在创作中特别重要而有趣。艺术的价值就取决于这种动作的心理内容。”同时,他还对动作提出了基本要求:动作“必须是有内心根据的,合乎逻辑的,有序的,而且在现实中是可能的”。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关于对舞台动作的论述和阐释,同样也适用于银幕或屏幕,因为人的行为的本质就是动作。在生活中,人总是通过各式各样的动作来完成某项任务或达到自己的愿望和目的。因此,无论是戏剧导演,抑或是影视导演,都必须为所要表现的人物寻找到合乎逻辑和顺序的、具有心理根据的、含有目的性和真实性的动作。凡是具有积极动作性的人物,才会在银屏上显得生机盎然,栩栩如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人物性格的显示,必须和人物动作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几个人都去做同一件事情,但怎样去做,则各不相同,各有各的心理根据。有的人是心甘情愿地去做;有的人是迫于无奈地去做;有的人则是违心地去做。
恩格斯说:“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所谓“做什么”,是指人物的外在行为,即外部动作;而“怎样做”,则指人物的心理状态及其完成任务的方式,即内部动作。外部动作与内部动作的交织融合,则显示出这一人物区别于其他人物的独特性格,也就是艺术中的“这一个”。
黑格尔曾经说过:“能把个人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是动作,人的最深刻方面只有通过动作才见诸实现。”这就最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人物性格是通过动作显示出来的。因而,剧本要想最充分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就必须为人物找到恰当的、为这一人物性格所独具的动作。而导演在分析剧本中的人物时,也要看剧中的人物动作是否具有这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