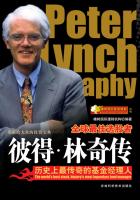似这等草菅生灵,于心何忍,于理何曲,于法何赦!为解干旱,也为减轻你们的罪愆,本县命令你们,立刻兴云播雨!否则,本县将按大唐律令,严惩不贷!”话音刚落,微风徐起,不一会儿,乌云翻卷,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百姓们沸腾了,他们在大雨中跳着蹦着唱着闹着。罗贯仰头看看天,俯身看看地,仿佛听见土地“吱——吱——”地喝水声,他的心里畅快啊。他放下令旗,跪在泥泞的土地上,恭恭敬敬地朝天磕了三个响头!百姓们也学他的样子,跪下来,恭恭敬敬地朝天磕头。
红鼻子打趣说:“打那以后,大家都说:‘天不下雨你甭怕,罗爷是龙王他二爸!’”逗得罗贯也笑了。“什么二爸?它们吃在洛阳,住在洛阳,应该给洛阳百姓办事!可惜啊,龙王也得吃喝!去年,咱们没钱,没办祭品,今年,又是没钱,它们再也不会白来喽!”里正搔搔头,“也是,没利的事,谁也不会干。可是,现在,青黄不接的,老百姓手头没钱,还真办不起个祈雨仪式。”罗贯问:“咱们村离洛河多远?”花白胡子说:“七八里。”瘦老汉说:“远倒不远,就是原来的水渠都坏了。”
“怎么坏的?”罗贯问。里正说:“大部分是年久失修。有些人也爱占小便宜,把渠刨的种了地了。”花白胡子说:“罗老爷,修渠的事,您就别想了,要经过好几个村,人家能同意吗?”罗贯说:“能不能,我也得去说。他们也要浇麦子呀!……”
话还没说完,一个年轻人跑过来,“里正叔,叔,快,快!……”里正问:“耗子,别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那个叫耗子的说:“快,快去!打猎,打猎的,人马,人马,都跑到麦地,去咧!把,麦子踏,踏倒,一大片,一大片!”罗贯一跃而起,拉着耗子就跑。董刚、关梓和里正紧跟在后,几个老人也火急火燎地追过去。
他们还没跑到地方,就见烟尘滚滚,一队人马风驰电掣地刮过来,像龙卷风,像洪水。所过之处,刚秀穗的麦子,有的断了头,有的折了腰,有的连根拔起,七长八短,参差不齐,像蝗虫扫过似的,一片狼籍!罗贯丢下耗子,一边跑,一边大喊:“停下,停下!”谁听他的!队伍仍然像倾泄的山洪,漫过麦田!
那是谁?一身明黄!皇上?是皇上!罗贯迎着马头疯一样跑过去,跑过去,象飞蛾,无畏地扑向烈火。马队根本就没看有人向他们跑来,依然疯狂地卷过来,卷过来,身后,尘土飞扬,盖住了半边天。董刚、关梓几个惊恐地大喊:“老爷,危险——危险——”罗贯刚到马前,就被马撞了个跟头,裹到马蹄下面。几个老人惊恐地“啊”了一声,回过身子,不敢看眼前的惨景。说时迟,那时快,罗贯就地一滚,躲过了铁蹄,一个鲤鱼打挺,飞快地抓住马缰绳,马,把他拖出五六丈远。马见是个生人,突然直立起来,仰天长啸,差点把皇上掀下马来。皇上扔了弓箭,两手勒紧缰绳,身子紧紧贴在马背上。马,落下了前腿,站直了,皇上一挥马鞭,打在罗贯脸上,脸,立即泛出一道血印,渗出点点血珠,像雪地里一枝含苞的红梅。
罗贯没工夫擦血,他急忙跪下,“下官罗贯,参见皇上。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混帐,你干的好事!”景进扬起拂尘又要打,敬新磨伸手拦住。罗贯再拜:“下官该死,冲撞了圣上龙驾!”皇上受了惊吓,有些恼羞成怒,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知道该死,跑这儿干什么!”罗贯哭着说:“圣上,您看看麦子,麦——子!”皇上回头扫了一眼:渐渐散去的灰尘中,几个老人,有的傻站着,呆呆地盯着麦田。
有的蹲在地头,双手抱着头,身子微微颤动。有的满眼是泪,抚摩着麦子的断茬。
有几个,拿着断了的麦杆,往倒在地面的麦杆上接。那手,颤抖着,两个断头,怎么也对不到一起。远处,成群结队的农民,有大人,有小孩,有男人,也有妇女,朝这边跑过来。景进瞅了皇上一眼,指着罗贯骂道:“你想干什么?拿百姓压皇上?
要不是皇上东荡西杀南征北战,百姓有好日子过?皇上打猎,打猎,也是为了——
百姓……”没等景进说完,罗贯哭着说:“现今青黄不接,百姓吃树皮,啃草根,没有怨言,就指望着麦子救命,也为皇上充实军粮。如今麦子正在秀穗,皇上怎么忍心践踏?似这样下去,百姓何以为生?我们这些小官怎么给百姓说?为民父母,怎么能这样对待百姓?请皇上先赐臣死,再去打猎不迟!”皇上本想赦免罗贯,听了罗贯的话,气得脸色铁青,“你,你,你竟敢拿百姓压朕,还要,要挟朕,赐死,好,好,朕,朕成全,成全,你——”“呔”,敬新磨喊了一声,翻身下马,指着罗贯厉声喝道:“罗贯,你知罪吗?”罗贯一梗脖子,“臣不知罪!”敬新磨说:“你身为县令,难道不知道我们皇上爱打猎?为什么还要煞费苦心,教百姓种地,纳税,充军粮?你应该让百姓饿着肚子,让军队饿着肚子,空出地来,种草,种草,你知道吗?再养几十头麋鹿,狗熊,野兔,山鸡,供皇上打猎!你,你都干了些什么?还说你不知罪?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说完,敬新磨也跪到皇上马前,“臣恳求皇上,让臣代皇上处死罗贯!”皇上一听,脸儿由青转白,又由白转青,眼睛在敬新磨和罗贯的身上挪来挪去,很长时间没说话。敬新磨和罗贯跪在马前,头抵着手掌,一动不动。皇上摆摆手,喝令打猎的队伍退回洛阳。那些兵丁像盛开的玫瑰被黑霜打了一样,蔫蔫地,不愿意退回。皇上大吼道:“磨蹭什么?耳朵聋啦?”
他们才怏怏地勒转马头,没精打采地原路退回。敬新磨拍拍罗贯的后背,起身上马,追皇上去了。只有罗贯还傻傻地跪在地上,半天不知道起来。众位乡亲跑了过来,喊道:“皇上早走啦!”花白胡子和红鼻子搀起了罗贯,心疼地为罗贯擦脸上的血。罗贯挡开两位老人的手,蹲下身来,心疼地看着折断的小麦。
五
猎没打成,皇上的心里积着火,把个舌头、嘴唇都烧得血红血红的。看看外边的天,一丝云彩也没有。热风一起,刮得树叶刺啦刺啦响,点火就着。昨天,太阳下山了,唐皇到御犬房,那些猎狗也没劲理他,趴在湿地上,舌头吐得长长的,只顾喘气。今天一早,太阳刚一露头,就烤得唐皇没地方钻,他要景进给朝门外挂上歇朝牌,就手摇绢扇,上了五凤楼。没有多大一会儿,刘夫人轻稠薄缎飘了过来,“热死了,热死了,找个清凉地嘛!”唐皇说:“你说哪里清凉?朕都走了四五个地方了,这算最凉快的地方。”刘夫人说:“妾给陛下弹曲《清凉散》吧,保证清凉爽心。”唐皇摆摆手,“得了吧,热得火烧一样,你弹的曲子还不是火上浇油!”刘夫人撇着小嘴说:“陛下不听也就罢了,埋汰贱妾干什么?”唐皇忙换了副笑脸,说:“夫人,别生气,我是热糊涂了,你弹的曲子,还能不动听?”刘夫人心里甜甜的,嘴上仍旧不饶人:“嘴里不说心里话!现在啊,您要我弹,我还不弹了呢。”“不弹就不弹。天热,一动一身臭汗,歇着吧。”唐皇关切地说。静了不一会儿,刘夫人又嘀嘀嘟嘟地说:“听说昔日长安,亭台楼阁成百上千,大明宫、兴庆宫高耸入云,今日的皇宫竟不如当时的公卿府第……”李从袭说:“这还不容易?咱们也盖它成百上千不就完了。”景进说:“怕没那么容易吧?”刘夫人问:“怎么不容易?”景进说:“租庸使常常哀叹用度不足,郭崇韬也为此事愁眉不展,陛下就是想盖一座两座楼,我看,都难,更别说成百上千!”刘夫人说:“有什么难的?不就是个银子吗?我去要!孔谦,还是比较听话的。至于郭崇韬嘛,”刘夫人看看唐皇,“就得有劳圣上的大驾了。”唐皇撩起锦帕擦了擦汗,说:“朕去说,又不要他拿银子。剿灭了梁贼,天下太平了,朕连个避暑的地方都没有,这皇上还当个什么劲!”说完,对景进说:“传租庸使孔谦。”
孔谦来了。唐皇问:“你热不热?”孔谦瞅瞅唐皇,短裤绸衫,四仰八岔地卧在竹躺椅上,敞胸露乳,旁边两个宫娥,不停地摇着扇子,忙说:“热,当然热呀!”说着,抬起袖子,擦擦脸。刘夫人说:“你还知道热呀!你看看,把皇上热成什么了?”孔谦诺诺连声。“找个风水先生,在皇宫寻个清凉处,盖栋避暑楼。”
孔谦的口张了几张,没说话,也没动。刘夫人问:“你,没听懂我的话?”孔谦的口又张了几张,还是没说话。“嗯——”刘夫人上身向前微微一倾,“孔大人呐,租庸使当的不耐烦了吗?”孔谦开口了:“可是,可是……”“我知道,你缺银子。要不缺,还要你当租庸使?随便逮个六只脚的蛤蟆……”孔谦搔搔头,迟疑片刻,转身要走。唐皇开口了:“悄悄的,不要声张……”
洛阳县衙。罗贯焦急地转来转去,口里念叨着:“这老天,不下雨,把人急死了!”徐放宜手端茶杯,跟在罗贯屁股后边,“老爷,喝点吧。天不下雨,谁也没办法……”董刚慌慌张张撞进门来,“老爷,不好了!”罗贯急忙迎上去问:“说,什么事?”“外边,几十个人打起来了,要出人命!“罗贯什么也没说,随董刚跑出衙门,就见街上打得一塌糊涂,七八个人已经躺倒在地。罗贯大声喝道:“住手!
住手!”近处的几人停下了,稍远的十几个还打得热闹。关梓跳过去,一把夺过木杠,来了个蛟龙点水,把三四个扫倒在地,众人才停了。罗贯问道:“为什么打架?”“你问他们!”一个公人打扮的说。“还问我们?你看看,你们把路堵成了什么样子?不让人过,还敢打人!”一个吊稍眉的人指指南边。罗贯朝南一看,果然有七八辆大车,横七竖八堵在路上。全是一色的松柏原木。那原木,有两三搂粗,十几丈长。“你叫什么名字?给谁家拉的?”罗贯问那个公人。“小人胡滦。给张大人运的原木。”“张大人?”罗贯觉得奇怪,能用这么多原木的,不是皇上,至少也是个大官。可姓张的大官,除了张全义、张宪,再没有谁了,而这两家最近并没盖房子。便又问“哪个张大人?”“汝州防御使张继孙。”“汝州防御使?他的义父,是不是张全义?”罗贯问。“是,是我家东平王……”“嗯——”“哦,是我家太尉,河南尹。”罗贯瞪着公人,“为什么堵着大路?狗仗人势?”“是,是,是他们,先出手打人!”罗贯更奇怪了:谁那么大胆,竟敢与河南尹家争路,还率先出手?他走过去,一眼就看到十几辆大车,用苫布苫着。罗贯过去,掀开几个车的苫布,全是青石柱础。罗贯问那个吊稍眉的人。“给谁运这么多柱础?”“你最好别问。”罗贯拉长了声音:“我要是还想问呢?”吊稍眉也拉长声音:“那你就问吧!”“你是不敢说,还是不屑说?”吊稍眉叉开两腿,两只胳膊横抱胸前,慢吞吞地说:“我是不敢说。”“不敢说也得说!”“我怕说出来吓破你的狗胆!”罗贯冷笑几声,说:“我是饭吃大的,不是狗吓大的。您,说说?”“皇上!”吊稍眉双手抱拳,向上一拱。“皇上?”罗贯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会儿,青黄不接,民力枯竭,皇上也在大兴土木?”关梓听言,在罗贯耳边说了几句,罗贯回过神来,和董刚几个分头劝说两方,“大路朝天,各让半边”,先把东西送回去,再到县衙处理纠纷。两方都降了火,同意这么办。等他们的车队走过,罗贯使个眼色,董刚、关梓分头暗暗跟着两队。
础石果然是给皇上拉的,听说是建避暑楼;原木正是给张继孙拉的,据说是盖府第。罗贯忙把皇上建避暑楼的消息报告郭崇韬,郭崇韬不信,又派亲信王鼎丞查看,还不相信,等亲自出马,才见几千工匠,干得正欢,郭崇韬坐不住了,心急火燎地上了皇宫。唐皇见郭崇韬来了,把短衫掩掩,在竹躺椅上欠欠身,吩咐看座,上茶。郭崇韬说:“我就站着。茶,我也不喝。”唐皇笑笑,说:“天,跟火炉子一样,爱卿不热?坐下,喝口茶,消消暑,也不影响说话嘛。”郭崇韬坐下,说:“今春至夏,两河干旱,别说军粮不充,百姓糠菜也吃不饱。希望陛下暂且停止营造,以待丰年。”唐皇一脸茫然,“爱卿说的什么,朕怎么听不懂呀?”郭崇韬说:“陛下不必隐瞒,为臣接到罗贯报告,也不相信,亲自跑了一趟,业已证实,陛下正命人建造避暑楼。”唐皇与刘夫人对视一眼,说:“有这等事?我们怎么不知道?”说完,扭头对景进说:“派个人,查查,谁在盖楼。”回头又对郭崇韬说:“朕的确不知道。派人查查再回答你,怎么样?”郭崇韬说:“圣上,昔日被甲乘马,亲当矢石,与梁贼拼杀河上,您觉得暑热吗?”“那时候,前有强敌,性命攸关,就算有酷热,哪里还顾得上呢!”“圣上明鉴”,郭崇韬说,“今日,圣上以为,外患已除,海内宾服,所以闲坐珍台闲馆之内,也香汗湿衣。圣上难道忘了,契丹在北,王衍、李茂贞在西,高季兴等人在南?难道忘了,今春连日不雨,百姓盼雨心焦?不说外患,只要老天继续不雨,民心也会浮动。陛下,要知道,创业容易守成难啊!”
“这个道理,朕早就知道。”“历代皇帝,哪个说他不知道?隋炀帝不知道,还是陈后主不知道?他们都知道!可他们……”唐皇的脸色有点愠怒,“他们都身死国灭,是吗?”“皇上明鉴,”郭崇韬也看出了唐皇不高兴,可他还是止不住要说:“可他们,还是明知故犯,身死国灭,又能怨谁?还在皇上继晋王位的时候,下官就引用国朝太宗的话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皇上难道不记得了?如果忘了,下官再说一遍:百姓,是国家根本,抓住这个根本,尸居衽席之间即可以治天地;忘了这个根本,你纵有泼天本领,也逃脱不了身死国灭的命运……”“放肆!”景进喊道。唐皇伸手止住了景进,说:“郭崇韬,你把朕当成什么人了?你不觉得,你说的有点过分吗?朕念你一片忠心,也不和你计较,你,告退吧!”郭崇韬听唐皇如此说,明白再也没法说了,便施了一礼,退出了五凤楼。
看着郭崇韬的背影,刘夫人说:“陛下,对郭圣人,你可要言听计从哇!”唐皇在鼻子里哼了一声。景进没有说话,从宫娥捧着的盘子里取过一方湿锦帕,替唐皇擦了擦汗。李从袭说:“郭枢密的府第,比皇宫还宽敞疏朗,自然体会不到皇上的酷热了!”唐皇白了一眼李从袭,问刘夫人:“你见过孔谦没?盖避暑楼的银子……”“见过了”,刘夫人说,“银子,现成的没有,他正在加紧筹措。不过,他还说了个主意,倒是蛮好的。”唐皇问:“什么主意?你说说。”刘夫人说:“把各州县和方镇上交的租税、贡品混在一块,再一分为二,一份叫做外府,交给租庸使衙门,充作公用经费,一份叫做内府,由妾掌管……”“好办法,好办法!孔大人不愧是鬼才呀!”景进抚掌称赞。唐皇的眉头攒成一个疙瘩,像个坟丘,“这样以来,岂不是……”“岂不是什么?化公为私?”刘夫人说:“你是皇帝,天下都是你的,有什么公的私的?”刘夫人停了一下,好像给孩子喂水,待他把这口喝下去,再喂另一口。“妾掌管的那一份,你用起来不是更顺手?宴游呀,田猎呀,或者给赐左右呀,再不用费神跑到租庸使府调拨了……”唐皇想想,这个理也对呀!紧锁的眉头徐徐绽开了。“可是,今春没有下雨,租税收不上,无论怎么分,还不都是空的……”“这还不好办?祈雨呀!”“你以为,龙王是你们家儿子?就是儿子,也不一定听老子的话!”景进插了一句。李从袭说:“龙王再大,也有人管他哪。”大家的头都转向李从袭。“我有一个朋友,叫杨千郎,能降伏天龙,命风召雨……”“你见过?”景进问道。李从袭说:“没见他降伏天龙,命风召雨,却见他玩过一些小把戏。”“什么小把戏?”刘夫人兴冲冲地问。李从袭说:“那天,奴才去街上采购,走到宣仁门,看见一群人把街道围得水泄不通,奴才钻进去。见一个人须髯飘飘,颇有仙风道骨。他面前有一张桌子,桌上什么也没有。他口中念念有词,右手朝空中一抓,就抓来几颗红枣。”“这还奇了!”“还有更奇的呢!”李从袭说,“他把那几颗枣交给旁边一个看热闹的人,让那人牢牢地攥在手中,他又念动咒语,往那人拳旁一晃,枣就到了他的手里。可那人的手还紧紧攥着!”“这只不过雕虫小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