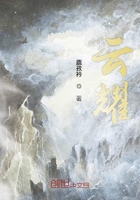这计策一出,公子罃的心腹吓了一跳。
不说军队暴走诛杀国贼主动政变这样的事从未有过,便是主动开战让墨家宣战这件事,更是会让天下震惊。
他颤抖着问道:“如此一来,只恐墨家北上……”
庞涓冷笑道:“鞔之适善用兵,岂不能主动被动之别?”
“如今诸侯汇聚洛邑,说是朝见天子,难道鞔之适会信?他自是知道这是诸侯在商量反墨之事。”
“然而墨家新得楚地五千里,一时无力北进,所以只当不知。我军若挑衅,墨家也必不会轻动,而是会选择宣战而不动兵。”
“墨家现在的局面,需要的是时间。三五年之内,若是南阳江汉未复,天下无可制墨家者。”
“而诸侯岂能不知?所以诸侯必要主动进攻,而墨家只要守住就好,而诸侯主动进攻,必要一齐用兵,数路齐进。”
“若是墨家真有能力北上,他岂能坐视诸侯会盟?若他尚有余力,必会趁着诸侯会盟不成之机,以攻代守,无论是破韩、卫、魏、齐任何一家,则诸侯便无力进攻。他既不做,非是不想,实不能也。”
公子罃心腹琢磨了一番,觉得似有道理,不太确定地问道:“你是说,若是这样,诸侯就必须要快点放弃分歧,先把反墨之事商量出个结果。而到时候公子缓已亡,魏国若不安定,墨家便可威胁到齐、韩?”
庞涓胸有成竹,点头道:“成阳,接连卫、齐。一旦诸侯怨怒,我们便以成阳撤军防备诸侯干涉为名撤军,齐卫必恳求我们不要撤,什么条件都会答应。”
“大梁,连接韩之飞地,我军若作势欲弃大梁,韩国必会和任何想要继续割魏的诸侯拼命。”
“事已至此,地不可不割,但这么一争,便可少割。况且若是这样局面再去割地,那便是顾全大局以为大义,而非被各国压迫。”
“西河卒入都城,便可威慑不亲公子罃者。诸侯不敢让魏国在此时大乱,也必不会推波助澜。事便可为。
“对墨一战,若大胜,韩齐秦皆强,于魏不利;若大败,则墨家北上无人能挡,于魏仍不利。是故,只有小胜、小败,于公子最利。”
“可以趁机变革,以武卒老兵为士、司马长、伍长,重建军队。墨家陈兵在前,公子便可收拾旧贵以集权,诸侯不敢让魏国乱起来,定不会支持那些旧贵。”
“魏国复兴,唯有此途。”
公子罃心腹道:“此事滋大,非我能主。我要即刻前往洛邑……”
目送公子罃的心腹离开,庞涓心中另有打算。
在他看来,魏国的路,只能这么走下去了。
他在西河许久,久历军阵,又多读书,看出了魏武卒的问题所在。
三十年前,魏武卒是天下第一强军,无可否认,因为魏国是第一个搞纯步兵方阵的,也是第一个开启了半募兵加府兵制先河的。
那时候魏国四面扩张,每一次扩张便意味着土地、人口,便意味着可以让军功转化为实在的利益。
三十年前,魏武卒们都还年轻,一旦被选拔,整日脱产训练,真的是可以做到一个打五个农兵的。
一个新被选中的魏武卒,家中有足够的土地,家中的兄弟父母不需要服役,只需要在家耕种,家里的一切都是从军之人赚来的。
一些立下了军功的,还能有奴婢隶农,从而使得家庭可以养得起一个真正的脱产士兵。
除了军中发的兵器、弩箭等,自己还可以购买更好的皮甲、自备驼载货物的马匹。
那时候没有火器,没有火药,甚至劲弩都少见。
那时候弓手还是以村社的乡射制度选拔出来的,各国的弓手数量都不多,秦国还在用古旧的战车。
脱产训练的武卒防守反击和结阵冲击,无人可挡。
然而,三十年后,种种问题开始显现。
越来越多的脱产武卒老了,老了之后让儿子接任,战斗力就难免下滑。
魏国二十年打了三四场大战,战战皆败,根本没有多余的土地和人口奖励军功。
泗上的火药和火器改变了天下的局势,青铜车战时代无敌天下的武卒,在新时代下已经落伍。
一个秦人的火枪手,可能只是一个训练了一年的农夫,一样可以用简单的手段打死一名脱产训练了二十年的武卒。
火药的出现,在三十年前拉近了泗上那群农夫和脱产的士阶层在武力上的差距。
放到西河,也是一样。
这些新兴的军事自耕农或者叫军功小地主太昂贵了,都是冷兵器的时候整日训练的优势太大,一辈子服役和那种平时训练几日战时征召的农兵大不相同。
可现在,一名武卒的开销足够供养四五名征召起来编练军阵的士卒,而四五名手持火铳列阵对射的士卒是可以胜过武卒许多的。
魏国没有强制分家,武卒的待遇是按照家庭计算的。
所以魏国经常会有一些十几口人的大家庭。
这种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因为供养出了一名武卒,所以他们不需要缴纳赋税和劳役,大约四名青壮男性受庇于做武卒的兄弟,带领依靠战功和战利品换来的隶农奴婢在土地上耕作。
一旦成为武卒,不需要服劳役,单单是这一点,就比普通家庭要强许多,劳役会毁掉一个自耕农家庭,而有人服劳役有人不服劳役则是土地兼并的最佳手段。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当年的那批老武卒,哪一个家里不是七八百亩土地,七八个隶农,十几个家人。
除了这些之外,一名武卒身上的武器、衣甲、粮食等,又需要大约两名青壮劳力在后方。
当年的变法,变得不彻底,导致了现在魏国内部旧贵族腐朽不堪用、而新锐的武卒也开始成为了利益集团不能轻动,这就是魏国现在面临的变革困境。
庞涓素有大志,认为自己若有机会辅佐公子罃,便可尝试着进行变革。
太激烈的变革在魏国难以实施,所以庞涓想到了一种不动多数统治阶层利益的变革方式。
那就是先利用公子之争贵族之斗下手,转移矛盾。
既然对外战争连战连败,魏国不能破局,不能够分配足够的利益使得新贵旧贵都满意,那么就趁着公子之争,杀一批旧贵,利用他们的土地喂饱新的军功地主。
这些新的军功地主出身的武卒,职业为兵,论及训练程度和纪律性,都是比一般的农夫要强得多。
西河之败的缘故,不是武卒不能打了,而是秦人的数量太多,使得武卒难以在“公平”的条件下作战。
庞涓遍观这三十年的战争,认为在火器、骑兵、步阵出现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会战之中战胜两倍的敌人,包括泗上那些军队也不行,除非是双方的训练和士气相差太多。
所以他认为魏国军制的方向,就是将武卒从“卒”变为“士”,从兵变成军官,拆散武卒,弄出一批职业的军官阶层,代替那些不合于时代的腐朽的血统士。
武卒整日操练,其纪律和战斗力,都不下于那些血统传承的士,而且相对于正统的士,这些武卒占有的土地相对而言更少。
将西河武卒拆散,以他们为底子,作为基层的伍长、司马长之类的军官。利用征召的农兵作为士卒,很快就可以拉出来一支政治上可靠并且依附于王权;战斗力上低于纯正的武卒但是却依旧可以一战的军团。
献祭一批旧贵族,比如趁着这一次公子罃和公子缓之争,把公子缓和公子缓一系的心腹贵族做掉,让大约五千户武卒瓜分掉他们的尸体,成为魏国的新一批低阶军功贵族。
这些武卒出身的老人将会成为军官,充实着将来新建的军团,大量征召的农夫和城邑手工业者,不需要为何而战,只需要他们头上的军官知道就行。
有了这么一批会听命于君权依附于君权的军功新贵,那么君侯手中就可以有一支听命的军队,就可以压服其余的贵族,从而逐渐开始变革。
而这些武卒出身的军功新贵们,可以世袭为军官,凭借土地和家庭财富获得良好的教育,凭借职业军官的家庭传统培养出足够的基层军官。
只要军官足够,就可以把各种各样的人训练成听着鼓声进军、不畏惧铜炮的合格的军队,将魏武卒从昂贵的职业兵精锐化为一批廉价的征召兵配上昂贵的基层军官的新军。
给予武卒出身的新士们一定的特权,使之忠心。
以武卒为基层军官,训练新军,压服旧贵。
在不大改的前提下,逼迫旧贵提供兵员和一定数量的军费。
在不动旧贵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重新组建一支战斗力可以基本保障、数量远胜于武卒的新军。
赏士不赏兵,因为赏赐兵卒的话,魏国这点家底根本赏不起,因为就算赏赐新的武卒士的那些土地,还是割了一部分旧贵族的肉才能割出来的。
庞涓的军改构想,出于泗上的军制,但又不太一样,毕竟两方的经济基础不同,国力富庶也大不相同。
但有一点,庞涓很清楚,泗上也有一群“士”,也就是那些职业兵和职业军官,他们是战斗力的基本保障,而宣义部、墨家组织之类的东西,魏国学不来,只能学这种职业兵和征召兵混合的办法。
不过泗上的职业兵领取的是工资,泗上的工商业利润、税收和廉价的粮食,都可以保证这些发的钱足够职业兵的生活。
魏国不行,发不起,只能用土地代替金钱,因为想要用金钱代替土地需要发达的工商业,这一点魏国做不到,只能饮鸩止渴发土地和用免税免役代替。
纵观天下,庞涓觉得自己的这一套军改的策略,和齐国的更像一些,也都是让一部分士做世袭军官,战争利益和他们息息相关。但齐国那是一整套的经济和军事的双重变革,那些有“轩辕”姓氏的军官贵族可不是这些武卒的那点土地和人口控制量能比的,而且经济模式也完全不一样。因为齐国靠近泗上,所以可以加深农奴隶农制度,从而让那些军官贵族得益,售卖粮食农作物以得利,并且拥有廉价的、被困在封地上的农夫做兵员。
魏国若想复兴,只有走另一条路。一条君权依靠武卒士和君权压制旧贵、旧贵和君权以及新军功地主合力镇压底层反抗的、对外扩张之路。不对外扩张,就只能新军功地主和旧贵族之间互相吃,就像现在他的计策,靠公子缓的尸体稳定武卒军心一样——对外吃不饱的时候,可能会出大事。但这是将来要考虑的,魏国已经到了绝路,只能走下去了,不然连谈将来的资格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