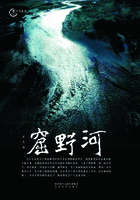“动了,他醒了。”景恺听见人类的声音,却不见人类,只怨自己的眼睛和舌头都不争气,瞎了就罢,还不能很快说出“这世界只听得见人声,却看不见人身”的本质。
“顾景恺!感觉好点了吗?”景恺耳濡目染,双眼沾上了些许世间温情,在月晕朦胧中睁开:“我在哪?这是地狱吗?”景恺刚对这世界产生的一点清晰却又被四边的啼笑给打回了地狱,他隐约地看清是房东和几个护士,惊得他直猜自己魅力过大,拉一个房东老儿也就算了,几位年轻靓丽的小姐也为自己陪葬,只向古代封建君主看齐。他问道:“我,我怎么了,我是不是在地狱?怎么回事?”
房东显然对景恺的魅力存有置疑,篡改生死说:“我们都是在医院。”
景恺的生机被一线挽回,又问:“怎么回事?”
“哎,你小子啊!太粗心了。”景恺见他吃了轻量的摇头丸,摆头的幅度和频率都不大,料定这头中的思想也不轻,忙追溯原因,房东哀道:“两天前的中午,我听见五楼也就是你家一声巨响,玻璃都震碎了,接着就是厨房冒出一串黑烟。邻居们都跑出来看,我上五楼怎么敲门也无反应。于是我就找到备用钥匙开门。一进门,屋内一片狼藉。”说到这,房东极像无液体溶解的固体颗粒,又饮下一杯碳酸汽水,致使他一边摇头一边叹气:“当时屋内已经起火了,火势不是很旺,出于紧急,我在电脑前发现你就抱起往屋外跑。幸好抢救及时,否则就……后来调查出是因为电磁炉上的锅子烧得太久爆炸,而锅子的钢片刺破了煤气罐引起的爆炸。你因此就在这躺了两天。”
“那,那我家怎么样了?”
“哎,还能怎么样,毁了呗!”房东的汽水仿佛有预留给景恺,景恺接着他未叹完的气继而叹气,却把那摇头丸制成了定心丸,景恺沉定思痛想这类荒谬之事以前只在电视看见,如今自己却上了电视。愚知肉体恋爱何等伟大,只要上了,就成伟人。景恺倒觉自己像个伪人,如今无家可归,一无是处,无路可走,一无所有……恨不得要成语词典中带“无”的成语都为他同情。清代张潮《出梦影》中有言:“竹以子猷为知己,菊以渊明为知己。”面对这番这情形,景恺无知也无知己。
“顾景恺,你看看谁来了?”房东一语又让景恺对警局有了刑事幻想。
“你们都出去吧!”景恺又听这话声倒不像是块打手的料,心中后怕失掉大半。只见那人身穿西装,年龄约摸知天命有余,却想真是警察,也不会严重到让自己满地找牙。
“不要太过用脑,我知道你在想我是谁。”
“那你是谁?”
“吃个桔子,其它的待会再说。”那人的口吻亲切得可与父母的温情重叠,可惜那桔子不像解锁回忆的钥匙,倒似上锁回忆的枷锁,景恺接过它仍想不起自己的缘分何时巧遇巧人。
“还没想起来吗?”
“不想了,我烦着呢!你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真的想不起来?”
“你直接说吧!”
“我——。”
“咔嚓!”“顾先生,按您的吩咐我买回香蕉了。”
“谢谢你!”景恺刚提起的心情又被护士小姐的一语杀得像跑了回车马,惊得他又跳入户籍普查的官职中:“你姓顾!”
“顾景恺!你病还没好吧!连自己叔叔不认识了!”
景恺吠形吠声跳了起来:“什么!”
“你先出去吧!他跟我有点小过节!咳咳……!”
“好的,你们慢慢聊!”景恺维护居民合法的隐私权益,待护士关上了门后又叫了起来:“你跟别人说了什么?你到底是谁?”
“隐菊的朋友!”他这话蕴意饱满得像酒足饭饱的壮夫,引得景恺不得不以思考的形式来估摸其质量:“这,这名字是在——”
“5230,Allstar……。”
景恺情不自禁,叫道:“是你!”接着拿出孔子讲义,不耻下问:“我认识你吗?你是谁?为什么送这些东西给我?你想做什么?有什么图谋?”景恺为维护自身利益甘走妇人之道,但毕竟是个冒牌,效果以多抵一,只换还那人一句:“我就这么难认出吗?”
景恺的记忆猛然又似中国商业的发展,曲折不止,最终被那张脸暗杀在一个晚上,待中国商业甘愿辱用嫖妓时间烘托出了景恺的答案:“是你,你是那晚的那人。”他顿时五内如焚赞道这世界的渺小,但再小也小不过中国商业的一夜,再大也大不出中国商人的一晚。景恺犹记高一离家出走的那两晚遇见他时,他只不过是个鹑衣百结的乞丐,如今在丐帮混出了钱源,当了帮主,乞丐之王落入他穿西衣打领带的一派威风中。
“唉!想起来啦!怎么样,我的乔装技术还行吧!”
景恺一脸无奈,想前两次无独有偶撞见他都是在妓女活动的时间,今日不巧,妓女猖狂,敢于光天化日之下揽客。那真是历史的一大退步,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便问他:“你怎么在这?”他突然又想起了什么,复补上:“还有,你怎么当我叔父了?到底怎么回事?”
“以后再跟你解释吧!我先问你,你妈呢?”
“走了!”
“走了?去哪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就算在美国也该飞回来了吧!”
“你别说了,我现在脑子一片混乱,你先回答我,你是谁?”
那人无计可施,便甩出传统文话说:“凭我是长辈,你该尊重我的问题吧!”
景恺蔑视注重传统之人,他常想:自己为什么要活在这世界,也许就是为了活出自己的世界。便拿出自己的传统,说:“你不会也是我爸的手下吧!”
那人即刻摆正态度,活出自己的世界:“不,景恺,你误会了,不是那样的!”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告诉我实情。”景恺的坚定逼得他对传统望而却步:“那我告诉你,你别吃惊。”景恺一笑完成使命,想:传统无非是一群活人对死人的追求,可就是有些人连自己是怎么死的也不知,所以你看那些要死的人是如何苦苦追求活。
景恺量他不是阿拉伯人,编不出什么天方夜谭,便将那惊一口吃掉,放在胃里韬光养晦,接着说:“不会,你只管说!”
他不假思索地冒出一句:“你常看报纸吗?”
“这与报纸有何关联?”
“广东一彩民喜中500万元大奖。”
景恺的胃快要撑不下这重惊,又不敢违诺诚信,像那拘留所的拷官,习惯性地试问一句:“莫不成就是你?”
“不错,就是我。”
没想到这一问倒钓出了大鱼,其大足以撑满景恺大空的胃。景恺的惊苦大仇深,终于脱离了苦海,逃逸出胃,感触一句:“我相信现实,但我不相信事实。我没听错吧!”
那人吞吃景恺一惊,倒不反胃,说:“这就是事实,别不相信。”景恺认错地比认命快,只有点头相信。
“咳咳……后来,我为了感谢你,就寻着那晚你对我说的年龄和学历去找你。当时找到你时你已跟你母亲相依为命,年纪轻轻就没了父亲,母子二人确实过得很不容易。于是我就花高价买了你们正对面的一套房子,在后来的日子里,一切都算平稳。得知你妈出外度假了,后来的事就这样了……”
顿时,景恺忘了悲伤,忘了快乐,忘了自己,时间冲淡了骗局,却将其又冲上了一个高度,骗局的骗局是结局,结局的结局是迷局。景恺一时想不出自己要做问题儿童还缺少什么疑问,只好从姓问起:“您贵姓?”
“免贵姓严,忘了啊!”景恺点点头,证明自己已从问题儿童升华到健忘老头。景恺的清醒逐渐被时间取代,问题接二连三道出:“严叔,你是不是有精神病?自己中了500万居然还来理我,若我中了100万我都早去逍遥了。”
景恺的口气说得连严父都快不相信自己,他笑着还回景恺精神病大夫的称谓:“没错,我是有精神病。这病叫受恩莫忘。”话罢后两人都为对方神圣的职业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两人的笑像林妹妹投胎,从天而降,声音大得惊得病房外的人都为之动容。
“当初要不是你给我100元,我能活到今天就算是个奇迹,更别说中了那500万。我的命算是你给的,我不想知恩不报,可能这就是你所说的有病吧!这个回答有水平吧!”
景恺忽略其水平,却难以忽视其真情。景恺想不到天下之傻,何傻不有,放着500万不享受而去扶贫救济,好在500万元没有灵性,否则定会因身为人民币而自卑死。因为人民币通常只会让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而从未遵循让穷人变富人的规律。眼下景恺算对“傻”有了新认识,这认识高人不浅,直教景恺认失,认实,认始,认事。这下他认识的比严氏见识的多,谓之见多识广。
“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
“我……。”景恺凝视着他,一股暖流斗转星移割破了他的喉咙:“那……。”
一只黄鹂留恋窗外的风景,啼过几声。景恺低下沉闷的头,让发丝掩住脸上的悲伤。只是这掩饰像是邮信,只对外开放,对内毫无一用。
“讲完了?”
“嗯!”景恺的头愈往下低,逝过的悲伤也被带入深处。他终究明白为何像李白这样的千古名人要留一头长发,故是多情寂寞,不用低头便能掩饰孤独。在坚持这个理论的前提下换种说法,政客从不说寂寞,而妓女时常寂寞,同样是人,政客却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妓女的寂寞之上,这便是有学历的男人与无学历的女人之间的差距。
“你现在无家可归了。”
景恺斜望那只黄鹂,身上的痛苦仿佛随它一起离了这世间,说:“不是无家可归,你应该说是无妄之灾,至少还能安慰一下我。”
“那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严氏的“想”像是抹了粉的女人,明白全露在脸上,景恺得其意:“你应该会收留我,或者认我做干儿子之类的吧!”
严氏做下一次深呼吸,一口气将景恺的话吸掉,在口中润了润那味道,感觉亦不错便又弃之欲出:“哈哈!干儿子就算了,做义子吧!”
这话听在景恺耳里,欣于心中,似乎天下一切要素都被赋予其中,景恺道:“跟我想的想差无几嘛!”
“咳咳咳……。”
“你怎么了,怎么总是咳嗽,有什么病吗?”
“没事,最近感冒了。”
景恺不在乎他的病情,反来问自己病况:“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不急。”
“噢,对了,我该怎么称呼你?”
严氏对后辈的名份已失逝在几十年前,如今贸然窜出一个,习惯地不能像唐僧五百年认个徒弟一般大方,便说:“随便你吧!”
“义父!”
“哈哈!义父就义父吧!”
景恺突然想起了上帝,若在此时不给他露脸,恐怕以后就没多少机会:“这一切都太意外了,像被上天安排了。”
“不,不是安排,是种缘分。”“缘分”二字在严氏口中的分量显得卑不足道,像是他这一生都靠这二字行事。
景恺瘫软在床,一切总算被和平托出。回忆中的自己,堪比梦还遥远,孤独之心犹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景恺听了一世的传奇,如今自己竟成了主角上演了传奇。都说上帝是女孩,可依发生在他身上的种种迹象示明,上帝是个不伦不类的女孩,既没母夜叉般暴烈,又无窈窕淑女的娴静,对自己爱理不理,拾起来后悔了又丢回去。假是带刺的玫瑰也有缓手的时间,可景恺比那玫瑰惨得多,只有眼福,没有手福,瞥一眼就扔。这要被李长孙(世上最先发明定时炸弹的科学家)发现,定时炸弹的桂冠险些就要被迫摘下。他闭目怆睡。
第二天,景恺安然出院,被义父带回了新居。景恺不忍看到旧家的残影,却让义父拾回了喜新厌旧的坏习,说:“阿恺,没什么好看的。咳咳咳……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对,过去的就过去吧!”景恺苦想着随义父上了楼。
新家的风格显然要比东方人含蓄,腼腆地只看内在美。景恺对东方人的大度不疑,却问:“义父,你对钱不感兴趣吗?这房子装扮得多少钱啊!”
严父的微笑形象地把那钱也叹微观止说:“放心啦!够用,把你养到一百岁都行。”他真正做到视钱如粪土,八十二年的生活都绰有余裕,这情操正是景恺所向往的。景恺吸取了义父金钱的微利,也小笑小度,算是对钱的轻视。继而走到自己房间,一看气派,东方人的含蓄转眼成了阔气,房内装摆的设备堪比入住故宫或是白宫。这意象不属东也不属西,可知不是东西。景恺整理好房间,略观了一下便与义父匆忙告别随后回校。
跨入久违的校口,景恺的心澎湃得仿佛能将此校纳入自己的情怀中。一跨进教室门这心却小到能让针眼针破,景恺一语:“报告!”
“你去哪了,怎么不请假?”全班人士一般蠢,以己度人,见蜈蚣如此反应,主从关系充分体现,射向景恺。
景恺招支不住,只得与他们头目坦白:“我生病了,没来得及向您请假!”
蜈公也学古人叹气一度,斟酌一小会儿才破口:“进来吧!下课来办公室一趟。”景恺步过一群大嘴女人和像大嘴女人的男人的身边,回到座位上。
“有什么好看的,黑板就不看,一个不守规的人有什么好看,你们是不是也想变成那样子?”景恺的喉咙仿佛被蜈公的全肢围了个圈,闭塞地默不敢声。一节课也便如此晃过。他的呆木拖着他的木呆走到办公室,蜈公的脚已翘得直比蔡依林的腿弧更近完美。景恺不是Jolin的粉丝,自没欣赏她的义务,对其腿也以偏概全否认。蜈公见自己腿法的魅力不足让景恺主动发言,气得恨不得拜谒聂风来招风神腿让其见识厉害,可风神腿不及封神腿,利益面前蜈公无话好说。
“来,顾同学,说说你的英雄事迹。”
“我,我生病住院了,躺了两天,今天才好!”
“什么病能让你这等人物都变成侏儒。”
“发高烧。”蜈公点了点桌上的一张纸,表情忽变得好像北京的高速公路,急转得让人反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