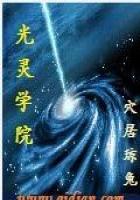下课铃响后景恺被没有地位的老师领到了办公室。他坐景恺立,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用食指夹着中指使劲往桌上叩了叩:“你敢顶撞我?你是不是不想读了!”这一叩对景恺倒无大碍,倒是引来一堆围观的狗仔,算是遵循了政治中的轰动效应。蜈蚣闲来无事,端杯绿茶悠坐着看戏。景恺没敢吱声,他顾及眼下父亲没给这群狗做经济工作,先天不足,后天难补。
许捷仁再顾脸面,怕有失老师威严,又用力在桌上叩了一下:“哑巴了是吧!我问你话呢!”这一叩,对景恺还是没事,可他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疼得他损尽了形象。景恺想笑不笑,想哭又不能,哭笑皆不得,恨自己不是画家笔下的人物肖像,从生到死都是一个表情,只好做画家笔下的鬼样,难堪地道出鬼话:“我没有那个意思。”
许捷仁似觉他这话甚不足偿还他手指的痛楚,反问道:“你没有哪个意思啊?”
景恺强忍:“我没有不想读书的意思!”他又向周围狗仔们看了看,一刬的脸都露着奸宄的笑。再看看同为受害的许捷仁,凶煞地想扮鬼吓鬼,只欠景恺一句话的刺激了。景恺生性不傻,把他那样子比作鬼,称为老鬼,许捷仁巡视六路,见到自己的同类正议论着自己,忙蹦出一句人话:“什么都不要说了,叫你父母来,我找他们谈谈。”景恺一听咋舌不已,但也迅速反回了他:“我父母不在,出差去了!”姜是老的辣,许捷仁这姜自身埋于教育数十年,老辣纵横,连笑说:“你少来,我教了十年书,你这破口舌,我一眼看破,给你面子,你父母电话是多少?”说着从袋中掏出手机准备拨号。大概是被那Maddog给感染了,景恺居然不知不觉地从口脱出:“151290……。”
“喂,请问是顾景恺的家长吗?”“噢!你好!你好!顾先生,是这样的……。”
景恺的心情随他的每一次的话语而低落。他不知父亲会怎样看待。要让许捷仁知道自己的家庭状况,定会被狗仔传遍“狗界”,那时,景恺就能在红人馆发言了。
“喂,顾景恺,你爸要和你说话。”景恺停止了丰富的想象,开始接受残酷的现实。
“喂!”
顾父显然生气,却又一贯绅士之风:“我没有称呼吗?”
“叮铃铃……”景恺的心被这铃声惊得“叮铃”作响,话语像挤牙膏一般被他挤了出来:“爸!”
“怎么回事!你母亲可真够仁慈的,要是我早替你休学了!你说你来到这世界有什么用?除了敲键盘的速度比较快还有就是能写一些流水账你还能干些什么?整天吃喝玩乐,不学无术……”顾父一口气将景恺的陈年坏事像排泄一般拉了出来,可怜景恺曾经的风光事迹得不到顾父肛门的宠爱,半天拉不出一个字。顾父身为大款,莫不在乎这时间的金钱,老鬼摇身一变成吝啬鬼了,心疼手机话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话费一元一角地落,所以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一分一秒地过,老鬼内心的血一点一滴地流,所以又可以说时间就是生命。
“好了,我话就说那么多了。等下我会跟老师说以后有什么情况找你母亲。还有以后我每个月打八百元到你卡上。”景恺也没多学女人的啰嗦便允诺了,他把手机交还给老鬼。老鬼一把夺过,怒视了景恺一眼:“喂!顾先生。真不好意思,打扰了……”许捷仁的转变可比变色龙之迅。
许捷仁挂下电话,心疼不已,又不好把小气二字挂于口上,只好写在脸上,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说:“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我也不想多说,希望你能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好了,你回去上课吧!”景恺表里不一给他留了个“噢”字便转身回教室。
“报告!”蜈蚣依旧懒醉如泥,眼也不眨说道:“才子回来了啊!”全班人以为才子是卓别林的化身,忙不迭发出一阵笑声,景恺觉得自己一米七十五的身高和英俊爽朗的面容没有卓别林那般伟大,也对得起有雪亮眼睛的群众,可惜群众的眼睛不雪亮。那笑也带有细胞分化的趋势,越笑越多,像要一下子把下辈子的欢乐在今天一齐释放。景恺摇头自叹,不敢看金慧欣,走回到座位上暗想一定要出人头地。
隔日,景恺未背弃自己昨天的诺言,早早地来到教室,竟没想到教室只有他一人,可见当今学生很少履行诺言。快走到座位时,他看见一个盒子静躺在自己的椅子上。这是第三次。景恺这时显出人本来的惰性,不愿费时思考,直接上前把它脱了个精光。同前两次不同,这次的礼物并非娱乐产品而为学习用品,几本最新的必备工具书复加一系列的辅导资料。景恺由衷地钦佩此人的先见之明,昨日刚许的志向倒被他先付诸行动。景恺料不到自己思考慢人一步,在这实践上也愚人一等。他实在摸不透是哪位慈善家,不惜血本为自己一再提供物质。顿时感觉自己此时的脑袋就像把漆枪,明明是把武器,打上去对人只有些许分量,却不及伤人作用。景恺此时对时间的珍惜犹若男人对美女的珍惜,恨不能学韦小宝同时珍惜八个老婆。景恺接受了没有八个美女会同时爱上自己的现实,转而化悲伤为力量,读起书来。
一个上午过得很充实,景恺并未走到《淮南子》中去“临河而羡鱼”。旁人看来这要归功于蜈哥和鬼哥的鼎力相助,景恺不由地感觉这两称呼既符合了中国的道德标准又满足了自己心中的不满,可谓一举两得。他正浏览着那堆学习资料,忽感有人在背后扯自己衣服,像是被乞食者苦苦拖求不放。景恺转过去想看看其面容是否与其饥饿程度相映成趣,不看不知道,一看是慧欣,景恺所想与所见方枘圆凿,怜悯之心幡然悔悟,叹道:
“笨蛋啊你!你怎么喜欢扯我?我又不是没名字!”
“呵呵!”金乞儿名实不符,笑料不止。
“好了,找我有什么事?”
“呃!文学社开会,现在要到学生会办公室集合。”景恺偷笑,原来她乞的不是食而事,名正言顺说:
“嗯,知道,走吧!”
金慧欣没说什么,腼腆地低下头,景恺走到她前面她才挪动步子,颇有乞食者对食物矢志不渝之精神。景恺看着她这举动,让自己的笑难以释怀,傻乎的样子略带些可爱。金慧欣遽尔走到他左手边问:“你昨天没事吧?”景恺毫无半点羞愧,一本正经说:“没事!只不过是教育了几个没有文化披着羊皮的狼罢了!”
“我觉得你身上有种傲气!”
“傲气?呵,在你看来,这傲气是个什么含义!”
“哎呀!说不清啦!反正不是坏话!”景恺怕自己笑起来比凶起来更可怕,于是捂着嘴笑——其实这动作应该是女人的特权,丑女的想法和景恺一样,都不想让自己的笑成为他人心理上的一种负担。而美女大可不必担忧,因为理论上,美女笑要比不笑漂亮。所以男生与乐观的女生初约时一定要谨慎,因为爱笑的不一定是美女,却很有可能是恐龙。金慧欣的话总是让景恺无话可说,好像她是老子,景恺是孙子。中国提倡道家学说,却不崇扬穷兵黩武。自然孙子人微言轻,毫无言语可说,即恐说了也是些废话。不想中国文化从古至今倒也能拥护和平,却只是庸护,真遇上战争,还不是照样用武,骗人尔罢。总的来说,教育局就是个骗局,教师就是骗子,学术便是骗术。我们的学生当然是集大片于一身,于是便有了大骗于一生。如果说能看穿这骗不净的道路,中国教育这片道路就是不尽的。中国人多数视力正常,因为他们身处社会。中国学生都是视力不正常,因为他们身处教育,原本他们视力正常,没有人喜欢眼睛,却没有人不喜欢眼镜,到最后,只能在教育里做盲人。景恺自诩:我不走寻常路,只为你们找回寻常之路。
金慧欣突然在景恺胳膊上轻捏了一下叫道:“又迟到了,都是你害的!”两人一齐进门,金慧欣喊道:“报告!”室内社员目光立即从社长身上移到了门口,景恺突然想起了什么也叫了一声:“报告!”那几十双眼睛像侦察的雷达,信号频率极差,时而不时地泛着秋波,怕是昨晚星星看多了,“耳濡目染,不学以能。”景恺四周环视了一番才发现大家关注所在——金慧欣一把手挂在了自己的左手上。景恺跟随大众把雷达的目光钉在那两手缠绵之处。很不幸,人往往是在无知中死去。金慧欣更惨,已经死了却还不知道死因。景恺于心不忍,再也看不下去了,解开她的手,在众目睽睽之下撇下她找了个隐蔽之处坐下。金慧欣余情未了,继而走过来坐在景恺身边。俩人离开片刻,而这门像有余音绕梁之奇,众人的目光滞留在门口,透过一绺阳光的照射,他们仿佛看到自己未来的憧憬。社长一咳嗽,雷达立即复位。
“顾景恺、金慧欣你们以后注意别再迟到了,还有你们自己的形象!”她又咳了一声,的确是昨晚看星星着凉了。台下雷达狐假虎威,认为咳嗽是种权威的象征,因而纷纷效感,以示自己侦察技术之先进。景恺于一旁听得揪心,他想这现代科技竟也同狗类家畜臭味相投——雷达,疯狗。不禁越想越有意思:两者都取第一个字凑成名词的话就是“雷锋打狗!”怕是劫富扶贫,难得世间能有如此好人。这样想着,景恺的心里便平衡多了。
“具体的要求就是这样了,现在分组吧!”社长一语话毕。“她说了什么?”景恺的疑惑飞满天空,可见不少。“呃!那个社长说明天要去高一级作宣传募招新成员,现在叫我们每两人一组分选。”景恺看着她又转向雷达们,那群雷达的面容产生的磁性与景恺相斥。为了不让这群高科技的目标再锁定自己,景恺的脸就一直排斥着他们的脸,望向前方对她说:“喂!我们一组吧!”金慧欣不解以为他在对着空气说话问道:“你在跟谁说话?”“笨蛋,这里除了你还有谁,Ghost?鬼?”景恺不知是否被那Maddog咬过,自己突然也做了个不折不扣的Englishdog。
“为什么要跟我一组?”
“你真笨!你看现在这情形我除了能找你谁还愿意跟我一组,pig!”景恺这次的智商随这疯狗的病源的感染渐趋变低,成了Englishpig。金慧欣只是浅淡地回答了句“噢”,社长目光如炬,便不随大众随主流一声咳下。
“好了,现在把分组的情况报上来吧!”
“顾景恺、金慧欣一组!”景恺的声音以光的速度排到了这条报名队伍的最前头。违背自然的是,这一群雷达的方向立即瞄准景恺,强大的磁性将他的头无形地打向后方。金慧欣在一旁哭笑不得。社长看见这一千年难遇的物理现象顿时惊讶不已,许久才回过神来:“顾景恺、金慧欣第一组负责高一一班二班和三班!”磁场方向也随这话一齐归位。
“走啦!站在这里给人当笑话啊!”
“噢!”景恺领着金慧欣步步离营,终于走出敌人所监视的范围。他缓下脚步恨这话为何不能同教育一样人浮于事。这样自己或许就不必出丑。他回向慧欣道:“你刚才干嘛勾住我?”她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跟在景恺身后。景恺再而减速想让她迎上来。却不料两人就像是一台摩托车的前后轮子,景恺前进她也跟着来,景恺减速她也放慢速度,始终隔着距离。景恺索性站在那不动,她也不吃亏,坚持摩托车静止的原则,只听得背后一阵窃笑。景恺矜持不住压迫,把双轮车变成单轮车直冲她面前:
“哎!你今天很不正常!”
金慧欣笑不惊心说:“嗯,你也是!”看着她可爱的神情,景恺真不忍心再去拷问,心中激起的不是愤悻,是爱情,他怕这恋爱的种子滋生得太快来不及间阻便同她告别一人离去……次日,早读时接到命令进行宣传。一路上,他们紧闭着嘴,景恺怕的是自己说错话,而金慧欣怕的是说漏话。一错一漏足以显示出这尴尬的场面。因为双方之前没有协调此项工作,结果一错一漏弄得错漏百出,尴尬之情进一步体现出来。好在如今学生听事颇有特点,他们中大多数都不喜欢当事人对着自己讲正事,倒乐意听他们说故事。若这故事能引起自己的高度重视,说明这是童话,若能引起他们深度重示,那便是笑话。景恺和慧欣就属于后者。被笑话了一次,经过此事后,景恺对她的感情愈加深笃了。与新兴起的学习动力相背而驰。他实在经不起爱情的责任,更不想一人承担两份爱情。这矛盾隐去不久,又呼之欲出。好比那毫无缝隙的乒乓球放在水中,刚一压下去,它又浮容出水,丝毫不受人施的压力。
景恺这星期和慧欣间频繁的交往都害于那该死的文学社。这文学社名义上说是招揽人才,可当权者哪知当今的文人不比古时的墨客。真正的龙皆有诸葛亮的血胤卧藏山中,剩下自愿露面的也只是些泛泛牛犊。所以,今次所招牛才逾过景恺这届老龙,文学社因此也发展了一回人力资源强社,在学校各社团中独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