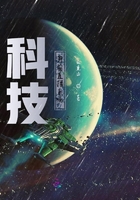一语点醒迷中之人。若说懿仁太子是太祖皇帝最得意的儿子,景阑是最疼爱的儿子,那宇文景睿则是他心中最像自己的儿子。爷俩出奇的一样,杀伐果断、英武睿智,还有一点,那就是猜忌心强。
宇文景中耷拉着脑袋道,“万岁爷为什么起兵,旁人不清楚,娘娘还不清楚吗?说到底还不是承文要削藩。其实承文没错,咱们皇上更没错,错就错在这套宗法上了。”
的确是这样,坐在金銮殿上的人想大权收归中央,可这样一来,地方的藩王就被逼得无处可走;若是不收起大权,皇帝还要看自己的藩王兄弟脸色,时间一久,必然生乱。
“与其等着四哥把我送进大狱里,还不如我自己知趣一点,缴了朵颜铁卫。”
“…”
“正好也去找她。”
我最终还是忍不住了,决定说出事实真相,“可她心里…没有你,她…不记得你。”
宇文景中猛然抬起头,仓惶无措地看着我。他自顾自地摇了摇头,“怎么会,我不信,我要去找她!”
我从来没见过宁王这么犟的一面,在我印象中,他就是那个永远都没正经的纨绔哥儿。其实,他内心的考量早已超出我的印象,他知道自己手握大权,将来必然成为宇文景睿的眼中钉,因此自己放权归隐。他更是一个痴情的人,尽管看上去不像。
他又说了一会儿话,无非是劝我的,之后便离开了。只是不知此次一别,又是何年何月能再见面,也不知,他能不能找到浣清。
天色暗下来之前,宇文景睿便来了凤鸣宫。与以往不同的是,我清晰地感受地到他的温柔。一举一动,皆是温情脉脉,可我内心却升腾起一种不好的预感,仿佛这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短暂的平和。
“听着今天嗓子好了许多,严沐到底是名医圣手。只是还不能多说话,要好好养着,那几个丫头是从前就伺候你的,也知人意,有什么事让她们去吩咐,你不许再累着。”
“婆婆妈妈的…知道了…”
他并未生气,只是沉寂了片刻,摸着我额头上的纱布才又问道,“还疼吗?”
我无声地摇了摇头。
“待会儿让丫头到内务司拿些修颜膏,等去下纱布之后记得天天涂抹,千万别落下疤。”
“嗯。”
“胳膊上的伤好了吗?”
“嗯。”
就这样,他问一句,我答一句,大部分只用鼻音哼哼一声便罢。他自觉无趣,便早早躺下歇息了。两个人明明靠地很近,但却像隔着千山万水一样,怎么都抓不住彼此的心。
接连几日,他都宿在了凤鸣宫,任凭翊坤宫那边怎么折腾,都没能将他请走。我不知道他是何用意,其实他呆在凤鸣宫也并无趣。
直到过了几天,十月十四,宇文景睿登基大典的前两天,宫里开始热闹起来。清晨时分,午门处的钟声刚刚敲响,辅佐宇文景睿的新贵家女儿便被送进了宫中,共十几人。除了宗族地位比较高的几位住在西六宫,剩下的都被安置在了储秀宫。宇文景睿原是要她们先来拜见我,但被我拒绝了,只图一隅清净罢了。
我还未来得及适应这份热闹,申时左右,燕京的女眷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