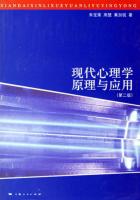不管出于什么,也断没有看人送命的道理,更何况如果他有什么好歹,门外一大一小两个女子定是要将她碎尸万段的。想到此处,天倾也顾不得别的,脚尖在墙上微一借力,人就直冲着白夜飞去。
那白夜见天倾来势汹汹,一副歹徒行凶的狰狞表情,只以为她是要对自己不利,向后一闪,人也顺势倒了下去。天倾未料到此人反应这么快,当下便化抓为吸,欺负对方并无内力相抗,硬生生将其头顶的幂篱吸到手中。
幂篱上的白纱本是见火就着的材质,此刻已烧的所剩无几,完全没有还给白夜的必要。天倾如此想着便弃了幂篱,又伸手取过墙上的烛台,前走几步欲查探白夜的情形。
豆大的烛火轻微跳动,天倾的视野亦随着它的跳动而忽明忽暗,因着专心找寻白夜未留心脚下,冷不防竟被个物什绊到——习武之人皆知,任何轻功除本身的高明与否外还要看各人的目力,若找不到适宜的借力之处,纵使夜无眠那等高手也无计可施。
也该着天倾倒霉,由于晦暗下不能视物,她便将着力点全放在右手上,待感觉右手腕磕到硬物时,再也没有变招的余地,只能由着身体下落。这一瞬间天倾想到自己摔倒后将发生的一系列连锁事件:重物落地的声响、萱璃的破门而入,以及自己的性命堪忧。
“若果真无法,也只有得罪天元殿了,只是如此一来又要生出诸多麻烦。”
正烦忧间腰际忽多出一只手来,就那么轻巧的一揽一提,天倾的身体便从新立稳在地上。
“多谢多谢。”她不着痕迹的向后退出一步,一面悄声谢着,一面又去看左手上的烛台,“要说公主府的东西就是好,如此一番折腾那蜡烛竟也不灭。”说话间已将烛台举至二人中间,而白夜的庐山真容也全然展现在她眼前。
白夜一定是个相貌极佳的男子,这点只看云华与萱璃的态度便不难猜出,但令天倾没想到的是,这“相貌极佳”四个字遇到他便也要分出三六九等了。
如果聚集世间半数的能工巧匠,大概可以雕刻出这男子七成的相貌,然而即便网罗世上所有丹青妙手也绝描绘不出他半分的神韵。若说其温和,可这温和中分明伴着桀骜;若说其圆滑,可那圆滑里又夹杂了孤注一掷的狠绝;即便是眼前凉薄似万事皆不挂心的眼神中也隐藏着一团不知名的火。
天倾定定盯着那双眼睛,那双眼睛则定定盯着烛火,明暗恍惚间,天倾分不清那跳动的究竟是火苗,还是他的心火。
“看够了么?”这是白夜第一次与她讲话,然而这态度、语气却绝不算友善。
天倾正尴尬的抽着嘴角,想不出要用什么言语才能证明自己并非断袖,忽觉地面轻微震颤,紧接着一道明亮的光芒穿透黑暗,将此间照了个清明。
“这是怎么了?”云华一打开门便将室内情状尽收眼底,虽说不曾点名责备,可天倾又哪里听不出来,当下便将方才之事一五一十的说了,只略去自己失态不提。
云华走近前来将白夜仔细打量,见有几率青丝已烧的焦黄,心里着实惋惜,“没事去摆弄那些做什么,好好的头发都毁了。”说着便命人取来剪刀,自己亲自执剪仔仔细细将那几缕焦发减去,又转向天倾说道:“今日本是想与莫公子畅谈,未料到被萱璃那丫头搅了兴致,好在天元殿有事将她唤了回去,不然还说不准要耗到什么时辰——说起那痨症,我倒也识得几位杏林妙手,但今日天已不早,若是公子不弃便在舍下屈就一晚,明日再做定夺可好?”
“这好是好,只是……”天倾显出三分难色,事实上若真如云华所说她的痨病只是计策,那任无寿便不在这里,自己也断然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但此来天元国都也是思无念的授意,她委实不相信通晓奇门之术的思老三会失算。
“只是房间要大些,不然睡得下这位就睡不下房上那位了。”白夜冷冷开口,此一言着实将天倾惊得不轻,要知那夜无眠的轻功可是天下间难逢敌手的,即便长眉仙君在此,不分出七八分精力于外间,恐怕也难察觉出他的存在。
“此人当真是邪门,还是少接触为妙。”主意作定,她便看向云华公主,略带不悦的说:“在下虽只是江湖中一个无名小卒,但也负担着家族兴衰之责,只身前往贵处,偶带一二随从也不为过吧。”
云华听得白夜的话,料定天倾是某个隐世家族的核心子弟,又见她为人坦率,一副不善心机的模样就更是将其视作了必须结交的人物,因此说到:“莫公子严重了,白夜向来谨慎,方才之言也并非怪罪。”说罢便吩咐侍女收拾出两处紧邻的厢房,安顿天倾住下。
“关于那痨病之说,八哥怎么看?”待得四下无人时,天倾才将夜无眠唤出。
自打被白夜窥破行迹,这夜无眠便是一脸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羞愧,此时虽听天倾问话,但心思却全不在此,故没头没尾的回说:“那白夜的确半点内力都无,可他的六识却是比江湖上顶尖高手还强,可疑得很。”
“我劝八哥还是将好奇心收一收,那人再可疑也与你我无关,休要学那孤老二的为人。”她说到此处才想起自那晚之后便再没见过孤无终,也不知他此刻躲在哪里逍遥。
坐落于闹市的倚兰阁里,孤无终怀抱佳人正饮得畅快,忽觉鼻头发痒背脊发寒,“阿嚏”一声将怀中美人喷了个五颜六色,“奶奶的,谁骂老子!”刚吼完就想起这世上敢骂他又能骂他的人不过那几个,心下着实没趣,再想饮酒才发觉美人早已羞怒的洒泪而去。
因着今夜月色皎皎,他索性提着酒壶走至阁楼边,凭栏远眺,就见一世的繁华景象,登时心有所触便吟咏道:“佳人去兮泪决绝,隔一墙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衾犹凉兮酒犹烈。”
话音未落,便听一尖细的男子声音喊道:“臭穷酸!一肚子酸文假醋!今儿就让爷爷好好教教你!”
孤无终闻言先是呆愣,再由愣变怒,复又转喜,模样就像个得了失心疯的病人,“不错不错,我竟不知还有人敢做我爷爷,哈哈哈——”说着便一撑栏杆跃下楼去。
待看得楼下情形又不由气闷,原来那尖声男子骂的另有其人。这种感觉就像是受邀赴宴,忙活大半天从头到脚准备齐整,待到了地方才被告知帖子送错了,人家根本不带你玩。这让酒至半酣的孤无终如何甘心?当下也不顾谁是谁非,瞅准空子就冲进战圈,三两下将身边人等撂倒在地,嘴里还嚷嚷着:“再来再来!怎么都跟软脚虾似的,孤爷爷我三五坛下肚都比你们站得稳!”
“管你是姑爷爷还是姑奶奶,遇到本将军也只能做孤魂野鬼!”说话间但见自倚兰阁前后左右涌入大量士卒,随后一武将打扮的男子便策马近前。
“舅舅——舅舅——”原先趴在地上装死的尖声男子见救星来了,立刻连滚带爬的跑了过去,那模样就像身后站着一个恶鬼,“舅舅,我本是带人来拿那偷了您小妾的酸儒,谁想到半路杀出这么个凶神——”他话还没说完,只听“啪”的一声脆响,那武将恨恨骂道:“不长眼的东西,让你再口无遮拦。”尖声男子捂着脸不敢反驳,只将满腹委屈都记在了孤无终身上,其余一众人都憋着笑不敢作声。
此时孤无终的酒已醒了大半,明白自己这是阻了人拿淫贼,当下一抱拳,正欲上前解释,就听那尖声男子再次开口道:“舅舅,这人虽不是那酸儒,可必定与他有关——此人的功夫甚为了得,兴许就是朝廷正在缉拿的歹人‘扫净天’!”
将军看了看孤无终,又想到那被自己捧在心尖尖上疼的美貌小妾,只喊了一声“拿下此人”便不再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