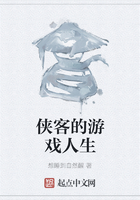马车内,庄稼汉横卧在中间,怔怔地盯着车窗。
车厢里的虽不怎的奢华,却也足够别致。
正中央一块檀木酒桌,车窗下码着酒坛,进里边的角落里,还摆放着一个双耳香炉。
庄稼汉躺在锦缎的褥子上,紧咬着牙关,忍受着煎熬的剧痛,偶尔从牙缝里挤出微弱的呻吟。
黄衣人歇依在窗边,悠然地看着自己的兄弟陪着小姑娘。
两人时而扮鬼脸,时而变魔术,时而讲笑话,犹如亲生父女一般融洽。
黄衣人心里也不禁泛起丝暖流,竟有些羡慕。
这世上,还有什么比逗小孩子更开心的事情呢。
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能让小孩子依靠更有成就呢。
黄衣人随口道:“老哥,你伤势如何。”
白衣人这才回过神来,道:“一会儿到了镇上,找家医馆,老哥就好生修养几日。”
庄稼汉慌忙摆手道:“不妨事,不妨事,小人怎敢劳烦两位大侠如此费心。”
白衣人只道他担心银子,展颜道:“身体要紧,老哥不必推脱。费用的事,在下自会解决。”
见那庄稼汉似要开口再说些什么,忙转向那小姑娘,道:“婷婷啊,一会儿到了镇上,咱们去吃好吃的。”
小姑娘眼睛放光,咽了咽口水,样子又是可爱,又是可怜。
可爱的孩子,天生就会让人可怜。
可怜的孩子,却要付出许多才会让人可爱。
可怜的孩子,大多是敏感的,即便很坚强。
庄稼汉转回头看向黄衣人,索性闭上了嘴巴,不再出声。
黄衣人则放下酒碗,自顾打坐起来。
小镇。
小镇不大,却也是镇。
集市虽非琳琅满目,物件却也丰富些。
酒店,布坊,各种摊子应有尽有,与久居的塞外已是天壤之别。
他似乎来过这里。
他似乎还有些熟悉。
但他早已不愿记起。
“阿桓,外面有个卖冰糖葫芦的,你带着婷婷下去买些回来。”
原来这白衣人唤作朱桓。
朱桓刮着婷婷的小鼻子,乐呵呵道:“婷婷,我们下去买冰糖葫芦?”
小姑娘爽快地点头答应,但这“要”字一出口,却又害羞地低下了头去。
“好,我们下去买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这四个字,从朱桓嘴里说出,就甚是有趣,逗得小姑娘哈哈大笑,笑的那样的纯真,那样的灿烂。
同样的字句,在有些人嘴里出来,就变得生动有趣。
同样的字句,在有些人嘴里出来,却会引起异样。
说话,明明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却也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朱桓领着婷婷下了车,吩咐赶车大汉去镇上打点留宿。
黄衣人此刻觉得很开心,因为他在乎的人很开心。
在意的人开心,远比自己开心更令人满足。
在意的人幸福,也比自己幸福更令人欣慰。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黄衣人从窗口望着两人的背影越走越远,漫不经心地道:“阁下的戏,也该收场了吧。”
马车内却还是一片寂静。
他在和谁说话?
黄衣人依旧笑着看那远处还未消失的一丁点儿人影,淡淡道:“此刻车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而这已是你最好的机会了。”
卧在一旁的庄稼汉突然怔住了,疑惑地盯着这个自言自语的黄衣人。
“我知你迟早要动手,便支开了那个女孩儿,放心动手吧。”
庄稼汉万没想到自己竟被看破,当下胸中一沉,冷汗直流,怒道:“你怎知道的!”
黄衣人仍是含笑盯着窗外,视线还未离开那对只剩下一丁点儿的背影。
许久,道:“那小姑娘在关门叫爹爹的时候,虽然凄惨,却也不自觉的透出了江浙一带的余姚腔。稍加品味便知是个戏童。”
见庄稼汉目瞪口呆,黄衣人继续道:“阁下装扮成山野农夫在关门等我,必然已算准了我的行程,是以在关口挨了一顿打,为的是有机会接近在下。但一个普通的庄稼汉挨了顿暴打之后却怎能不受内伤呢。”
庄稼汉下意识地瞧着自己的胸膛,面上更是露出惊异之色。
黄衣人又伸了个懒腰,漫不经心道:“你虽不时呻吟几声,又强自扰乱心跳,但呼吸吐纳之间中气十足,显然有些内功。”
见庄稼汉还是不做声,黄衣人又道:“搭救你上来的是我那兄弟,一路上和你女儿玩的不亦乐乎。你非但很少注意他们,却一直盯着车窗,暗地里用余光观察我的一举一动。显然那并非你的亲生女儿,不过是你分散我注意力的棋子罢了。”
庄稼汉忽地哈哈大笑,忿忿道:“原以为我魏延生在戏台摸爬滚打三十年,演技足以骗过你,想不到竟被你看出这么多的破绽。”
黄衣人仍旧盯着窗外,却敛起了笑意,长叹道:“山西名旦魏延生,殊不知再好的戏子,其演技也敌不过县城的一个九品小吏。在下虽不才,却也做过三品的官。”
魏延生嘿嘿冷笑,嘲讽道:“世人都称你玫花傲骨左侍郎,想必阁下的演技,则更为高明吧。”
黄衣人摇头苦笑,无奈道:“若是在下屑于用这些东西,恐怕也不至于流落江湖了。”
瞬间,他的眼神中,似流露出些许的哀伤与不舍。
但这哀伤与不舍中,却绝没有丝毫权力与金钱的影子。
远离了权力与金钱,他反而更加快乐了。
只因,远离了权力与金钱,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多数人,是无法理解这种感受的。
只因在多数人看来,这样的选择是极其的愚蠢。
魏延生瞪着血红的双眼,怒骂道:“王何欣!七年前你淫我妻子,杀我全家,这等丧尽天良,今日我定宰了你的狗命!”
话音未落,魏延生腾空起身,闪电般解下腰带,死死盯着面前的男人,目光中抱着必死的决心与悲愤,喃喃道:“冬儿呀冬儿,今日为你报了仇,我们夫妻就团聚了。”
王何欣却还是拄着车窗,竟动也不动,轻叹道:“冬儿呀冬儿,若是你夫妻今日团聚了,你却告诉他你连见都未曾见过我,可一定要送他回来呀。”
魏延生厉声骂道:“放屁!你还不受死!”
手中腰带瞬间连攻五招,攻势狠辣,招招打向心口要害。
黄衣人瞥见魏延生腰带前端颜色青黑,心知定是淬了剧毒之后来跟自己拼个生死。
但见招式凶猛无比,不由赞道:“早听闻,山西名单魏延生,舞袖飞花击千鼓,果真不假。”
七年前,他是个风流倜傥的男子。
出身梨园世家,五岁起便跟随父亲登台唱戏,颇有造诣。
白皙俊美的脸蛋儿,纤弱轻盈的身子,轻灵委婉的媚态,令女人都自愧不如。
可如今,面前这个衣衫褴褛,笨拙壮硕的庄稼汉,却又如此的真实。
谁也不知,这些年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令他有如此的改变。
只是知道,这些年,他一定活的很辛苦,过的很痛苦。
他的确,是个重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