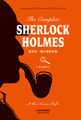三点才过,会馆大门竟缓慢打开了,露出黑乎乎的缺口。然而,大门就这样敞开着,却没有任何人进出。大概又过了五分钟,大门关闭了。
“这是怎么回事?”吕鸿低声问马宇弈。
马宇弈也很不解地摇摇头,去问陆冰月。
陆冰月说:“很奇怪,我也不知道。”
吕鸿说:“是不是我们的行动被他们发现了?我们应该抓住时机,进去看看。”
马宇弈起初不同意,说现在贸然进去搞不好会打草惊蛇。后来吕鸿说那她自己进去,马宇弈没办法,只好同意。但是,他说三人一同进去,目标太大,他一人进去就好了。
马宇弈那天晚上这一去,就再没有活着回来。
吕鸿的思绪被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打断,一看却是个陌生号码。
她接起来,听到里面没有人说话。吕鸿下意识地“喂”了一声,对方还是不回答,只传来粗重的喘气声。
“你是谁?”吕鸿警觉地问。
“你是个聪明人。”说话者听起来像个男人。声音又粗又低,“楚尚岩的身体和孟蝶的脑袋,一定让你想起了不少往事吧?”
“是啊,他让我想起了李家坡侏儒案。”吕鸿察觉此人来者不善。
“你那次差点送了命。”
“算是流年不利吧。”不知为何,吕鸿内心升起一股勇气。她决定和这个人周旋。
“哈哈哈!”对方居然笑了起来,“你不是个会开玩笑的人。不过,这句话倒还贴切。”
“看来,你对我的性格十分了解。”吕鸿说。
“将近十年了嘛。我的眼睛一直没有从你身上挪开过。”那人说。
“你不会是爱上我了吧?”吕鸿没有想到罪犯会主动浮出水面。犯罪分子这样做,往往是另有阴谋。
“哈哈哈!你这是第二次让我笑了。我的炸弹计划是不是很有创意?”
“和你的侏儒谋杀案一样有创意。先生你这么有创造力,该怎么称呼啊?”
“你和从前相比,成熟了不少,越来越会说话了。你就叫我‘索魂者’
吧。看来,咱们非得见见面不可。”对方居然提出邀请。
如此嚣张!吕鸿保持住冷静:“好啊。在哪里见面?”
“等你找到孟蝶的身体,就会找到与我见面的地点。不过,此事只能你我两人知道。”
电话就此挂断。
吕鸿很冷静地思考了几秒。这个电话已经证实她一开始的直觉是对的。今天的案子确实和数年前的侏儒案有关。
她再次拨打高毅的电话,她要把当时发生的一切,包括案卷记录中没有记载的部分,通通告诉高毅。不过,吕鸿已暗自决定,不把今天接到的这个神秘电话告诉高毅,她并不是要对这个自称为“索魂者”的人信守承诺,对待穷凶极恶的罪犯,没有承诺可言。她是不愿意再次打草惊蛇。
“柔洁美”织袜厂里机器声十分纵情地隆隆不断。厂房的背后躺着一片公墓,翻过公墓向阳的山坡,背阴的一面就是李家坡。
高毅和孙立在门卫的带领下,走进了副厂长办公室。副厂长是个外表精明的瘦个子男人。他热情地和高毅握手,问有何贵干。
“楚尚岩楚厂长呢?”高毅问。
副厂长遗憾地说:“不在厂里。”
“哦?”
“你们找楚厂长有事?”副厂长算盘般的眼珠拨动着。看来,他把什么可能性都想过一遍了,就是没想到楚尚岩的死。副厂长一边给高毅和孙立倒茶让烟,一边说,“实话说,我也是两天没联系上他了,真着急呢。他老婆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老婆?”
“对。他老婆叫孔玫,原来是我们厂的厂花,嫁给厂长后就没来上班了。”
“他家住哪里?”高毅嗅到线索的气味。
“就在后面的李家村。楚厂长原本就是李家村的人。咦,二位警官,你们怎么知道楚厂长两天没来厂里工作了?”
“他已经死了。”
“啊!”副厂长手里的烟掉在地上。
高毅说:“请你暂时不要打电话告诉他妻子。我们亲自过去对她说。”
副厂长愣愣地点头,过了好一会儿,才从紧绷的喉咙里问出一句话:
“他是怎么死的?”
“谋杀。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中。”小孙说。
“楚厂长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高毅重新点燃一支烟,递给呆若木鸡的副厂长。
副厂长接过去,狠狠地吸了一口,才把魂儿吸回来,口气仍旧木木地说:“他待员工和下属都不错,人也挺大方,不过,就是有点好色。”
“你们厂效益怎样?”高毅问。
“一直很好。”
“楚厂长身边是不是经常跟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
“没有啊!他身边除了办公室里的女秘书,没有其他人了。”
在高毅和小孙起身离开的时候,副厂长好像忽然想起来什么似地说:
“他最近这一个多月精神状态不是太好。好像有什么心事。我问过他几次,他就是不说。他是厂长,他自己不愿说,我就不好多问。不知这一点,对你们破案是否有帮助?”
李家坡。
李家村。
这里正是吕鸿提起的侏儒案的事发地。难道,那起大案的破获只是个假象,余波未平?难道警方当年办错了案?
楚尚岩的家很好找,村里人都知道。一栋四层白瓷砖贴面小楼,外带一个高墙垒筑的小院。
门是虚掩的。有几只鸡在门后发出“咯咯咯”的叫声。还好,里面没有养狗。
小孙叫了两声“孔玫在吗?”没有听到回答,正要推门,一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女子忽然出现在他们身后。
“你们找孔玫干什么?”她气势汹汹地说。
“你就是孔玫?”小孙问,心里寻思,她这么凶,难怪家里不用养狗。
“这要看你找她干什么了?”
“我们来调查点事情。”小孙露出了警官证。
楚尚岩的家装修豪华,每一件东西都透着金钱堆砌的俗气。高毅没想到卖袜子能赚那么多钱。
孔玫请他们进屋后,不停地唠叨,一会儿责怪楚尚岩手机关机,一会儿说自己打麻将手背,就在她提议再找个搭子,和高毅小孙凑一桌麻将边打边聊的时候,小孙实在是按捺不住了,皱着眉头说:“你老公死了。”
孔玫“啊”了一声,然后咬紧双唇,忽然间一句话不说了。
小孙以为自己刺激到她了,心里正开始内疚,她又长长地舒了口气,仿佛吐尽了长期积压在心中的闷气似的,说:“这下终于好了。一切都结束了。”小孙又想,要是将来讨个老婆像这样,自己非疯了不可。
“怎么回事?”连高毅都被她捉摸不定的脾性吊上了胃口。
“你们跟我来。”
三人鱼贯上了小楼第四层。前三层每层有三个房间,门都是敞开的。
只有第四层,才走到楼梯口,就被一道厚重的防盗门挡住了。
孔玫站在门前,开始撩起上衣,做出解裤腰带的姿势。
“你这是干什么?”小孙又一次被这个女人弄得紧张了,担心她要耍诈,谣言警察侮辱她。
“他以为一把锁就能把我锁在门外,休想。”孔玫从裤腰带上解下一把钥匙,打开了防盗门。
四楼是个一贯而通的大房间。厚厚的窗帘把房间遮蔽得一片黑暗。
孔玫开了灯。
空的。这个房间是空的。没有任何家具,墙上没有任何饰品,白净如洗。只在房间中间,有一个草编的蒲团。
“怎么回事?”小孙惊讶。
“你们告诉我呀。”孔玫说,“半年多了,他要么不回家,要么一回家就躲在这里,闭门不出。”
高毅在房间里走了一圈,掀起那唯一的蒲团,发现一个小小的符号,一个三角形,中间有一个圆形,圆形中间有一个小点。
似乎在哪里见过?
“你老公出门,身边有没有老跟着一个二十几岁的人?”小孙问孔玫。
“男人女人?”孔玫怔怔地看着这个空荡荡的房间反问。
“男人。”
孔玫疯狂摇头:“他出门只会带女人。”
“谁?”
“很多。我一开始还吃醋,后来就懒得吃了,不消化。”
“他还有什么异常吗?”小孙又问。
“这还不够吗?”孔玫转过脸来,两眼直视小孙。
高毅和小孙刚离开楚尚岩的家,没走多远,就听见孔玫声嘶力竭地号啕大哭,如一枚刚发射的高射炮,直插云霄。
“这个女人,怎么让人感觉恐怖。”听着女人唱戏一样的哭号,小孙后脖颈一阵阵发麻。
“这不能怪她,有个不忠实秘密又多的老公,谁碰上都受不了。”高毅忽然停下脚步,转身问,“你还想看更恐怖的事情吗?”
“哦?好啊。”
“咱们走。”
高毅带着小孙离开了李家村,向后山坡走去。
原来,刚才高毅看见蒲团下的图案后觉得眼熟,想起了在汉唐小区的案发现场见过,就给警员白欣发出短信,让她查一查装孟蝶人头的购物袋。
两分钟后,白欣回复说,购物袋内侧有一个图案,三角形套圆形加一点。
古墓门口荒草丛生。地道口在侏儒案后重新安装了两扇木门,一把生锈的铜锁挂在上面。
小孙随便两下就撬开了。尽管外头艳阳高照,墓道中却有一股腥湿的寒气立刻扑面而来,地道内黑漆漆阴森森,仿若那些死去的侏儒还在其中。
高毅刚伸出手,对小孙作出一个“你先请”的姿势,手机就忽然响了。
是吕鸿打来的。
吕鸿把她所知的李家坡侏儒案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了高毅,最后顿了顿难过地说:“那天晚上要不是因为我的无知和固执,马宇弈也不会出事。”
“你不要太自责。如果那天换成是我,我也会忍不住进去看个究竟的。
后来的大火是怎么发生的?你还记得吗?”
“对于那场大火的起源,我也不清楚。当时在马宇弈翻墙进去后,磨山会馆里便火光冲天。大火是从会馆的各个角落同时开始的。后来经过证实,是有人浇灌了汽油故意纵火。分明是要烧毁所有证据。也许,正是因为马宇弈进入了磨山会馆,才打草惊蛇。大火发生后,我和陆冰月好不容易砸开大门,冲了进去。我们在火中寻找马宇弈,可是火势实在凶猛,我们不得不放弃。在消防队扑灭大火后,我们在二姨太居住的房间里发现一间密室,里面有一个被捆着烧死的男人,经宋老师鉴定,正是马宇弈。”
电话中吕鸿的声音中断了片刻。高毅能够想象她此时伤心的模样。
负疚依旧的吕鸿最终定下心神,继续说:“后来,我们成功抓捕了刘惜鹤。据她交代,她的姐姐因为自己身材矮小就自暴自弃,后来在泰国网络上加入了一个叫做‘兰那’的组织。”
“‘兰那’?就是‘八百媳妇国’在泰国的名字?”
“对。刘惜鹤发现,她的姐姐刘倩鹤一开始加入这个组织的时候,心情忽然开朗了许多。然而,就在半年后,刘倩鹤变得冷漠,忽然决定来中国工作。后来,刘惜鹤不放心,也跑到中国来。她渐渐发现,这个名叫‘兰那’的组织,实际上是一个打着帮助残疾人的旗帜进行邪教活动的组织。这个组织认为身有残疾是自己有罪的表征,只有进行集体自杀,才能洗清自己的罪恶,升入美好天堂。磨山会馆是他们夜间进行活动的地点。”
“这也说明为什么会在同一座古墓里同时发现那么多侏儒尸体了。可是,刘倩鹤的尸体为什么是在古墓外的保险箱里呢?”
“这一点,我们一直没有找出真相。我们推断,可能是在集体自杀之前,刘倩鹤忽然改变了主意。对方为了不走漏风声,才杀了她。但是,她这样的人,又没有资格进入墓穴,只好埋葬在墓穴附近。墓穴中的诅咒,特殊的三角符号,侏儒的衣裤,都是兰那组织为了蛊惑人心,一手操纵的。兰那一直是在网上活动,当磨山会馆被烧毁之后,就消失得干干净净。”
“听你这么说,这个案件仍是悬案?”高毅问。
墓穴中似乎传来呜呜的风声,像有人躲在暗处哭。小孙听了高毅对于李家坡侏儒案的叙述,心里越发一阵阵发毛。他有个坏毛病,就喜欢瞎想。
此时,小孙心里发毛地嘀咕:“在很久很久以前,后山坡上有一座古墓,古墓里有一群蹊跷死亡的侏儒……”
“说不定,这趟行程可以让你找出侏儒案的真正凶手。”高毅话打断了小孙越来越恐怖的思绪。
小孙朝前,墓道中若有若无的风把他吹得一晃一晃。
“害怕了?”高毅在后面打趣。
“是风。”小孙搪塞。不就是个古墓嘛,他安慰自己,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土和石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小孙心里这么想着,可是当他走到墓穴边上时,却呆住了。
高毅赶上来,也呆住了。
侏儒案结束后,局里已经运走了所有石棺,清理了现场。这里应该空空荡荡才对。然而,在黑暗的墓穴半空中,却飘浮着一个黑影。黑影像一个倒写的英文字母“V”。
一束细细的微光从道口投射到黑影身上,如同舞台的追光灯。高毅打开了打火机。
一具尸体。
尸体身上只穿有一件长袍,无鞋无袜,被一根绳子从腰间系过,悬吊在墓穴正中。高毅和小孙正要想办法把尸体解下来,尸体腰部的绳子忽然断了,从空中跌落,腐烂的肉体在地面上堆成一摊。
数年后,吕鸿再次走进这个神秘墓穴。古墓苍凉不变,吕鸿的生活已物是人非。
又是这里,又是这略带甜味的尸臭。这个墓穴引发的案件,如同一个无形幽灵,一直附着在吕鸿心上。
墓穴中的尸体头和身体是缝合在一起的,身体属于一个女人。头却是男人的。一看就是楚尚岩的头。
“身体难道是孟蝶?”小孙问。
“很有可能。不过,最后结果要等DNA比对后才能知道。”吕鸿克制住内心的激动,尽量冷静地检查尸体,悄悄寻找索魂者留下的暗示。“索魂者”曾留下话说,等吕鸿找到了孟蝶的尸体,就能够找到与他见面的地点。
这个人为什么要自称“索魂者”呢?这个名字,从字面上看,目的再明显不过了。那么,此人到底要为谁索魂?索谁的魂?吕鸿想起了“二姨太”
的诅咒,凡是进入此墓穴的人都得死。
“马宇弈的事,不能怪你。”高毅轻轻走到吕鸿身边,蹲下来,小声说。
他见吕鸿不言语,好像没听见似的,认为她心思都在那具女尸上,就想吕鸿毕竟是老法医了,能控制情绪。这样一想,高毅略微放了心,又轻轻走开了。
其实此刻,吕鸿的心里早就乱了套。她很仔细地把这女尸的尸身和楚尚岩的头检查了好几遍,却没找到索魂者留下的丝毫信息。
凶手为什么一直玩换头游戏呢?
这会不会是一种暗示?
吕鸿仔细观察尸体颈部,在气管内,她似乎看见一个比拇指还小的小球。
杀害楚尚岩和孟蝶的凶手曾经制造了三起假炸弹恐慌。这一次,会不会也是假的?
索魂者此时在暗处,自己在明处。索魂者的游戏才开始,他不会轻易要自己的命,否则在解剖室里的时候,这人早就得逞了。他是想先和自己玩玩。
这么一想,吕鸿站起来,大声说需要安静一下,请大家都出去。吕鸿的声音有些颤抖,但墓穴的空旷将其掩盖了。
考虑到吕鸿的情绪,高毅挥挥手,所有的警员都依次离开了墓穴。
“请你也离开。”吕鸿对留下的高毅说。
高毅想了想,转身走开。
等墓穴里只剩下吕鸿和那枚可能爆炸的小球后,她抽出了小球。
很安静。没有倒数的计时器,也没有惊恐的爆炸。
小球是个小蜡丸,中间有一条卡合的缝隙,很像一粒微小的中药丸。
吕鸿掰开,露出一张纸条,上面写:梦以昨日为前身,可以今夕为来世。
在睡梦中,把昨天当做自己的前身,把今晚当做自己的来世。这句话是以梦为喻。
今天刚好是自己生日。凶手一系列的计划都是从今天凌晨00:00:01时开始。吕鸿骤然明白,这一切都是冲着她来的。
在磨山会馆被烧毁后,再没有人出资重建会馆。吕鸿记得,在会馆原址上,好像盖起了一个什么酒吧,名字就叫梦喻。
下午的酒吧,一般都空荡寂寥得宛如死人的梦。吕鸿到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并不是喝酒的地方,而是一个手工制陶的陶吧。
这些年,马宇弈的牺牲像重重阴影,悄然笼罩着吕鸿的内心。为了避开这段记忆,她从不来这里,经过的时候,也刻意绕道走,所以,远远地看见招牌是“梦喻”,还以为是喝酒的地方。
吕鸿存了包,换上专门的罩衫,坐下。她的身前有一摊提前和好的泥。
顾客要做的事情就是制陶中最省事也最考验想象力的环节,把一堆烂泥塑成某个形状。吕鸿伸手揉泥,假装做个花瓶,观察起里面的其他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