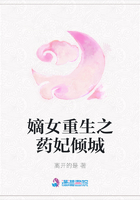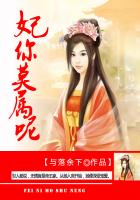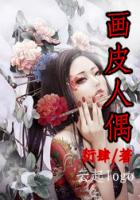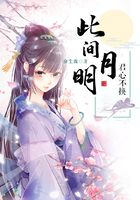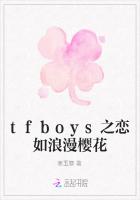孙无忌一愣,面色也跟着凝重一层:“可是陛下,倘若此事为真,也须当机立断。先帝一生,化解多少危难,说来说去不就是八个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独孤元嘉点头:“舅父所言甚是。所以眼下,第一要务便是查出真凭实据来。一来我们才好名正言顺,堵天下悠悠众口。二来也好教他心服口服,再无怨念地认罪伏法。”
孙无忌眉头一皱:“陛下所言虽是正理,只怕时不待人。”
独孤元嘉紧接道:“所以朕才特意请舅父商议。天下虽大,满朝文武,可朕只相信舅父。”
他沉沉地看着孙无忌,孙无忌也抬起头看向他,似乎从他的眼神里感觉到了那一份沉重的信任,忙又垂下了眼睛。
独孤元嘉道:“这件事就交给舅父,五日之内,给朕一个明确的答复。”
孙无忌一惊。
五日。
五日就要将谋逆大罪查个清楚,实在太短。可五日若真用于谋逆,却业已足够。
当年,神武门之战,隐太子、巢刺王谋逆,先帝平叛也不过就是一朝一夕的事。
孙无忌感觉到了棘手。皇帝到底是出于信任,急着要他查清事实;还是因为心生怀疑,要他自己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大约是看到他的犹豫,便听独孤元嘉又道:“朕也知道,五日就要舅父查清谋逆大罪,实在是强人所难,但除了舅父,朕也无人可托。不管怎样,你们都是朕的血肉至亲。”
孙无忌心中略动。想起皇帝自小就有一副仁义心肠,又亲眼见过废太子同魏王争权,位正东宫之后,便一心善待诸亲。登基以后,更是下令为濮王营造府邸。皇帝虽是不说,孙无忌却也明白,皇帝是不希望再发生兄弟相残的故事。如今却有人告诉皇帝,他极力避免的故事又将重演,他怎么能轻易接受?
唉!
一时间,孙无忌也感慨良多。
当初,他力排众议,既不尊废太子元乾,也不拥魏王元泰,更不立吴王元恪,几次三番在先帝面前力保时为晋王的皇帝,也就是看在皇帝的一副仁义心肠上。
其实先帝虽十分疼爱皇帝,甚至让他自小住在甘露殿,却没怎么想过立他为储君。这就和民间老父疼爱幼子一样,喜欢幼子喜欢得让他时时刻刻就在眼前,巴不得为他把一生都安排妥当,但要说起继承家业、支应门庭,却又另有打算。
先帝不止一次地说,吴王元恪英武类己。废太子、魏王两败俱伤后,先帝的心思就落到了吴王身上。因孙无忌一口咬定吴王非嫡出,有一回更是气得先帝直指着他的脸面问,你这样偏袒元嘉,难道是因为元恪不是你的亲外甥?
孙无忌仍是丝毫不让,申之以嫡庶大义。
先帝毕竟是个英明的帝王,这口火气咽下去,却也知道孙无忌说得有理。况且,吴王虽贤,皇帝也不是不肖。皇帝自小在他身边长大,他又怎么不知道皇帝是个什么样的人。思来想去,才在最后采纳了孙无忌的建议。
就是这样,皇帝入东宫之后,先帝也不是没动过改立的念头。只不过,孙无忌太了解先帝,一旦感觉到先帝心动,便抢先将那萌芽掐断。这才让先帝死了心。
可如今,皇帝当断不断,却将这烫手山芋丢还给他,也是因为这一副仁义心肠。
孙无忌也不由得在心里暗暗自嘲:这算不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呢?
然而皇帝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他自然不能再推脱。起码皇帝有一句话说得很是,谋逆事关重大,是要诛九族的。如此重大之事,交给他总比交给别人好。
便朝着皇帝深深一拜道:“老臣遵旨。”
皇帝似是松了一口气,朝着孙无忌微微一笑。
孙无忌临退走时,皇帝却又叫小内监取来两枝百年老参。
“听说舅母近日身上不大好,”独孤元嘉关切地道,“这两枝老参给舅母补补身子。”
孙无忌忙道:“已经大好了,岂敢劳动陛下挂念。”
独孤元嘉笑道:“朕知道舅父府上也不缺这点儿东西,这不过是朕身为晚辈,略尽心意罢了。”
孙无忌不便再推,忙向皇帝谢恩。
待孙无忌退出殿外,皇帝叫高有忠招来郑尚宫。
郑尚宫即是左尚宫,也是宫里的老人了。她先是侍奉孝和皇后,孝和皇后归天,便又侍奉先帝。今年也有四十开外,却还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可见年轻的时候,更是个叫人心动的美人。
独孤元嘉道:“眼看着重阳节就快到了,宫中还有几位太妃,吃穿用度须仔细些。”
先帝归天后,没有生育的嫔御一率送入感业寺修行,生育过的嫔御则迁去大安宫,同太祖的几位嫔御作伴。皇帝对几位太妃一向照拂有加,隔三差五地便会派郑尚宫送去珍馔。
郑尚宫笑道:“奴婢遵旨。奴婢先向惠妃娘娘请安,待惠妃娘娘仔细示下,奴婢再去拜见几位太妃。”
因宫中无后,实际由惠妃苏冷月打理后宫一切事务,因此郑尚宫才说先去向惠妃苏冷月请安。
独孤元嘉淡淡地点了点头。
且说惠妃苏冷月也没闲着,皇帝这么多日子没来她这里,也没去任何嫔御那里,一直待在甘露殿,早引起了她的注意。是故,宫人一禀报郑尚宫求见,便被她即刻宣入。
郑尚宫满面笑容地向苏冷月行完大礼,讨好地笑道:“奴婢几日不曾拜见,惠妃娘娘越发光彩照人了。”
苏冷月笑着全盘接受:“郑尚宫可算来了,想必近日忙得很。”
郑尚宫笑容微微一滞,仍是陪着小心道:“在惠妃娘娘面前,奴婢哪敢放肆。实在是奴婢庸人一个,若是能沾上惠妃娘娘一星半点的聪慧,也就不必忙成这样了。”
苏冷月笑着轻啜了一口茶。司琴也不觉抿嘴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