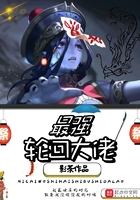“嘶……”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外落到我紧皱的眉间,我紧紧捂着胸口,弯着腰,想要减轻胸口的痛。
不,确切的说,痛应该是来自我胸口的那颗痣。那颗我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血红色的朱砂痣!
我出生在炎热的六月,火红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产房的走廊被闷热的空气笼罩着,护士给我裹了一层薄薄的棉布就塞给了我爸爸。
焦躁不已的我,紧闭着双眼,挥舞着手脚,一不小心就让爸爸看见了我胸口的那颗还不算血红的痣。
“啪……”一声脆响伴随着爸爸略带愤怒的声音,“死苍蝇……”
这颗痣注定让我的出生比别人多了一道疼痛,那是来自父母对我的溺爱,就像是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的脚踝,仿佛注定是我一生的弱点。
爸爸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在80年代的时候,能当上教师,那他的知识水平是很有含金量的。我在爸爸的庇护下,顺顺利利,稳稳当当的考上了大学。
我的前半生很平静,很顺利,波澜不惊。一如我胸口的那颗痣,安静的随着我的年龄默默的变化着,从以前的芝麻大小,变成现在的黄豆大小,从之前的墨色,变成现在宛如滴血的红。
除了洗澡的时候,我低头注视它一会儿,基本上我都是忽视它的,直到26岁生日那一天,在爸妈抢过我的生日蛋糕,许愿我快点嫁出去的那一刻,它突然疼了起来,像是被一根针轻轻的扎了一下。猝不及防的,和刚出生时候挨的那一巴掌一样,让我愣了几秒钟后,才叫出声来。
那一夜,我破天荒的做了一个宛如身临其境的梦,梦的一开始充满了恐惧,我似乎被一种很恐怖的东西追赶,我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只知道梦里我一直在不停的躲着它,甚至好几次我能感觉到它的逼近,却仍然看不清它是什么,直到我精疲力尽,已然绝望的时候,一个人忽然出现在我身后,紧紧将我护在他的胸口,随着耳畔那句温柔的话语:“别怕,我一直在”,我便进入了深度睡眠。
虽然我睡眠质量一直不好,经常会做梦,但是在梦里我都知道那是梦,可是这个梦却让我分不清真假。
第二天我拿着医院的检查单,从医生办公室里木然的走了出来。脑海里浮现的是医生的漠然:“你这颗痣是良性的,突出浅表皮层的黑色素,没有恶化的现象,你要是觉得看了二十多年了,烦的慌,可以用激光点掉。”
当医生说出点掉的时候,我的痣又被扎了一下,我摇摇头离开了医院。
回到家,便看见外婆拿着一张黄色纸符神秘兮兮的和我妈在探讨着什么。
“破了?这个人会不会是个骗子?”妈妈面露苦涩。
我的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
“不可能的!这个算命的会过阴,请了一尊阴间的大神才问出来的,我们家鸾鸾是童子命,据说这个童子命分真童子和假童子,难就难在,鸾鸾是真童子。我把你给的鸾鸾的那套衣服给他了,他说只能以假乱真,先破一破,日后找个八字过硬的,也能成,只是姻缘这个事可遇不可求”
妈妈被外婆神神叨叨的样子,唬的不知所措。
我轻轻咳嗽了一下,两个人才发觉屋外的我。
外婆用胳膊肘轻轻的捅了捅妈妈,一双眼睛滴溜溜的暗示着什么。
妈妈慌忙收起黄色纸符,笑着说:“鸾鸾回来了啊!”
我装作什么都没听见的样子,和她们打了招呼,便回房了,心里却断定,她们肯定是上当了,算命的很多是在玩文字游戏,什么姻缘讲究缘分,只是在推脱自己的责任,如果就此可以结婚,就算他的功劳,如果不能,他也可以归结为缘分未到。
不过当真是缘分未到,转眼间,已然二十九岁的我已经成了大龄女青年,依然单身,每次恋爱都坚持不到三个月,不论以多么甜蜜的开始,结局都带着狗血的悲伤。
就这样走走停停,我便剩了下来。
欢欢喜喜的参加了最后一个单身闺蜜的婚礼后,我终于有了一丝怅然若失的感觉。不论走到哪里,总觉得身边冷冷清清,二十九年来,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孤独。
走在夜雨朦胧的街道,我抬头看着屹立在雾气中的那盏路灯,昏黄的灯光下飞舞着的雨滴,透着说不出的哀伤,忽而想起二十六岁生日那晚,出现在我梦里的那个男子,几年间,我不停的梦到他,每一个梦里,他都是在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将我护在他的胸口。
我曾经很努力的想看清楚他的面容,却总是在睁眼的那一刻,忘记的一干二净。唯一留在我记忆中的除了温暖的胸口,便是他让我沉浸难以自拔的声音:“别怕,我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骗子”我将自己埋进洗澡水里,透过荡漾的水浪,胸口的那颗朱砂痣红的像是要滴出血来。
洗完澡,躺在床上,我用手机百度了一下“胸口的朱砂痣”,发现说法五花八门,倒是有一个回答吸引了我。
“胸口有朱砂痣的人,会隐藏着前世的记忆,因为前世死后不愿意喝孟婆汤,所以被孟婆留下了印记。”我默念着,手指轻轻抚摸着那颗朱砂痣。
梦中的你,会是我前世的记忆吗?
“别跑,你是我的!”略带戏谑的声音从浓雾中传来,我慌不择路的跑着,似乎想要离身后的浓雾远一些。
莫名的我排斥这个声音,霸道中带着玩弄的语气让我很不舒服。
“别怕,我一直都在!”我再次落入那个熟悉的温暖中。
是他,他来了,刚才慌乱的心似乎一下子安定了下来,身后的浓雾也渐渐散去,一个高大的身影若隐若现。
“她是我的!你休要碰她!”追我的那个身影似乎有些愤怒。他伸手想要拉我,却被拥着我的人挡了过去。
“鸾鸾一直都是我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我的,你们使用卑劣的手段想占有她,我不可能袖手旁观!”沉稳的声音从我头顶掠过,我抬头,注视着他的脸,那样自然而熟悉的感觉,似乎我们已然相识千年。
“小子,我劝你还是离开她,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鸾鸾,别看了,快醒醒!”他眉间焦急,如星的双眸透着焦急。说话间他推开我,已经伸手挡开那人挥来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