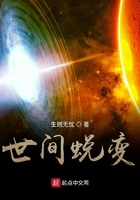跟在战时的中国坐在三等车厢的旅行比起来,纽约高峰时期的地铁反而成了天堂。我们去潼关时坐的车就像鱼罐头一样挤满了人。
中国人本质上是很我行我素的。几个世纪以来的生活方式使得不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都养成了自扫门前雪的习惯。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早就已经众所周知,人们对于旁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给别人造成的不便也很容忍。比如,如果车站上的一个男人隔着车窗把他的大捆行李扔在了乘客的膝盖上,乘客稍作反抗后又有五个包裹扔过来。这事引起了人们的哄笑,不过大捆行李被放在了走道,成为了可以容几个人坐的座位。
在潼关下了车,穿过了一排贩卖小食品和开水的小贩后,我来到了八路军在当地一处外墙糊满黄泥的建筑物内的办事处。我们要在这里过夜,这儿的人们带着我看了看我将要在上面过夜的长板凳。
河对岸的南边高地就是这趟窄轨铁路的终点站风陵渡村了,这条铁路向北二百九十英里就是现在正处于日本人控制下的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府。黄河由西向北流经风陵渡,从村子所在的高地脚下急转向东流去。发源于西面的渭河和洛河就在此处汇入黄河。
潼关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的任务就是为西安抵挡来自南部和东部的敌军。日军在几个月里就夺取了风陵渡高地,但是他们的军事扩张也就到此为止了,这群人还没有准备好为了横穿这里而做出牺牲。
第二天的时候,我们下了高地到河边上了一艘小帆船,在湍急的水流中行进了半英里后抵达对岸。整个南岸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仓皇从太原府军械库调遣来的军械设备。不久,南岸将会重新成为世界聚焦的焦点,而木板条又将成为中国军队急需的军需品。
因为山西的火车在夜间不运行,一辆年久失修的公共汽车在风陵渡等着我们。我们每人要了一碗面条填饱肚子,周围的男人们、女人们和小孩儿们都站在我们身后,好奇地看着几个面色红润的外国人笨拙地用筷子吃着面条。
“走吧!”公交司机大声地呼喊道。我们整装上了车,汽车很快向北拂尘而去。对于我们的目的地我仍旧一无所知。的确,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有时我从早上睁开眼就要开始思考晚上将在哪里过夜。除了接受即来的事件外我们也别无他法。
在那天的晚些时候,我们看到了类似县城的城墙样物体。“到临汾了。”随行的工作人员解释道。
临汾是这个省新的省会,若想前往临汾的话必须要再走一百三十英里。由阎锡山将军领导的当地政府就座落在那里。
在一座石制大门前有人挥手让我们停下,几个青春洋溢的士兵用洪亮的声音欢迎了我们,他们的手臂上还戴着刻有八路军标志的徽章。显然,他们中的有些人是我身为卫队成员的同伴的老朋友了,他们都互相对对方挥着手,然后友好热烈地相拥在一起,嘴里还大声说着“欢迎啊,同志。”
军队的后勤部副部长杨立三将军热情地接待了我。过了一会儿,他招待我洗了脸,吃了一顿豆芽、米饭和鸡肉烹制的便饭,这顿饭在这个地方已经是盛宴了。
但是这一天的旅程到此还没有结束。大概因为我是到此地来的第一位外国政府人员,晚饭后杨将军盘问了我拜访军队的原因,我能够看地出他们对于我的动机有所顾忌。然而,下午的时候我接到通知,我将被送往汾河西北方向的领导人培训学校。一个小时后我和另一个士兵兼向导的人一起漫步回去。临近黄昏时我们到了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小山村。
这个小村子仿佛因为诚挚友好的同志情谊而散发着光芒。除了老人、妇女和小孩以外,其他人都穿着平纹蓝布的军队制服。大约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女孩们把她们的蓝色军帽帽檐拉过了黑色的齐刘海,无所顾忌地同年龄差不多的男孩玩耍在一起。村民之间也相处的其乐融融。
我被安排前去这所学校的校长——彭雪枫将军的办公室。彭将军本人约四五十岁,精瘦且精力十分充沛。随后而来的又是一场盘问。很明显,我坦诚的回复让彭将军十分满意,于是他接下来向我解释了关于这所学校的办学目的。
这些青年男女在这里接受训练以成为游击战的主力。如他所描述的,游击队的队员都是在这一紧急时刻自愿加入军队的。他们以连、营为单位,大部分都是就地招募,受 训后在他们对其地形地貌有所了解的地方组织形成抗日力量。
三男一女四位学生就是这个学校的全部教员。每门课程持续九周的时间,学生毕业之后就离开学校到日军后方组织游击战。课程的内容中百分之六十是军事策略和技术,尤其要学习老游击队员的实战经验。余下的就是些政治课了,学生们接受代表政府的基本原理的教育,学习如何组织社团,以及社团里个人及团体的道德准则教育。
第二天彭将军(我发现他只是个“同志”)陪同我参观了学校的教室和宿舍。学生们搬着自己的凳子在各个房间窜来窜去。课本都是油印的小册子组成的。课堂教学的形式让人联想起美国大学的教学,学生们做着大量的笔记,老师在黑板上画着示例图给学生讲解。
学生的宿舍非常整洁。学生们以十一人或十二人为一组分享一间宿舍。中国北方的卧室里有一个升起的高台,他们管这叫做“炕”,从这一面墙砌到另一面墙,被北方人当成床使用。炕的基底用砖围起,底部用石头垒起,抹上泥后就相当于一个火箱。在炕上睡觉感觉就像睡在了灶台上。一般情况下,人们在炕的一端生火(有时在屋外),生火产生的热量大小视睡觉的人距离火箱远近而定。中心是整张炕最舒适的地方。
这些房间里的炕要分配给班里的每个人。白天时被子要整洁地叠放在每个人的床头位置。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也都要求统一摆放在指定的地方,甚至连牙刷和毛巾都有各自特定的位置。如此整齐划一的军容军表真是让西方军队感到汗颜。
到了晚上,学生们会分成小组围坐在木炭火盆旁讨论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有一个小组对于诗歌感兴趣,而另一个小组却置身于绘画当中。其他的在研究音乐、文学或者手工艺术。晚上10点钟时他们就回宿舍休息,准备迎接新的一天。
他们告诉我,爬山是每个学生必须接受的训练之一。第二天早上我跟我的同伴一起加入了餐前早操的队列。天亮之前他们整好队伍前往村后的小山。爬了十五分钟后我们碰到了一连串的台阶,大约能绵延一英里至山顶。
学生领袖把男性分成了几个小队,每隔五到十步安排一个人。
“注意看着我给的信号,“他说,“我要看看你们谁能最先到达最上面的台阶(大概一英里的距离外)。”
他口哨声一响我们立刻出发,叫喊声,笑声,在这条小窄道间碰撞着,声音随着人群沿着阶梯向上蔓延。没有几分钟的时间学生们就在山顶集合了,大声地喘着气扇着风,浑身都散发着生命的活力。
他们围站成了一个圈唱起一些为新中国而写的振奋人心的歌曲,他们的声音激情迸发,声音穿过了他们脚下那个连汾河也渐渐消失于彼的灰色山谷。
我该给他们唱首美国歌曲吗?不,但是我会用我的口琴演奏一曲。我的嘴唇适应了乐器后开始酝酿要奏一曲陆战队的战歌——《火海浴血记》。没多久他们就一起哼起了曲子。当他们又整队开始向斜坡下齐步走去时,两队人马还哼唱着这首美国陆战队的歌儿。
彭同志有新消息给我。南京已经陷落,美国的班奈号炮艇也被日军的炸弹击沉。细节的缺失让我陷入了沉思,思考这一事件带来的影响都是什么。我那些领事馆的老朋友在不在舰上?美国本土那边是什么反应?1898年时梅因号沉没的历史又再次重演了吗?这次的事件是日本蓄意策划的吗?因为缺乏更加深入的信息,我决定将我的旅程进行下去。
“如果你想的话,今天就可以去军队的司令部了,”彭同志知会我道。这真是鼓舞人心,此前我正因为行动被限制而感到十分懊恼。
司令部在北边二十英里的地方。他们给我准备的是一匹从日军那里虏获的瘦高而笨拙的马,马鞍已经备好了。下午的时候我们上路了,小刘——我年轻的保镖、一位背夫,还有个专门驮行李的牲畜。
快到傍晚时我们到了一个看起来很祥和的小村子,顺着一捆电话线我们到了一个一眼看去就知道是军机重地的地方。
我把马拴在了打眼的地方后观察了我的四周。向我走过来的是个健壮结实的男人,中等的身高,穿着平纹蓝布的制服。他古铜色的饱经风霜的面庞上带着热情的微笑,他伸出的手正试图握住我的。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这个人就是朱德,就是那位享誉全八路军的领导人。而且直觉还告诉我,我交到了一位暖心慷慨的朋友。
没有一张照片能够不失真地记录下朱德,因为没有一张静止的照片能够准确描绘出他富有活力而又散发着善良友好的气息的脸。在接下来的那一个月里我逐渐发现,朱德受到了他部队里每一个人的爱戴。只要在老兵的面前提起他的名字,老兵的眼中就会出现柔和的目光。“朱德?啊!朱德啊!”他们会兴奋得说不出话,语调中也传递着他们对于朱德的爱戴之情。朱德带领着他们经历了上千场的战斗,他与这些官兵们同甘共苦。不管环境有多艰苦,他对于每个身边的人都坦诚相待。
在与他共处几个小时之后,我理解了那种感觉,短短几个小时的相处后我就能够完全信任他。
他身上的贵族气质使他与众不同。他性络中的无私、友好、耐心,使他浑身散发出别具一格的人格魅力。他乐于接受别人的批评,说起自己的成就时非常低调,对于军队现在的处境也有着发人深省的看法。
这个男人的生活在他四十岁那年出现了巨大变革,并且决定下半生致力于带领他的同胞走出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双重绝望。他带领红军从南部的江西省历经了六千英里的长征到了大西北。
后一周的时间里,当我跟着他的随从在山上远足时,我更深层次的认识到了朱德非凡的个性。我总结出他拥有着三种卓越的性格,我把这些性格转化成了易于理解的美国的名人。我感觉,他有着罗伯特·爱德华·李译者注:美国将领。的亲切,亚伯拉罕·林肯译者注:美国政治家,思想家,第十六届美国总统,任期内爆发南北战争。的谦恭,和U·S·格兰特的顽强意志。
第一次的见面时他带着我穿过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式住宅的院子(房屋将一个院子围在中间)到他的司令部。屋子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供睡觉的炕,一头放着一个壁柜。墙上挂着一张山西地区的地图。我们在这儿用中文聊了一会儿后翻译就进了屋。原来这个翻译也是我的老相识——周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