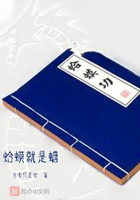乔山危急之时被他救出,本应心生感谢,但不知为何看到司马楠那一脸谦卑的笑容,想起刚才他满面笑容之下忽然出手对付昆仑两英的手段,而且轻易认出了自己,心中反而生出几分说不出的恐惧之感。
司马楠见他神情有异,微微怔了一下,连忙上前两步将他的穴道解开,扶起乔山道:“乔公子勿要惊疑,今日一早在妙明寺前,公子已露出了形迹。公子的形貌……虽然大有改观,但口音步态却还是能让人心起疑心,老夫一直悄然尾随公子,只想探明真相,刚才公子面临危机,老夫不得不出手相助。这昆仑双英的武功并不高明,但身法特异,老夫若不使诈,只怕不仅救不下公子,自己也不能全身而退。”
乔山知道自己形迹已露,抵赖也无意义,只得拱手致谢。司马楠引乔山从偏门出了乔府,出门之时道:“公子有所不知,此所宅院,皇上已赏赐给翰林学士刘铮,以后乔府便成了刘府了。”乔山回头望去,呆立了片刻,也无一句言语。
这次去的地方又是芳华堂,四月前乔山激愤之下,出走芳华堂,今日却又回到此处,只觉冥冥之中,万事皆有定律。洗浴洁面,梳理熏香,换了了一身干净的袍子,乔山依稀又有了几分翩翩公子的味道,只是头发稀疏凌乱,面孔浮肿难消,看上去仍然去不掉那分奇异之貌。
芳华堂的仆役奉上茶水点心退后,司马楠赞道:“腹有诗书华自华,乔公子略微梳洗一番,便又有了人中龙凤之姿。”乔山一直对他这般谦卑之态心有余悸,只是淡淡一笑,并不说话。
司马楠饮了些茶水道:“那日在六和塔初见,公子便婉拒了凌云先生之议,其实凌云先生极其看重公子之才华,可惜人各有志,公子自有高见,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些老夫都领会得到。凌云先生中当世高人,失望之下,却也不会对公子心生芥蒂,后来……天有不测风云,凌云先生知晓了乔家的遭遇,也曾托人多方探听消息,以凌云先生之能,当然能够获取外人所不知的事情。”
乔山心中也知道凌云先生野心极大,原本是想对他敬而远之,但此时乔家遭此大难,可托的二人蒋柏青不幸身亡,陆华轩退避三舍,唯一可指望之人也就是凌云先生了,听到司马楠又提到他,心中不免已有所动。
司马楠观他神色,又道:“凌云先生所知,远非我这些下人所能了解,不过,老夫曾无意听到一个秘密,此事只恐与公子,甚至与乔家之命运都有无法推托之关联了。”他心计了得,边说边察言观色,见乔山神情已有所变化,又低声道:“老夫虽是大理国人,却知道几十年前,大宋中有一位名动天下的相士,能够洞悉天机,这三朝天子的即位时辰,甚至大宋国的命运气数皆在他心中一一有数。”
乔山道:“莫非这位相士就是那位栖崖老人?”
司马楠道:“公子果然博闻强记,确实就是那栖崖老人。他智慧高妙,洞悉天机,却又抛不开世俗名利,忍不住把这些预测之事一一泄漏出来。话说天意难违,泄漏天机必遭天谴,他为此四十眼盲,五十失聪,六十下肢瘫痪,一生虽然富足,却凄苦孤单,并无子嗣传人,传闻栖崖老人留下一部小册子,记载了此后百年之重大变故,这册子名为《天眼拾遗》,栖崖老人病故之后,《天眼拾遗》便成了朝廷中人人争夺的对象。”
乔山道:“在下多次听闻我乔家似乎有一本什么武林秘笈,引得众人觊觎,我乔家遭此大难和这小册子有关吗?”
司马楠道:“江湖传闻中的武林秘笈与《天眼拾遗》倒不是一回事。老夫略有所闻的,是与这《天眼拾遗》相关之事,那本书几经周转,曾在某一时段,凌云先生也曾目睹此书。可惜那书到凌云先生手中之时,辗转多人,几番争夺,竟然缺了数页,此书又是栖崖老人盲眼所书,用语隐晦,字迹重叠不清,但可辨认之字中,隐约可知似乎大宋之亡,也在书中确有记载!”
乔山心中一惊,他以前也曾听说那位栖崖老人洞悉百年天机之事,一直只当这是民间传闻,并未多加留意,如果司马楠所言为真,难道这繁华昌盛的大宋,如今已不到百年的气数,又想到司马楠多次提到他是大理国人,难道他心中还有他图?他这一番思索,神情间自然便流露出来。
司马楠笑道:“我看公子刚才神色不善,可是对以为老夫对大宋江山有所图谋?其实公子多虑了,老夫虽是大理国人,但追随凌云先生已有数十年之久,只知忠于主人,并非为大理国所想。”
乔山问道:“刚才司马前辈称此书和我乔家的遭遇有关,难道此书中亦有提到?”司马楠摇头道:“老夫福缘浅薄,未能观得此书,不知其中有何深意,实在不敢妄言,但凌云先生必定知道其中某些缘由,公子若要知晓详情,还是须得向凌云先生请教才是。不过今日凌云先生尚在湖州,待他来临安之时,老夫自会引公子与他相见。”
乔山沉吟了片刻,又轻轻摇头,司马楠笑道:“公子还有什么疑惑之处尽管直说,老夫虽然愚鲁,但有所知,必不隐瞒。”乔山道:“在下原本想亲眼一睹此《天眼拾遗》,不过如此神物,刚才所思也许只是痴心妄想。”
司马楠却道:“如此书尚在,老夫以为凌云先生决计不会对公子藏私,以公子之智慧来共同参详,必然从中所获更多。只是《天眼拾遗》在数年前,已从凌云先生手中丢失……”他忽然止住,凝神聆听片刻,才又压低嗓音道:“传闻此书已到了宰相韩侂胄手中,韩大人正是仗了此书,才能这些年逢凶化吉,职位攀升,权倾朝野。”
他见乔山神情并无兴奋,也无喜悦,便继续道:“凌云先生近日即来临安,许多事情老夫所知有限,也不敢多言。请公子耐心静待数日,或许能解得许多疑惑。公子遭遇令人同情,暂时在此芳华堂中歇息几日,恢复些身体,你看如何?”
乔山起身道:“前辈心意在下领了,今日既蒙前辈相救,在下心中感激万分,此种恩义难以相报,不敢再受恩惠。”
司马楠道:“公子此言差矣,若要成就大事,何须固执于此等小节?老夫所为,一是听从凌云先生之命,二是老夫本人一向仰慕公子的才华风骨,公子不必为此不安。”乔山道:“恕在下直言,正是因凌云先生心志高远,在下恐不能相助,所以心中惶恐,只怕辜负了前辈一片盛情。”司马楠见他如此潦倒,居然也不肯多受恩惠,心中不免有些不以为然,便道:“既然如此,那也不必强求,老夫送你回去便是,老夫现在就住在这芳华堂中,公子若有什么指教,到此处来寻我便是。”
二人又回到小巷中,乔山见到那破旧肮脏的窝棚,心中忽生一种亲近之感,一把掀开门帘,见胡七背朝自己蹲在棚中整理东西,似乎感到了身后有人,胡七忽然一惊,一把铜钱跌落在地上,回头见是乔山,便骂道:“人吓人,吓死人……咦!阿三你在哪里发财了,换了一身新衣服,老子差点没认出来。”
乔山笑道:“遇到一旧友……”他转身去看,见司马楠已转身离去,就这一两句话间已走出好远,胡七跟了出来,看着司马楠的背影,眯起眼睛道:“旧友,旧友!老子以为是个小妞你的老相好呢?却还是个老头子!”忽然他转身过来,伸出手对乔山道:“旧友给过你银子没有?”
乔山摇摇头,回到窝棚中长长吐了一口气,躺下闭目养神,觉得这里比住在舒适的芳华堂中更为自在如意,司马楠武功高强,态度和善,循循有礼,但在他心中始终不敢与之亲近,总感觉他笑意背后藏了极深的机心,倒还不如凌云先生那般直言其事来得果断。几日后见到凌云先生,或许可从他那里获知一些讯息,只是自己一无所有,却不知能拿出什么来换取,乔家蒙冤的罪名就是谋反,如果真要助他成就大业,岂不是真正成了谋反大逆……想到这些,乔山心中烦恼又生。
耳中听到胡七道:“阿三,你既是逃婚出来的,在临安可有什么相好?胡七哥哥今天高兴,带你出去玩玩如何?”乔山又一次听到他说“相好”二字,阿莲的甜美笑容忽然跃入脑中,心中如遭重击,几月时间过去,也不知阿莲现在如何了,想来是应当知晓乔家已遭遇大难,也不知她心里作何想,那日从横渡离开时久拥阿莲,那份温软似乎还在怀中,仿如那已是多年以前遥不可及之事。
又听到胡七的声音道:“阿三醒来!哥哥看你神色不正,真在想你以前的相好吗?”乔山睁开眼,见胡七不知从哪里找出来一身干净的衣服换上,头发也梳理了一番,他身形高大,挺了肚子站在窝棚里,倒也很有几分气概,不似乞丐模样,只是他面容肮脏,嘻皮笑脸的看上去极是滑稽,乔山看他眼神中闪过的几丝狡狯之色,忽然明白过来,白日里在妙明寺旁,他给过一断腿乞丐几个铜钱,那时便觉得那乞丐的眼神似曾相识,显然就是胡七假扮的了。
乔山道:“嗯,怪不得能骗到钱使,你那宝贝木盒里不是仅仅能扮断腿吧,什么断胳膊断手也是可以的。”胡七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道:“小子果然有几分聪明,正好你也换了衣裳,咱们出去快活快活,这临安的似花舫、凤鸣阁咱们的确花不起那钱,但浣花街的小妞其实也不赖呀,走!哥哥出钱。”
乔山摆摆手道:“在下无此癖好,这事还是免了,你自己去快活吧,如果有心,记得带点酒回来。”说完便倒下缩入棉被之中,不再说话。这浣花街是临安著名的烟街柳巷之一,价钱极是便宜,乔山心中自然清楚,他原本也不屑于去这些地方,何况刚刚念及阿莲,心中苦楚万分,只想痛饮一场,沉沉睡去,忘却这些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