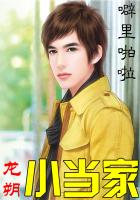寂寞的公路上,两辆越野车马不停蹄地奔跑着。
全面车内坐着路雁和薛峰,而李艳被刘强带着在后面的车里,李艳是路雁故意支开的。
终于越过了省界,李艳才缓缓地开了口。
“说吧,我是不是太由着你了?这是什么?”抖着手里厚厚一沓账本,李艳面无表情。
薛峰暂时放慢了车速,看着路雁较真的样子,只得无奈地说:“哎呀,就是偷个账本,也将他们支出去了。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这不是因为露脸了,才跟刘强赶紧往远处撤吗?”
“是吗?”路雁很怀疑,“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账本就这么轻易被你偷出来了?刘强跟你一起去的?为什么你带他不带上我?论拖后腿,我觉得他比我强!”
路雁对自己的功夫还是有些自信的,刘强那三脚猫功夫,她最多三分钟就能撂倒他。
“放心,你的用处在后头。祖国人民离不开你!”薛峰嬉皮笑脸,车子却被他开的又快又稳。
“你说这次我们去哪里?找我亲生父亲,一定要带上李艳吗?”路雁非常不解。
要她说,直接把李艳放到哪个养老院,顺便交接给警察最合适。
“是的,必须找到你的父亲,确认你的身份和你母亲的身份。只有李艳才是当年的人证!”薛峰不知道在想着什么,说的话让路雁感觉到非常坚决。
“你想把我留在我亲生父亲的身边?”薛峰的斩钉截铁,换来了路雁的一连串的怀疑。
带着李艳,找到亲生父亲,然后呢?李艳就可以被安全保护到能当庭做人证的那一天吗?除非自己也一同留下。
那么,薛峰呢?在老虎窝里直接掏了几掏,偷出了账本,那些人岂会善罢甘休?
难道薛峰这次建议自己先找到亲生父亲,只是为了让自己和李艳留在这里,而他却要一个人单枪匹马,续将一系列的证据收集齐全后,公布于众吗?
想到这里,路雁坚定地说:“我不要一个人留下。我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参与,这不是儿戏。”
路雁的坚决让薛峰很无奈,这个女人总是那么倔。不过,他喜欢没办法。
两天以后,一行人来到了一个繁花盛开的小镇。
然而,在这个大家辗转反侧方才找到的小镇,绕了三天也没有找到李艳嘴巴里的那个姓宋的人。
看着李艳梳洗干净之后,面色温和,眼神中闪着愧疚,路雁也不忍心责备她。
“艳儿姨?你确定是这里吗?”路雁看着李艳。
“是啊!就是这里。二十六年,你妈妈说,在这个繁花盛开的小镇里,有一个姓宋的知青,说好了在这里等她。当年,你爸爸确实是在下放当知青的时候,才和你妈妈认识的。”李艳也有点着急。
“下放知青,即使回到自己的故乡,这么多年了也不一定还在这个地方了啊!算了,艳儿姨,我们走吧!”路雁有些失望,微微叹了一口气,低着头,揉了揉太阳穴就想走。
“唉!大婶儿,你们这边哪家人家是姓宋的啊?听说,是以前这里的老住户,那会子,他家家门的大院前,长着一棵两人合抱的枣树,是在村东头的。”李艳依然不死心地拦住人就问。
就在她拦了三四个,拦到第五个人的时候,居然真有个人说了点有用的。
原来这里两年前拆迁,改建花镇。当时除了愿意留下来承包花田的人没搬走,其余的住家户当时走掉了百分之七十。巧的是,当时留下来的就有一户姓宋的人家。
这宋家,早几十年前,就是本地老住家户。就一个儿子,父母死得早,儿子就离家闯荡去了。
而这家里的这个儿子,据说原先出去闯荡后,就在外地做大事了。不知怎么的,这年纪大了,反倒回来承包了一大片花田,种起来花。性格也很古怪,从来不见他出来跟人说过话,更别提主动跟村里人交往了。回乡后,就一个人住在花田尽头的一间草屋里。
这草屋原先就只盖了两间,后来,这房子在不知不觉之间,竟盖出了一大片。
现在这镇子里最正儿八经的种花的,其实就是这家了。但是因为这家人几乎不出来,花田也是有雇佣花农,定期上山开坑种植。慢慢地,熟悉这家花田的,并且定期上山送日用品以及干活的人们,都叫这家人为“大老板”。而忘记了,两年来,全镇最大最有钱的的这家花农其实就是二十多年前的老人家宋家。
听了这个老乡的话,几个人确实觉得很意外。
原来这里真有个宋家,也真的是有个跟李艳口中年龄相仿的那个宋姓男子。那个可能就是路雁生父的男人。
上山找到宋家花田的时候,已经临近傍晚。一行人的影子被月色拉得长长的。路雁有种预感,今天开始她的人生路似乎又到了一个拐弯儿口了。
瑟瑟夜风吹过耳边,薛峰听着李艳一路上唠叨着几十年前的往事,突然之间有了八卦的兴趣。
“见了你亲生父亲,你会不会抱头痛哭?”
路雁奇怪地盯了薛峰一眼,露出一个看白痴的表情。
“呵呵!雁姐不是那种矫揉造作的女人,雁姐威武,潇洒,哪儿是峰哥你想的那种矫揉造作的女人。”
光头强这话说的是真心的。像路雁这种女汉子类的女神,也是他非常欣赏的。只是,他自认不及薛峰的三分之一的能耐,因此,很多时候,仅仅是欣赏路雁的帅气和不拖泥带水,敬佩路雁的豪爽,当然也觊觎过路雁的美色。只是让他造次,他是一点儿也不敢的。
“你们一个一个脑子进水了吗?”路雁真是被这两个男人脑洞大开给打败了。
先不说她那几十年没见的爹是何方神圣,见了面还不知道是不是人亲生的,即使是亲生的,让她路雁就做小鸟状,抱着她亲爹抱头痛哭,她倒不如跟她爹来个一醉方休,来的过瘾。
路雁往天上暗自翻了个白眼,不知不觉间,一行四人就到了半山腰间的几栋小屋跟前。
夜色西沉,几间小房子高高矮矮凑建在一起。虽然一间间看上去都不算大,但是,听山下的花农说,这些房子都是近两年才建造成的。
四人不禁暗自疑惑。
房体的墙壁看不出很新,四周长满了护壁的古藤蔓条。廊下高高矮矮,摆列着一盆盆的绿植,在夜色之下,能感觉到郁郁生机。
透过门前正房的一排朝南的花格木质窗,可以看见屋内有个男人的身影,正坐在一张摇椅上,“咿咿呀呀”地听着一首古老的戏曲。
门前的树影婆娑,门内的长衫男人低吟,似乎走错了时代,走错了场景。
这哪里是一个小镇的花农,这里明明是世外的桃园。
轻轻推开门,薛峰轻拉着路雁掀起了门前的一副门帘。
“你好,请问是宋先生吗?”
屋内的人似乎有一刹那的恍惚,但是手里的摇扇没停,摇椅上的男人也没回头,戏曲依旧唱得更欢。
“打扰了,宋先生……”薛峰又拉着路雁上前几步。
摇椅上的男人慢慢坐直了身子,僵硬的身体似乎因为长期没动弹,此刻动起来显得机械,又不自然。
颤巍巍地放下手中的紫砂茶壶,那男人缓缓起身,素雅无尘的白色中式长衫,让他的背影看上去十分的干净。然而,就在他站起身转过来的那一刹那,在此之前对着男人所有的憧憬都化为了惊奇。
中年人的身姿,却有着沧桑落寞的沉重面容。男人的眉目与路雁有些相似,但是满脸的沧桑和悲凉。那咿咿呀呀的老曲子,仿佛诉说的就是他本身的沉重故事。
尽管男人一身的出尘,但也只是说的他一身衣着不凡。灰黑长裤垂坠笔直,白色衬衣贴服,在几人进来之前,想必他已经静坐多时。但此刻站起身,一身衣裤依旧整齐得不可思议,没有一丝褶皱。
“呃,你们?”仿佛老裁缝手中古老的铁剪。这位分明不老的沧桑男人皱起了眉头,喉咙间的声音破败得就像多少年转不动的风车。
“您是宋子右吗?”路雁忍住心中的压抑与悲伤,上前两步,紧盯住他的双眸。
“你是……”男人的声音略显清晰。
“方春青是我妈妈。”路雁清澈的双眼,干净而又坦然地看着他。
“方,方,方春青?春儿?”男人的表情终于有了更多的变化。
那一身的老态龙钟,终于掀起了片片波澜。
惊乱的神色,在看向路雁年轻又活力的脸庞后,闪过一丝尴尬,怀疑,审视的目光更是在路雁身上来回地游走多时,最终惊奇席卷了他的神色,狂喜密布脸庞。
“你是春儿的那个孩子?春儿怀着的那个孩子吗?我的孩子吗?啊?”似乎是很久没有说这么多的话,男人说的十分含糊不清,却硬是憋着一口气,将所有问题倾泻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