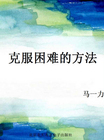岳依依吓了一跳,“怎么了,舅舅?”
“回到那三封信的照片,放大一点!”林云泰说,把身下的椅子向电脑的方向挪动了一下,“再打开白丝方巾的照片!”
岳依依照做,打开三封短信的照片其中一张,在旁边打开写有“舍利盗雍者,正也”的照片。
“克勤,你来看看!”林云泰侧了一下身体,给滕克勤让出空间。
林云泰用笔在屏幕上指出第一封信中“其时久也”一句中的“也”字,第三封信中“今世之逐利者”一句中的“利”和“者”字,以及信件末尾日期中的“雍正”二字,让滕克勤仔细比对。
滕克勤调整了一下屏幕角度,两只眼睛不停地左右转动,细心对比着林云泰指出的几个字。
“没错!应该出自于同一个人之手!”滕克勤肯定地说。
“这么说,在石函中留下雍正著作和白丝方巾的正是这个杜徽了!”林云泰说道,因为杜徽的三封短信中没有提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以致于他们忽略了这三张照片,更没想到要对比一下杜徽的字迹。
“杜徽留书旨在嫁祸,甄灵均断指挂印意在赎罪,两人的做法大相径庭,彼此矛盾,看来两人的所作所为虽然同时发生,但彼此毫不知情。我们之前推断过甄灵均可能被人强迫去盗挖舍利,如果这一点成立,甄灵均很有可能是被杜徽强迫的,所以这两人才会同床异梦。”岳依依分析道。
陈耳东低头沉思,岳依依说的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如果再深入地思考一下,甄灵均也有可能是被那个巡抚强迫的,杜徽留书嫁祸雍正要么是这个巡抚的授意,要么是出于自己本意。
如果杜徽留书嫁祸是那个巡抚的授意,两人又是坚定的同谋,那么他跟甄灵均之间则是志不同道不合,两者所作所为存在龃龉还是能说得通的。但最后杜徽失踪又怎么解释呢,难道是被巡抚杀人灭口了?
如果是出于本意,杜徽的心理肯定是对这种行为比较痛恨才会留书嫁祸,很有可能他根本也是被巡抚所强迫。反观甄灵均,他断指挂印是在赎罪,内心一定是很抗拒盗挖舍利这件事的。这样说来,杜徽和甄灵均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同的立场,既然两人在榆社期间朝夕相对,不应该不了解彼此心中所想,如果彼此意识到对方跟自己是同道之人,还彼此独立留书嫁祸、断指赎罪就有点说不通了。
再者,如果杜徽出于本意留书,为何不直接说出实情,指明盗挖舍利的人就是巡抚呢?为何在石函中留下雍正的著作和留下写有“盗舍利者雍正也”的白丝方巾呢?难道....这根本不是嫁祸,而是说出的真正实情?也就是说像岳依依猜测的那样,盗挖舍利其实真正的幕后之人是雍正?
想到这里,陈耳东心中一惊,连忙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众人听。
“我觉得雍正是主谋的可能性很大。”岳依依说,“雍正指使巡抚盗挖舍利,巡抚把任务交给杜徽,还用强迫的手段找来了甄灵均,其实这两人都不愿意,但因为他们城府都太深了,彼此都没有向对方坦明心迹,导致最后两人的所作所为产生矛盾。”
“抛开动机不谈,确实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滕克勤的刑警身份让他的思维一直都很理性。
陈耳东点点头,不得不承认岳依依说的是有道理的,杜徽和甄灵均立场相同,不代表他们会向对方表露出来。根据张汉英的描述,甄灵均相貌奇特、沉默寡言,杜徽才识高朗,定是城府极深之辈,两人即使朝夕相对,但彼此隐藏心迹,也是有可能的。陈耳东想到此,摇了摇头,规则和道理好懂,但是对人性自己还是搞不懂。
其他人纷纷提出自己的疑问,大家争论了半天也没有结论。这是很显然的,因为每一个结论都缺乏更多的线索去佐证,所以最终只能沦为猜想。
众人在困惑与不甘心中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众人到楼下吃早餐,在餐厅再次聚首。
陈耳东昨夜已计划好今天上午和滕克勤单独调查一下榆岭寺的那个老妪,于是跟众人说上午想和滕克勤去一趟YS县民政局。之所以和滕克勤去,是因为他的刑警身份有助于开展工作。
“还以为你们两个要去领证呢!”石坚强口无遮拦地开玩笑,被滕克勤一巴掌打在后脑勺上。
林云泰今天的主要工作是查阅史料,查明张汉英提到的那个巡抚的身份,他正打算早餐后用岳依依的电脑登陆文物局的网上图书馆,查阅清史档案。听到陈耳东的话,知道他有自己的想法,表示赞同,毕竟分头行事也能提高工作效率。
“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石坚强问。
“不用,你和依依留下来协助林叔。”陈耳东摆摆手说。
滕克勤提醒大家务必小心,防止黑衣人白天偷袭。
陈耳东坐上滕克勤驾驶的越野车,让他开向西大街9号的民政局。
滕克勤没有多问,打开导航向西大街驶去。
滕克勤知道民政局负责的工作种类庞杂,工作窗口和服务部门很多,找对口的部门要花费不少时间,于是化繁为简,直接走向咨询台。
“你好,我们想查阅一下YS县百岁以上老人的资料。”滕克勤亮出自己的警官证,没有说明他是外省来的。
对方一个戴眼镜的女孩看了看身材高大,正气凛然的滕克勤,没有多问,带两人去民政局老年办,房间里一个老太太正在看报纸,看到有人来访,爱答不理地问所为何事。
滕克勤再次亮了一下警官证,说明来意。对方同样没有多问,毕竟来人要找的资料也不是什么机密文件。老太太站起身来,从文件柜里拿出一叠资料。
陈耳东接过资料,坐在老太太对面翻看起来。这是YS县目前健在的百岁以上老人的档案,档案袋上的统计数字经过不断涂抹和更改,最新的数字显示是42。
陈耳东仔细翻阅了两遍,却并未发现石斑琼这个名字。
“阿姨,榆社全县的百岁老人都在这里了吗?”陈耳东问对面的老太太。
“活着的都在这了。”老太太放下报纸,从老花镜的镜框上方看了看陈耳东,“已经不在人世的,材料在另一个柜子里,不多文件有些多,我给你拿去。”
滕克勤刚想说不用,但老太太已经颤巍巍地再次站起身来,便没阻止。
“这是前两天刚整理的材料。”老太太把另一叠材料放在陈耳东面前,“你们找的人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滕克勤道了声谢,接过老太太递来的资料,没有回答她的问题,随意地翻阅起来,因为他确定自己要找的资料肯定不在这里。
没想到刚翻到第一页,滕克勤就倒吸一口凉气。第一页的档案上,赫然写着石斑琼的名字!
看到滕克勤惊讶的表情,陈耳东站起来接过他手里的文件,看到石斑琼的名字,陈耳东也是一惊,想不到那个阿婆已经去世了。
两人看向眼前的档案,姓名一栏写的是石斑琼,出生日期写的是1898年7月15日,今年117岁!真是高寿,两人感叹道。档案仅有一页,没有照片,联系方式和生平事迹栏均是空白,但是地址一栏却清楚地写着“榆岭寺村四组十二号”,两人确定人没有弄错。
两人仔细看了看档案,只见纸张的眉头处有一行手写的字迹:2015年6月18日,估计这就是老妪的死亡日期了。毕竟一百多岁的人了,说没就没了。
“阿姨,您对这个人的情况有印象吗?”陈耳东问那位老年办的老太太。
老太太看了一眼档案,说道:“这人是前天死的,我们按照公安局的通报材料刚调整的档案。”
“百岁以上老人自然死亡不是应该有各乡镇民政部门和街道办统计,统一上报给你们民政局吗?怎么公安局给你们通报?”滕克勤对这方面的政策非常熟悉。
“这个老阿婆不是自然死亡,是被人杀死的。”民政局的老太太淡定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