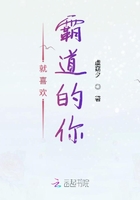故乡,岂是一山一水?是晨起的鸡鸣狗吠,是日暮的袅袅炊烟,是母亲的锅碗瓢盆,是父亲的沉默关怀。它是内心深处最温柔的部分,软软地,暖暖地,怀念、甜蜜、疼痛和依恋。
经常会感念韩东的几句诗:
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每当厌倦的情绪来临\就会有一阵风为我解脱
我家临街,北门外是一口井,井水很浅,下雨的时候,用瓢舀就能喝到水。
晚上村子里放电影的时候,小孩子们就在井边用石子圈出地方,抢占有利地形。井水很浅,不需要盖盖子。吃过晚饭,抽着旱烟迟来的人,只好站在后面,或是爬上土墙、矮房,抢不到近处,只有抢占高处,屏幕正面背面全是观看的人。
春天村里的的槐树挂满了槐花,一串串槐花洁白耀眼,弥漫着沁人的浓香。孩子们找来竹竿,在上面绑上有弯钩的铁丝,站在路边、走在街上、爬上房顶去钩采一串串槐花,采摘下的槐花,被捋下来,放在小簸箕里,大人们用槐花做馅儿,蒸包子,烙饸子,闷窝头。小孩们把剩余的槐花兜在怀里,用手指抽出里面嫩黄的花蕊,放在舌尖上,细细地咀嚼,直到唇齿间流溢出细细的甜香。
农历三月二十五螃蟹节,大街小巷摆满了螃蟹。孩子们上午只上两节课,学校给孩子们留足闲逛的时间。平时手头拮据的父母亲这时则大方地给孩子两三毛钱,孩子们会在最热闹嘈杂的街头买一只自己最心仪的螃蟹带回家,吃完螃蟹,将螃蟹腿卸下,装在铅笔盒里,留作到学校炫耀的资本。
这一天我家的灶台前会爬满父亲从集市上背回来的青绿色的螃蟹,忙碌的母亲把螃蟹逮进大盆,洗完后一块儿倒进铁锅煮沸,我们站在锅沿儿边,等待螃蟹逐渐变红,不等坐在桌前,用筷子捞起一个,蹲在门槛上享受螃蟹大宴。
吃剩的红红的小虾小蟹都被放进竹笼里,吊挂在屋内房顶的铁钩上,让孩子们可望而不可即,留做下顿的美味。
夏天的晚上到邻居家看电视,土炕上坐满了人。等到电视剧演完,大人们都关好大门睡觉了。我拐过街角,绕到街前的两棵大槐树下,顺着树干翻墙而进。
悄悄地插上屋门,钻进蚊帐。看着墙上晃动的斑驳的柿子树的影子,在心里余味未尽地哼唱刚刚看完的电视剧的主题歌,伴着蛐蛐的小夜曲入眠。
八月十五中秋节,白发的奶奶,迈着颤悠悠的细步,用微颤的手指,夹住一个像柿子一样大的月饼送给孙子孙女。我们舍不得吃,把月饼埋在装满了粮食的柜子表层,留到晚上和家人一起分享。
走出村子,走过一条长长的白杨树林,再经过一片豆田和一片玉米地,经过两条沟壑,穿行在夕阳西下的旷野中,就在我因为天空飞鸟的尖叫而恐惧地呼叫“爸爸”的时候,就到了小河对岸我家的花生地。父亲在花生地里搭了个窝棚,窝棚前有爸爸烤花生和老玉米的小地炉子。
晚上我和爸爸住在窝棚里看守一地晾晒的花生,身下的高粱秸秆上偶尔有小虫爬出来,不过并不咬人。凌晨四五点的时候,就会传来各种鸟儿的叫声,河边的杨树杈上住着一窝小鸟,它们的家在暗蓝的夜幕下显得格外高远。
微雨的清晨,是捡拾花生的好时候。白亮的花生会在细雨的冲洗下暴露在绵软的沙滩上,我和长辫子的姐姐在晨光微露的旷野上抢拾花生,姐姐捡得快,在我快要急哭了的时候,爸爸则会用他宽大的手掌,迅速地扒开地垄边的桑枝,那里遗漏的花生多,爸爸手快,不一会儿,我的筐子就满满的,甚至满到长出一个圆锥形的尖儿来,我则留给爸爸一脸的憨笑。
帮爸爸把晒好的花生装到牛车上,我躺在最上面,看着天上行走的白云,看着树尖儿悠悠地被抛在后面,随着牛车的颠簸,尽情地舒展四肢,像躺在一个甜蜜的梦里。
“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为一百多老兵送骨灰的台湾老人高秉涵含泪说。
乡愁,是游子解不开的扣、绕不过的山、走不到头儿的路,是割不断的回忆,是扯不断的亲情,是撇不下的牵挂。
故乡,岂是一山一水?
是晨起的鸡鸣狗吠,是日暮的袅袅炊烟,是母亲的锅碗瓢盆,是父亲的沉默关怀。
它是内心深处最温柔的部分,软软地,暖暖地,怀念、甜蜜、疼痛和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