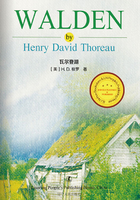听到噩耗传来的时候,我正在去成都出差的路上,十万火急的声音,让我心惊肉跳。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几日前还与我有说有笑的两位同事,怎么瞬间就离我而去?他们在出差的路上究竟发生了怎样严重的紧急情况,要导致他们连一丝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任我做多少无端的猜测,终是无法改变他们已然离世的事实。
冷雨冰凌,湿滑泥泞的路上,时有险象发生,心情无处可落的沉重,像一把生锈的重锁横横地躺在心窝上,让人无法喘息。直到车安全地驶入市郊的收费站时,我才长长地舒了口气。还没到家就接到单位电话,去殡仪馆迎接同事的遗体归来。马不停蹄地赶去西郊的殡仪馆,他们是我朝夕相处的兄弟呀,我怕我去晚了,这最后一面就见不到了。
撕心的哭声,几度昏厥的母亲,让无数眼泪直奔而下。搀扶、劝慰、安抚,在这样的时刻显得那么多余,我不知道能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两位失去儿子的母亲,一个八十高龄,一个年近七旬,她们的白发在寒风中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站立。叩问苍天,跪拜黄土,还她们的心肝宝贝呀!
一个36岁,一个48岁,正值人生的好年华,他们却走得那样匆忙。给所有相识相知的人留下永远的遗憾和永久的思念。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这一切担当,让两个家庭从此不再完整。多少眼泪,多少悲伤,要多少日子才可以忘记呀。
走进那幢楼里,那是我们共同办公的地方,电梯门口向右转就是他们的办公室。桌子上还摆放着他们两个人的岗位牌,一个叫鲍吉永,一个叫屠岸卿,他们还用那样真诚坦率的眼神看着我,仿佛他们从来不曾离开过。
我还记得我每次去他们部门的时候,整个屋子堆满了资料盒,他们埋头在那些材料与数据里苦干。见我到来,总是客气地要请我喝杯茶。鲍老师长相稍显严肃,在不熟悉的时候,许多人不大敢与他说话。事实上,他是幽默随和,豁达善良的人。他冷不丁的说出一句话,让人捧腹半天,他还一脸严肃的样子。小屠年轻些,我看他像是自己的小兄弟那样,他一直在乡镇基层所里工作,调来市局的时间不长。他寡言少语,勤奋好学,每次遇见打招呼时还有些略微的羞涩,是人们心中的那种好孩子的形象。小屠的母亲拉着我的手,眼泪汪汪,悲伤难抑地跟我说起他的孝心,说起他刚满十个月的孩子,点点滴滴让人心碎难过。
还是昨天叫着娘亲回来的孩子,转眼就成了隔世的人,多么想这只是一场梦,一场让人疼痛的梦,当梦挣扎着醒来的时候,他们还是母亲手心里鲜活的孩子。他们还有许多未竟事,上至高堂父母,下至年幼孩子,又有哪一处不是需要他们那双勤劳的双手和赤诚的心灵呀。人间最悲伤的事莫过于白发人送了黑发人。残缺的家,要经过多少时光的安抚,才可以渐渐平复。而这失去亲人疼痛,却永远直立在亲人的心中,无论何时想起,都是切肤的疼痛。
与他们同部门的两位女同事,眼泪断线似的流下来,她们说这早已超越了亲兄妹的情谊又如何丢得了呀,泣不成声的回忆里,处处是他们在田野里奔跑的姿态,那样鲜活,那样亲近。每次出差的时候,同在一个部门,连水杯都从来不计较,不嫌弃,亲如家人一样。这千年修来的缘分,让我们成了同事,成了朋友,成了亲人,这手足般的深情呀,为何要这样短暂?为何要这样匆忙?
灵堂里,年轻的脸上,还看不到多少岁月的痕迹,他们刚毅的脸却被时光定格了。菊花肃穆,人人伤怀,各个哽咽。我们与他们只隔着一尺的距离,却隔着一世的光阴。他们安静地躺在冰冷的世界里,与亲人、朋友、同事作最后的告别。无声,无语,大悲,大哀!他们可否知道身后那张更加冷冰的铁床就是人生的最后归宿。一场火,一把灰,一抷土,留给默默的青山。从此,想见仪容空有影子,欲闻笑声杳无音!
白茫茫的天地,白茫茫的哀乐,迎面地扑来,打在脸上,疼在心上。一个仪式,终只是一种告别的方式,而留在心里的伤疤总会不定时复发。也许只有珍惜当下,珍惜所拥有,才不愧于一次送别带来的悟道。
安息吧,我可亲可敬的两个好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