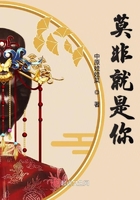一个月以后,景仁死了。
景仁死的时候,瘦的皮包骨头。邻里们前来吊唁,见着了,全摇头叹息。冯媚也是假惺惺地哭,边哭边诉:什么不要活了,你走了我怎么办呀?什么药片片吃了一箩筐,咋就不见效呀?邻里们交换一个眼神,劝慰还是要前劝慰,要她节哀,要她想开点。
景仁父母早亡,景家在镇上属外来户,没有同宗的族人,加之兄弟俩常年在外,也没有交下太多的人情,他的死亡没有引来多少人的关心。虽然镇子上疯传冯媚同汪镇长不清不白,但景仁一直有病是实事;男人有病,女人在外面找个相好司空见惯,谁也没有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现在的人情本来就薄如纸,何况人死如灯灭,谁愿意多事呢。
劳芊芊自景仁一死,就赶过来帮忙。她是冯媚的好朋友。卖棺材,选坟地,尸首入殓,设灵堂祭奠,等等,全是她在忙活张罗。停灵三天后,景仁就被草草下葬了。
两天后,景义回来啦。一进门,他就抱着哥哥的灵牌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哭罢,他质问冯媚:
“为啥不等着我?”
“你哥年轻,又无子嗣,按乡俗,只能停灵三日。”冯媚说道。
“那为啥不早点给我打电话?”景义再问。
景义接到报丧讯息,是在哥哥死后的第二天。
“你哥一直病,一直病,谁知道,那天夜里,突然就没啦。我一个女人家,只知道哭,哭都哭昏了。第二天有人提醒,才想起来给你打电话。怨我么?”冯媚挤出一串眼泪,说道。
景义无言以对。
出了哥哥的家门,景义脑子里疑云重重。自己走得时候,哥哥的病情明显好转,短短几个月,怎么突然就死了呢?嫂嫂是个不安分的人,是她照顾不周,导致哥哥病情加重?还是出了其它状况,哥哥是死于非命?哥哥死前怎么不给自己打个电话呢?这里面有蹊跷。
景义悄悄在镇子里走访街坊四邻,有人回答:不知情;有人回答:死时在身边帮忙,见过最后一面,人瘦的不像样,是病死的。
景义的行踪被人告知冯媚,她很是心慌,赶忙去见芊芊。
“慌什么慌?他明明就是病死的,让他查去,你甭理会。”芊芊呵斥道。
“万一,万一他查出个什么,我们怎么办?他可是特战兵,能耐大着呢。。”冯媚不放心地说道。
“这件事我们做得天衣无缝,他能查出啥?除非你告诉他内情,任是神仙也找不出来真相。你肯告诉他吗?别怕,再说,还有汪镇长呢。”芊芊给冯媚宽心打气,说道。
冯媚镇定下来,走了。
果然,景义一连寻访了两天,毫无结果。他心中苦闷,晚间一个人蔫头蔫脑,奔了哥哥的坟地。对着哥哥的坟头,他双膝跪地,又是一场痛哭。
“哥,你死的好苦呀!死的时候,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做弟弟的连一天也没有伺候过你,你让我心里咋过得去?你为啥不早点给我打电话?嫂嫂也为啥不给我打电话?是你不让打吗?我想不明白,也问不明白,你要是有冤屈,现在就显显灵,告诉我。”景义连哭带诉,哭得让人断肠,诉得让人动容。
不知何时,一个黑影悄悄站在他的身后。
“逝者已逝,你就是哭塌他的坟头,他也无法开口说话。还是问问活着的人吧,人可是有嘴的。”黑影开口说道。
“你是谁?”景义霍然起身,问道。
“沈喜权,本镇的副镇长。”黑影答道。
“你刚才话里有话,能明说吗?”景义目光逼视着沈喜权,沉声问道。
沈喜权没有见过景义。景义壮实的身材,浑身隐隐散发的煞气,令他不由得后退了一步。这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他心里想道。
“咱们素昧平生,我说的话,你能相信吗?”沈喜权并不慌张,反问道。
“我会分析,会求证。”景义回答道。
“你果然训练有素。好,我说。我并不知道你哥哥是怎么死的,只是听人说,你嫂嫂不是个守妇道的女人,早就和镇长汪为国勾搭成奸。这件事情,陌南镇上传得很广。一个月前,你哥哥去食为天饭庄捉奸,听说受了伤;至于怎么受得伤,我无从得悉。自从那一天后,你哥哥便再没有出过门,也没有上过班。你嫂嫂倒是毫不收敛,汪为国也是越发放肆,天天往你家跑。镇上的人都看不下去,但没有谁敢说闲话。后来,你哥哥就死了。”
沈喜权说得很详细,但叙说开始前,不是加上“听人说”,就是加上“听说”,没有给出任何肯定的答案。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景义逼问一句。
“我说是打抱不平,仗义执言,你肯定不信。刚才介绍过,我是副镇长,副镇长同正镇长之间关系往往很微妙,明白这话的意思吧?前面我说的,你不信,就权当耳旁风好啦;要信,千万不要出卖我。”沈喜权老奸巨猾,干脆把话说得十分直白。
“谢谢你。”景义说道。
嫂嫂冯媚的为底细,景义心里清楚,沈喜权的话,他心里已经相信了七八分。
“年轻人,我知道你本领高强,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就是不能莽撞。现在什么都讲真凭实据,你到何处寻找真凭实据呢?即使是找着了,无非是男女间的事情,你又能怎样?我估摸,他们用的是软刀子杀人,不会留把柄的。还是忍了吧。”沈喜权用了一招激将法,假惺惺地说道。
“我不会忍!我哥哥不能死得不明不白,一但查明真相,不管软刀子硬刀子,他们都得付出代价。”景义坚决地说道,并且恨恨地一拳打向身旁碗口粗的杨树,杨树应声而折。
沈喜权见到景义如此刚猛的一拳,心头一震。不过,他马上转为暗喜。看来,汪为国这回有麻烦了,还是大麻烦。他假惺惺地劝了几句,要景义别冲动,然后就告辞了。
景义站在哥哥的坟前,思索了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