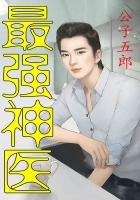云出按照南司月指导的方向,终于找到了那家君悦古董店,单看门楣,就知道是一个有钱的主。
普通商家,哪里会有这么大排场?足足三个门面大!
这招牌更是鎏金溢彩,飞扬跋扈的题词,在云出眼中,就是这么几个字,“我很有钱,来打劫我吧!”
所谓店大欺主,她又没有任何凭据,待会,不会被如狼似虎的小二给打出来吧?
她现在可是多愁多病身,再也经不起几次摔了。
心里揣着不安,云出吸了好几次气,才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刚进门,便装模作样地往厅旁的太师椅上一坐,脚则翘在旁边的八仙桌上。
“叫你们老板来见我!”
云出这样嚣张的作态,让店小二一时半刻也拿不准主意。
而且,她身上这件用白狐腋下绒毛制成的衣服,也实在让人生不起轻忽的意思来。
——单单这件衣服,就能买下他们半个铺子了。
而且,还有价无市!
小二到底是见多识广之人,愣了一会神,便好脾气地端来一杯热茶,毕恭毕敬地递给云出。
云出也沉得住气,拿捏着架子,将热茶接了过来,装模做样地尝了一口,而后摇头晃脑道,“是极品毛尖啊,不错,不错!”
小二顿时傻眼了。
难道我刚才泡的不是普洱?
云出当然知道是普洱,她走南闯北这么久,就算对茶这种高端消费品没什么兴趣,却也了解一些,只是看见小二那副谄媚的样子,就想寒碜寒碜他。
纯粹体内恶劣因子作怪。
丫仇富。
正在两人大眼瞪小眼,场面有那么点尴尬的时候,古董店的老板掀开帘子,拿着个鼻烟壶,慢条斯理地走了出来。
云出本来编造了一大通话,来杜撰自己是南王府的一个管事。哪知,她刚刚站起来,什么话都没说,那个大腹便便的老板便神色一肃,撩起下摆,拱着手,毕恭毕敬地朝她拜了拜。
“姑娘好。”
云出眨了眨眼,点头,客气地笑了两声。
“姑娘有什么吩咐?”老板又拜了拜,继续严肃地,认真地请教她,一点开玩笑的意思都没有。
“……拿钱。”云出很汗地回答。
在旁边伺候的小二,也是一脸的汗。
老板手里拿的可是鼻烟壶,鼻烟壶是帮人醒脑的,可不是酒。
难道,那里面的鼻烟,竟被歹人换成了迷烟?!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账房,把里面的银票全部拿出来!”小二正在胡思乱想呢,老板眼睛一蹬,朝他吼了一句。
小二吓了一跳,赶紧猫着身,掀开帘子,钻进了后堂。
云出也看得目瞪口呆,手里的茶都忘记放下了。
“哎呀,怎么能给姑娘喝这么劣质的茶!刘小五,赶紧把前年淘来的贡品给姑娘泡上来!”老板后知后觉地凑过去,鼻子在茶杯前就是这么一闻,随即,又冲着后堂大喊了一句。
这阵狮子吼,差点把云出的腿从桌子上吓得掉下来。
不过,那腿刚落到中途,便被老板眼疾手快地接住,随即,又毕恭毕敬地帮她摆回到桌子上。
好像,她这样翘着腿搁在自个儿的台面上,还是给了他面子似的。
“多……多谢。”云出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来,心里不停地琢磨:到底是哪里被南司月做上记号了?还是那么神奇的记号?
简直点石成金啊!
说话间,刚才被差遣进去拿钱的小二已经捧着一盘子厚厚的银票,走了出来。
云出的眼睛立刻刷得一下冒出了星星。
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银票啊……好吧,就算以前见过,那些也不是给她的啊!
而现在——
“姑娘请笑纳。”老板眉头也不皱,用布包将银票一包,端端正正地滴了过去。
小二站在一边,脸上因为肉痛,而不停地抽搐着。
老实说,云出想接过来,非常非常想接过来,她的手已经不由自主伸了出去,好在,她还有一丝理智,所以,也同样一脸肉痛地,从那个包里,抽出一张面值一百两的银票,咬着牙,勉强地笑道,“一张就够了,不用那么多。”
“姑娘千万别客气。”老板殷勤地劝说着。
如果不是眼前的景象实在太真实了,云出会认为这是一个梦境。
这就是她十几年的日日夜夜朝思暮想的美梦啊。
竟然有人拿着一大叠银票硬要塞给她!
“……还是,不要了。一百两,够了够了。”她忍住自己几乎要接下来的动作,捏紧那张一百两银票,然后,从桌上跳下来,一哧溜地跑到门口,而后,回身,朝老板抱了抱拳,“多谢老板,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再见。”
老板几乎还想追出去,哪知云出溜得实在太快,眨眼就没了踪影。
直到云出再也见不到影了,小二才回过神,转头,看怪物一样看着自个儿正在擦汗的老板。
“老板,为什么要对这对姑娘这么好?依小人看,这位姑娘也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出来的姑娘,有一股子江湖气。”
“你懂什么!”老板将肉呼呼的眼睛猛地一翻,煞是吓人地又瞪了小二一眼,“回去烧香拜佛吧!还好这位姑娘的胃口不大,若是她真的说出一个我们承受不起的数字来,我们砸锅卖铁,烧杀掳掠,也得给她凑齐罗!”
“为……为什么啊?”小二被吓得往后疾行几步,颤抖着问。
“难道,你没看到她右耳上的绿宝石耳环吗?”老板用一种很奇异的语调,低低地说,“南王府中人,凡见戴此耳环的女子,就必须不问代价地满足她的任何要求。”
这一下,小二也目瞪口呆了。
他们后面的谈话,云出没有听见。
她拿了银票后,本着以前的职业习惯,顿觉此处不可久留,能闪多快,就闪多快。
何况,这个冤大头的神志明显就是不清楚嘛。
害得她也一头雾水。
不过,那一百两银票却是货真价实的。
云出先找了一个票号,将银票换成了实实在在的银子,然后兜着一包银子,晃晃悠悠地朝酒楼走了回去。
酒楼下面有一个卖糖葫芦的,云出已经进了门,走了两步,又折了回来,买了两根鲜红欲滴的糖葫芦,雀跃着上了楼。
等爬到了楼梯口,云出抬起头,堪堪看到正倚窗而坐的南司月。
他果然在等着她。
等待,很多时候是看不见的,可有时候,又是能看见的。
从姿态,从神色,从他安然垂下的眼睫和手边渐冷的茶水。
紫色的,绣着云纹的大麾迤逦地垂在地上,黑色的长发用金冠整整齐齐地束在脑后,鼻骨清晰笔直,从侧面看,轮廓被暗暗的光线模糊,不甚清晰,多了一份婉约的祥和。
一个六岁后就一直生活在黑暗中,却比任何人都骄傲的南王殿下。
云出的唇角不由自主地弯了上去,故意将脚步声放得很重,“我回来了!”她大声吆喝。
南司月没什么反应,可是笑意从唇角,传到了眉梢。
然后,她大喇喇地坐回他的对面,然后,对着等了很久、脸上却没有一点不耐烦地南司月,笑眯了眼,将刚才发生的事情,眉飞色舞地描述了一遍。
“你说,他的脑子是不是被门板夹过了?”最后的最后,云出好笑地问。
“恰恰是因为他没有。”南司月古怪地回答道。
云出眨巴着眼瞧他,“什么意思啊?”
南司月没有再回答,他将脸转向窗外,感受那缕透过窗户、缓缓袭来的清风,正想继续端起那杯已经凉掉的茶,冷不丁的,对面的云出忽而站了起来,拿着一个长长的东西向他捅了过来。
长长的形状,是根据气流的变化,和十几年的经验猜出来的。
可具体是什么东西,他不可能猜到。
空气里有股奇怪的、甜丝丝的味道,瞬间及近。
他下意识地想往后避开,可一念起倾身过来的人是云出,南司月的身体稍微滞了滞。
下一刻,一个甜甜的小山楂,便撞上他的嘴唇。
“喏,糖葫芦,尝一个吧。”某人半边身子都悬在桌子上,一手拿着一根糖葫芦,笑眯眯地催促道。
南司月进退维谷,张嘴不是,不张嘴也不是。
云出则很有耐心地,保持微笑,相当执着地看着他。
——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架势。
可是,这种情况并持续多久,南司月也根本没有妥协的意思,他突然站了起来,刚才还柔和宁静的脸,忽而变得清冷而疏离。
“太晚了,我们回去吧。”他说。
云出怔了怔,看着他迅速转身,缓步向楼梯那边走了去,撇撇嘴,也不生气,将两根糖葫芦往左手一塞,然后放下银子,小跑着跟了过去。
……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南司月的样子,怎么那么像落荒而逃的模样呢?
糖葫芦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可怕了?
想不通啊想不通。
南司月似乎走得不快,可等云出追上他的时候,还是累了个气喘吁吁,她本来就没恢复完全,刚才又跑上跑下了半天,这时扶着腰,免不了咳嗽了几声。
听到她的咳嗽声,南司月终于停下了脚步。
两个人就这样陡然站在大街中央,周围人群熙来攘往,从他们身边擦过。
“既然咱们……咱们不吃了,那就,那就回……回去吧。”云出伸出手,为双方解围道,“反正已经出来这么久了,只怕阿堵他们还以为是我拐走了你。”
南司月这次却没有再握她的手,径直越过她,淡淡道,“好,回吧。”
不过,这一次,他的脚步放得很慢,也方便云出从容地跟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