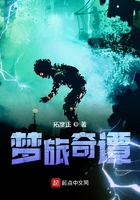唐三抱着云出,用肩膀大力地撞开一家医馆的门,他还未站稳,便揪起其中一个伙计的领口,急声道,“叫大夫出来,快点!”
他的话音未落,一个颤巍巍的大夫已经走了出来,见到唐三怀中的云出,他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招呼唐三将病人抱进内堂。
伙计则在门口左右张望了一下,远远地见到巡逻卫队又来了,他赶紧合上门板。
到了内堂,唐三将云出小心翼翼的放在床上,手依旧按着她的背,将真气源源不断地输进去,减低她的痛楚。
大夫到底是有经验的人,他略略看了云出一会,正要发话,目光却瞥到了凌乱青丝间夹杂的绿宝石耳环。
大夫的脸色离开凝重了,他站起身,招呼着伙计过来,对他吩咐了一两句话,然后去药柜那里,取了将近十几味药,迅速地折回来,将药递给唐三,“赶紧把这些药煎了,不然,孩子就真的保不住了。”
“哦,好。”唐三满额的汗,闻言,一把抓住大夫的手,郑重道,“不管要有什么代价,都必须保住他们,两个都要保住!”
“知道,老夫全力以赴,你赶快去煎药吧。”大夫说着,摆摆手,让唐三出去。
唐三也不敢耽误,拿起药包,便冲到了后院生有炉子的地方,卖力地舀水煎药。
前堂,老大夫重新给云出把着脉,眉头也越簇越紧了。
等唐三好不容易将药给煎好,一面嘶嘶地吸着气,一面端进来,他跨进门槛,匍一抬头,便发现屋里已经多了许多人。
正坐在云出床沿边的,一脸疲倦,紫衣上还有浓浓的杀伐气息,正是刚刚从别院回来的南司月。
舞殇与阿堵则站在他身侧,亦是一脸疲倦。
刚刚经历了生死,还脱险没多久呢,便听到了这个消息,怎么会不累?
唐三站定,双手捧着热腾腾的汤药,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倒是南司月率先开口,他握着云出的手,略有点憔悴地抬起头,淡淡吩咐道,“药烫,舞殇,帮唐宫主端一下。”
舞殇闻言,上前将唐三手中的药给接了过来。
刚触到杯沿,舞殇不禁皱了皱眉:那药果然很烫,唐三刚才捧着的时候,却好像完全没有知觉一样。
她的目光忍不住扫向唐三的手,果然烫红了一片。
——大概,是太担心了,以至于连自己的痛感都忽略了。
“对不起。”唐三手中一空,他讪讪地垂下手臂,很真诚地说了三个字。
没有照顾好云出,是他的错。
在刚才,他察觉到云出有了身孕,而且,一度遭受流产的威胁时,唐三痛悔得恨不得将自己一头撞死算了。
她大大咧咧也就算了,他怎么能和她一起大大咧咧。
“不关你的事情。”南司月转头看了看云出惨白、昏沉的脸,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这才站起身,缓步走到唐三面前,“我该感谢你,把她安全地带回来。”
“哎,你不知道,她之所以变成这样,完全是因为我。”唐三懊恼地、将方才的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而后郁闷地骂了一句,“这个笨女人,什么时候能为自己多想想,也不至于变成这样。”
可骂归骂,心里还是疼得无以复加。
还是那句话——
恨不得把自己撞死算了。
南司月很安静地听着,只是,听到云出说与唐三‘共生死’的时候,他的眉心微微一剃,并不明显,转瞬即逝。
“那个……她不会有事吧?”言归正传,这才是他们此时最关心的问题,“还有……孩子,孩子不会出事吧?”
“云出没事。孩子……”南司月面色一痛,摇头道,“暂时不知道。”
这个消息,他等了很久很久,却未想,是在这种情况下得知的。
“对不起,我没照顾好她。”唐三又道了声歉,不知为何,在看到南司月的时候,唐三只觉心中五味杂陈,说不出什么感觉,但更多的,确实是歉意。
他怎么能够让云出在他身边出事呢?
“不,谢谢你,她本应该由我照顾的,我却太过大意。”南司月低声道,“我早应该发现的。”
上次在曲阜见面的时候,她就显得那么憔悴困倦,是他心中想起其它事情,是他太过大意,没能守好她。
照顾云出,本是他南司月的责任。
这个言外之意,唐三焉会听不出来?
两个男人,还是第一次这么敏感地站在一起,一时间,竟是默默。
舞殇也发觉了一些什么,端着药催道,“王爷,是不是先让王妃把药服了?”
南司月这才转身,唐三则在原地站了一会,然后很知趣地退了出去,“我在外面等吧。”
过不多会,舞殇与阿堵也退了出来。
房门在他们面前合上。
阿堵和舞殇都是一样的忧色,他们当然不希望在这个关头,小世子或者小郡主出什么事。反观唐三,他的脸色却沉沉寂寂,一直跳脱无忧的神情,终于收敛,漂亮细长的眼睛,黯而深邃。
是他错了吗?
这样无忧无虑地在她旁边,不给她任何压力,保持着一个朋友的距离,还是,错了吗?
明知道,只要在她身边的人,她都会一个不落地放在心上——原来自己始终是贪心的,哪怕是作为一个朋友,仍然希望,自己能在她的心上。
可同生,可共死。
他想努力地承担起她所有的喜怒哀乐,却未想到,这些承担,本应该尽数交给另一个人。
想到这里,唐三突然站起身,猛地推开门,面对正要吹汤药的南司月,沉声道,“即便……即便孩子真的保不住了,你也不要怪她,我以后会适当地保持距离。”
南司月抬头,惊奇地看了他一会,然后,心平气和道,“我当然不会怪她,更没有怪你,唐宫主,你想得太多了。说起来,我真的要谢谢你,谢你为我们劫走了那一车炸药,也谢谢你一直以来对她的爱护。”
唐三沉沉静静地站在门口,未置可否。
南司月则继续低下头,将汤勺里的药汁吹冷,声音依旧平和安静,“因为信她,所以我信你。”
唐三怔了怔,秀美的脸一片黯然,他低头苦笑,静静地退出房间,转身,大步朝门外走去。
阿堵莫名其妙地看着决然离开的唐三,正要请示南司月是追还是不追,舞殇却一把拉住了他。
“你老婆为了别的男人、把孩子给没了,你会不会生气?”舞殇瞪着阿堵,简直想用砖头敲醒阿堵的榆木疙瘩脑袋。
“可是,唐宫主和王妃都不是故意的……”阿堵挠头,怯怯地辩解道。
舞殇无语地望着他,“如果是故意的,你以为我们现在还能安稳地坐在这里?王爷早把这里夷成平地了!可正因为不是故意的,王爷才更憋屈,你知不知道第一个孩子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王爷现在是有情绪也无处发泄,他又不是圣人,还真的像菩萨一样无嗔无怒啊?”
阿堵似乎还有有点不懂。
舞殇则懒得继续和这个榆木疙瘩脑袋纠缠,她担忧地朝里面望了一眼,然后轻轻地合上房门。
内堂里,汤药的温度已经刚刚好,南司月轻轻地扶起云出,让她小心地靠在自己怀中,手指轻巧地将她额前的散发拢到了耳朵,“醒醒,先把药喝了,嗯?”
声音很柔很轻,好像稍微大一些,便会伤到她似的。
云出晕晕沉沉的,听到了他的声音,她下意识地往南司月怀里钻了钻,像只懒洋洋的小猫。
南司月莞尔,也不忍再叫她,想了想,索性自己先含了一口,再低下头,一点点将药水给她哺了进去。
药确实很苦。
他略有点心疼,可还是必须让她喝完。
手臂松松地搂着她的腰,在摸到云出依旧平坦的腹部时,南司月心中又是一痛。
能不能保住,暂时还没定数,大夫说,十有八九是保不住的。
如果孩子真的没了,说不心疼,绝对是假的。
天知道他多么期待他们的小孩降世的那一天,他们没有享受到的童年无忧,他都会全部给他。
——可事到如今,只要云出能康复,什么都可以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