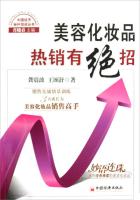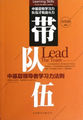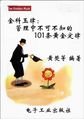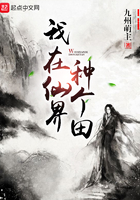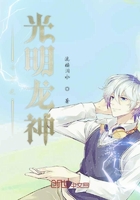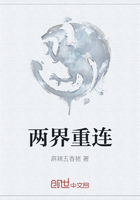此外,巴菲特认为,如果公司领导者在股市上大量回购本公司股票,是在表示他们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准则,而不是盲目追求扩大公司规模和业务。这种姿态会向市场发送出良好的信号,从而吸引一批正在股市中寻找管理优秀且可以增加股东财富的公司的投资者。一般来说,股东会有两次获利机会,一次是在初次买入股票时,第二次是由于投资者们对公司产生兴趣,从而对股价的上涨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管理层是否诚实
巴菲特一直敬重那些在股东年会上,全面且详实报告公司营运状况的管理人员,尤其尊敬那些不以大众可接受的财务准则为借口搞会计花招,而是能够充分、真实地披露公司经营状况的管理者。因为坦诚是巴菲特对企业管理层人员的必须要求,也只有这样的管理者才能把成功分享给他人,并勇于承认错误,永远向股东保持坦诚的态度。
财务会计标准只要求以产业类别分类的方式,公布商业讯息。有一些管理者利用这些最低标准,把公司所有的商务讯息归类为同一个产业类别,使股东难以理解或得知每一个业务部门的实际经营状况。巴菲特对此嗤之以鼻,他坚持认为,无论是否属于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资料,还是超出一般公认会计原则要求的资料,只要它能够帮助具有财务方面知识的读者回答下列三个重要问题,就应该公布。
(1)公司的大概价值是多少?
(2)它未来的发展潜力有多大?
(3)参考以前所做的交易,管理者是否能够充分掌握公司的营运状况?
在这方面,巴菲特所领导的伯克希尔公司的年度报告是很好的榜样。在伯克希尔公司的年报中,以下讯息都能找到:伯克希尔所有下属公司的收入、帮助股东判断公司营运状况有帮助的讯息。不但达到一般会计准则的要求,还提供了许多额外的信息。巴菲特敬重那些采用同样坦白作风向股东公布资料的管理者。
巴菲特非常欣赏那些勇于公开讨论失败的管理者。巴菲特说:“大多数的年度报告都是虚假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个公司都在犯错误,只是大小不同。但是,大多数管理者所提出的报告都太过乐观,而不据实以报。这些经理们只考虑他们自己的短期利益,不顾股东的长期利益,但是长久下去,每个人都会受害。”
巴菲特相信,能公开承认错误的人更有纠正错误的机会。在每年年报中,巴菲特总是把伯克希尔公司的经济现状和管理成果,一五一十地向股东们介绍,包括好坏两方面。过去他曾经承认伯克希尔在纺织业和保险业上面临了困境,也承认自己在管理这些企业时所发生的错误。在伯克希尔公司1989年的年报中,巴菲特列出了他曾犯下的错误,并命名“头25年的错误(精简版)”。两年之后,改名为《每日错误》。在这里面,巴菲特不只承认错误,同时也列出因为他未能适时采取行动所丧失的机会。
有人说,巴菲特之所以敢轻轻松松地公开承认错误,是因为他持有42%的伯克希尔普通股股票,根本不用担心会被公司解雇。这的确是事实,但营运报告上的改进也是有目共睹的。巴菲特认为,一个管理者对股东们开诚布公,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他说:“误导他人的主管,最后也将误导自己。”
三、管理阶层是否能够对抗“盲从法人机构”
如果说管理层只要勇于面对错误就可以增长智慧和受到股民们的信赖,那么为什么还是有许多年度报告只披露成功的业绩呢?既然分配资金会如此简单和符合逻辑,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资金运用不当的事情发生呢?巴菲特将其原因归结为“盲从法人机构”。“盲从法人机构”就好像旅鼠(生活在草原上的一种老鼠)盲目的行动一样,公司管理者倾向于效仿其他经理的行为,不管那些行为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巴菲特声称,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令人吃惊的发现。在巴菲特没有步入投资界之前,他一直认为那些经验丰富的管理者都是极其诚实而又聪明的,做出的决策都是理性的。但当他步入投资界后,他才知道:一旦盲从法人机构开始发酵,理性通常会大打折扣。
巴菲特认为盲从法人机构的行为会出现在以下几种情况:
(1)一个机构拒绝改变它目前的运作方向;
(2)就像工作占用了所有可用的时间一样,所有的计划与并购行为,也将会消耗全部的可用资金;
(3)在每项业务上,不管经理人员的筹划有多么不明智,都会迅速获得属下的支持,他们提出详细的报酬率及策略研究作为回应;(4)盲目模仿、争相攀比同类公司的行为,包括扩张、收购、制订主管人员的薪资或者做其他的事。
在很早以前,伯克希尔所属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总裁杰克·林沃特,帮助巴菲特发现这种盲从行为的毁灭力量。当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在收益不足,甚至赔钱的情况下承保的时候,杰克·林沃特拒绝再签发任何新保单,并离开了这一市场,致使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损失甚微。同样地,在储贷业界通行的策略偏离正轨的时候,芒格与巴菲特当机立断改变储贷企业的投资方向,也为公司降低了损失。所以,巴菲特一直认为,管理阶层是否能够对抗“盲从法人机构”是投资一家公司前必须考虑的因素。
财务准则:市场成长与保留盈余一致
我宁愿对的模模糊糊,也不愿错的清清楚楚。
——巴菲特
巴菲特衡量管理行为和经济表现的财务准则,是以某些典型原则为基础的。首先,巴菲特关心的不是某家公司在某一年的经营业绩,而是看重该公司在4—5年的平均业绩。巴菲特认为,公司的获利不是一成不变的,用一段时期内的平均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对那些宣布公司年终业绩惊人,实际上却不反映真实价值的会计手法巴菲特也没什么耐性。相反,他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关注证券收益,而非每股收益。
2.计算“股东盈余”,以了解公司的真正价值。
3.寻找经营利润率高的公司。
4.公司对其拥有的每1美元,是否创造了至少1美元的市场价值。
一、股东权益报酬率
市场上流行用公司的每股收益情况来评价一家公司的年业绩。诸如在过去一年中,每股收益是否有所提高?是否高到可以吹嘘的地步?巴菲特则认为,每股收益是个烟幕。因为很多公司都以保留部分上年度盈余,做为一种增加公司股权资本的手段,所以,巴菲特认为,对于每股收益这种表面数据的增长,不必过于兴奋。如果一家企业通过增加10%的股权资本,使其每股收益提高了10%,那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样做,与把更多的钱存入银行,使利息增加没有什么两样。
巴菲特主张,评价和衡量一家企业或公司管理获利能力的最重要指标是“股东权益报酬率”(没有不当的融资与会计上欺骗的方式等),而不是看公司每股收益是否持续增加。因为这一指标着重从股东利益角度出发来考评一家公司,同时又注重公司现有资本投入的有效率。所以,巴菲特比较喜欢以股东权益报酬率——经营利润(分子)对股东权益(分母)的比例,作为评估公司年度表现的依据。
在运用股东权益报酬率之前,巴菲特建议投资者需要做几项调整:
第一,所有可出售的有价证券应该是以成本计价,而不是以市价来计算。因为股市的总体价值会严重影响某一公司股东的证券收益。比如,当牛市出现时,整个股市大幅上扬,因此公司的净值大大提高,那么即使公司的运营收入大幅增加,也会因为分母更大而使股东权益报酬率降低。相反,当熊市出现时,市价的下跌会减小分母,这会让普通的运营状况比实际看起来好得多。
第二,投资人也必须有能力控制那些会影响营业盈余的各种不寻常因素。巴菲特排除了所有的资本利润和损失,以及所有可能增加或减少运营收入的特殊事项,他正努力设法独立划分出企业各种特定的年度绩效。他希望知道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管理层能创造多少运营收入。他一直认为这才是衡量公司业绩的最好办法。
另外,巴菲特始终认为,一家优秀企业应能在没有或极少负债的情况下,用股权资本来获得良好的股东权益报酬率。他对公司借由增加其负债比率来提高股东权益报酬率的做法不感兴趣。他说:“好的商业或投资决策,是不用借助负债的杠杆作用就能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经济成果的。而且,高负债的公司在经济衰退时容易受到攻击。”巴菲特宁愿在财务品质上犯错,也不愿以增加负债的方式拿伯克希尔股东的福利冒险。
尽管巴菲特很不愿意增加负债,但是一旦确实需要举债时,他也不畏惧。巴菲特通常在预料到未来使用状况之前借债,而不是在有明显的用钱之需,甚至急需用钱时才去举债。他说:“如果在决定收购企业的时候正好有充裕资金,那当然是最理想的。”但经验告诉他,实际情形往往相反。货币供给宽松会促使资产价格上扬,紧缩银根,利率调高则会增加负债的成本,同时会降低资产价值。当市场上出现理想的收购价时,更高的利息率很可能会减损交易的吸引力。所以,巴菲特认为,在管理公司时,最好把资产和负债分开。
这种先把钱借来,以求将来可以用在绝佳的商业机会上的经营哲学,对短期盈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巴菲特只在确信未来的经营会带来比目前债务成本更高的利润时,才会采取行动。由于得到合适收购的机会有限,巴菲特希望伯克希尔公司时刻做好准备。
负债是很有学问的,不能盲目,多少负债比例才是合适的?巴菲特在这一点上没有提供任何建议。但是可以明确的是:不同的公司根据其现金流不同,而有着不同程度的举债能力。对于那些必须靠相当程度的负债才能达到较好的股东权益报酬率的公司,应该抱持怀疑的态度。
总的说来,股东权益报酬率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让我们预估企业把盈余再投资的成效。长期股东权益报酬率20%的企业,不但可以提供高于一般股票或债券一倍的收益,也可以经由再投资,让你有机会得到源源不绝的20%的报酬。
二、股东盈余
巴菲特警告投资者应当注意,会计上的每股盈余只是评估企业经济价值的起点,绝不是终点。他说:“首先要知道的是,并非所有的盈余都代表相同的意义。”他指出,资产利润比高的公司,其会计报表中的利润只是表面的,可能披露的是虚假的收益。因为通货膨胀实际上征收了高资产企业的大量通行费,使这些企业的盈余变得虚无缥缈。会计上的每股盈余只在分析师用它来估计现金流时才有用。
巴菲特又警告说,现金流同样不是一个评估公司价值的完美工具,它经常会误导投资者。现金流适合于评估初始投资很大而后续投资较小的企业,如房地产、油田、电报电话公司、公路桥梁公司等。而对那些需要持续投资的公司,仅仅用现金流的方法是无法正确评估公司价值的,比如生产制造型企业。
一般地讲,现金流量的习惯定义指税后利润加上折旧和摊销等非现金费用。根据巴菲特的解释,此定义的问题出在它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资本支出。公司在其生产年度中必须将多少的年度盈余用于购置新设备、工厂更新及其他为维持公司经济地位和单位产品价格所需的改善费用上?巴菲特根据多年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在美国,大约有95%的企业的资本支出正好相当于公司的折旧率。巴菲特说:“你可以将资本支出延迟一年左右,但是若长期下来仍然没有做出必要的支出,交易必然会减少。这项资本支出与公司在劳工与设备上的支出一样,都是企业营造所需的费用。”
由于强力收购致使现金流的概念和方法运用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巴菲特认为,“现金流的数字”通常是被公司和证券行业的市场商人使用,用来把那些不合理的解释为合理的,以促成一些原本不可能成立的交易。当利润不足以支付垃圾债券或无法支持愚蠢的高价时,很容易诱使人们去关注现金流。巴菲特说:“除非你愿意抽出那些必要的资本支出,不然把注意力全部放在现金流量上绝对是死路一条。”
与现金流相比,巴菲特更倾向于使用“股东盈余”来评估公司价值,即公司的税后利润加上折旧、摊销等非现金费用,同时,减去资本性支出费用以及可能需要增加的营运资金量。巴菲特承认,股东盈余并没有提供许多分析师所要求的精确计算结果。原因很简单,计算未来现金支出经常需要严格的估算,但这里采用的方法是粗估法。尽管如此,巴菲特还是说:“我宁愿对的模模糊糊,也不愿错的清清楚楚。”
三、毛利率
巴菲特认为,如果管理者无法把销售收入变成利润,那么再好的投资都是枉然。在他的经验里,习惯于高成本运营的经营管理者会继续找到办法增加经常性支出,相反,只需低成本营运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则会设法节省开销。
对那些不断增加开销的经营管理者,巴菲特一向是不屑一顾。同样是这些经理,必须提出改善计划把成本反映到销售上。每当一家公司公布它的成本削减计划时,巴菲特就认为,这家公司对“开销与股东们之间的意义”毫不了解。巴菲特说:“真正优秀的经理,不是那些在早晨醒来说‘我要在今天削减成本’的人,这如同那些早晨醒来,决定呼吸的人一样,是十分可笑的。”
巴菲特非常赞赏威尔斯法哥银行的卡尔·瑞查德和保罗·海山,以及首都/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汤姆·莫菲和丹·柏克,因为他们毫不留情地删减不必要支出。巴菲特说:“他们都厌恶比实际所需多出来的数字。
而且,此两对管理体系,即使是在利润创纪录的情况下,也会和承受压力的时候一样拼命地删减支出。”巴菲特自己对成本和不必要的花费也很强硬。他对于伯克希尔公司的毛利率非常敏感。他了解任何企业经营所需的合适的职员数目,而且相信对公司的每1美元销售,都有一个合适的费用水平。
在低成本运营方面,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典型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