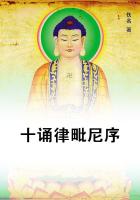他反拿起她的左手,绕到了她的身后去:“我听你弹琴的时候,你的手太紧张了,要用最最放松最最自然的状态,把手指张开按弦。练习的时候,当你的四个手指都按住同一根弦的时候,刚好四个指尖都处在正确的位置。”他带着她的手摸索到一个吉他品位上,“就像现在这样,手放到5品上,每个手指都头是压在各个品丝的前面一点儿,就是按各个品的最省力的位置。如果你在这一品上练习爬格子,你的手没有任何压力,起不到任何开手效果。有个小窍门就是把手往前面移一品。这样手不能刚好压住合适的位置,但是又不是相差太多。然后开始爬格子。然后你可以依次练习四品、三品……以此类推。记住,最重要的是音准!每天不要少于二十分钟,但也千万别练得太猛,要是让手部过劳就得不偿失了。”
说完这一大段,他松开了她的手。
明蓝回头,仰面朝他望了一眼:他站得直直的,脸上平静无波。
她揉了揉自己的脸颊:不自然的僵硬,发热的皮肤,就连嘴角微微带着的傻笑的弧度还没完全收敛起来。
“你没什么想法要和我说么?”
她一惊一乍地嚷了一声:“诶?我什么想法?”她的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甚至没太明白他意之所指。
然后她立马收到了南庆的一个“大白眼”。虽然他目不能视,不能真正朝她翻出个鄙视的白眼,但他那副神情活脱脱就是一副气恼又轻蔑的味道:头微上扬、一只脚懒洋洋地往前伸了伸,手叉了一下腰,又放下了,摇着头,“哎”了口气。
他低吼道:“明蓝,我刚教你的,你到底听了多少?”
一个半小时后,南庆宣布下课。明蓝把吉他靠墙一放,搓了搓按弦按到发痛的手,下意识地长呼出了一口气。
南庆也放下自己手中的吉他:“你有没有后悔找我学琴?”
明蓝道:“严师出高徒,我才不后悔呢。”
南庆笑说:“等你练到我觉得OK的时候,师父送你一把好琴做奖励。”
明蓝看了一眼他自己的吉他,说:“我不要什么琴,只想在每节课结束后,听你弹一首曲子。这便是奖励了,行么?”
南庆点点头,拿起吉他拨弄起来。
前奏过后,明蓝怔住——他弹的不正是《檐前雨》么?只是他把曲子移植到了吉他上,编曲方面做了不少改动,可仍然听得出是这支曲。
“吉他的弦音更容易模仿雨声的叮咚,能显得整首曲子更加轻盈生动,所以在我过往演奏这首曲子的时候,也常常都是与吉他合奏的。”一曲过后,南庆抬起头,对着她的方向轻轻说道。“也许有一天,我弹独弦琴,你弹吉他,我们能合奏出这首《檐前雨》。”
她的心里被凄然的情绪占满,喃喃道:“我恐怕是不行的。”
他的眼睛大概是因为没有焦距,虽然正对着她,却并不似在看着她,而是穿过她的身体、投向不知名的远处。明蓝却一时间错觉,他的眼神像是能洞穿人的心事。
“你在想江淮?”虽是问句,他的声音里却是笃定的。
他的话提醒了她:时间不早,她该回到江淮那里去了。
“南庆,我该回去了。”她向他告辞。
他忽然朝她的方向抓了一把,她吓了一跳,停住了起身的动作,而他也凑巧握住了她的手。
似乎是感到自己的举止不妥,他一瞬间就松开了他,吞吞吐吐地道:“我让人准备了我们两个人的午饭,吃过再走吧。”
他的样子看起来有些孤独惆怅。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奇妙的特质,有时候明明你觉得他很开朗阳光,可有时候又会在某些瞬间,让你感受到他的敏感脆弱。明蓝心软了。
“好吧,反正江淮也说过,我如果饿了,可以在外面吃。那我就不客气了。”
她刚说完,就见他的面色有些冷淡下来,仿佛在按捺下某种不好的情绪。可过了没一会儿,便又笑嘻嘻地吩咐佣人摆饭,在餐桌上对她的招待也很是热情。
“你来越南也大半年了吧?我得考考你,知不知道会安有哪三大小吃?”他发问道。
“我好像听人说过,什么‘白玫瑰’之类的,记不清了!”
“你一次也没尝过?”
“给你送帖子那次,是我头一回来会安,匆匆忙忙的,就回去了。”
南庆说:“我右手边第一盘便是你说的‘白玫瑰’。”
明蓝看过去:雪白柔软的米皮包裹着未知的馅子,捏成了玫瑰花样的形状,在盘子里摆开几朵,花心处还撒上了虾松,边上摆了一碟鱼露调制的汁水,确实很符合“白玫瑰”这个菜名。
南庆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明蓝挟起一朵,尝了尝味道:平平淡淡,算不上有什么出众之处。
“味道怎么样?”
“很好吃。挺……清淡的。”她找不到其他的形容词。
南庆撇嘴一笑:“假得很。”
她也跟着笑了,并不因为被识破而感到不安。“这道菜只能说,外形尚可,味道嘛,乏善可陈。”
南庆说:“我喜欢你说实话。并不是所有主人都期待着客人对自己家的菜式做口不对心的赞美。何况,咳,”他笑道,“这些菜又不是我做的,我干嘛要替厨子听那些虚话呢?”
明蓝扑哧又笑。
“其实吧,我也吃不太惯这个,毕竟我不是土生土长的会安人。只不过我也很少指定厨房做什么菜,他们又都是本地人,自然做本地菜比较多。再者,我想着你来会安一趟,尝点当地特色的小吃也不算白来一遭,就让厨房做了这些。与‘白玫瑰’相比,倒是另外两道——炸云吞和捞面还不错。”
明蓝好奇地打量着另外两道菜:这越南云吞的模样和中国的云吞迥异。油炸成金黄色的脆皮上直接盛着馅料,并不包裹在云吞皮内。捞面的外观倒是挺“正常”的,面里放着几片生菜叶、豆芽等配料,用酱调和着,看上去还挺勾人胃口。
南庆的面前已经另外用三个小碗盛好了菜。明蓝看了一眼问:“你不开动么?”
他挟了一口“白玫瑰”送入口中,咽下之后,抿嘴笑道:“你只顾你就好。”
明蓝想起上次他曾经说过“因为吃汤河粉之类的东西时,总是难免会有油水溅到脸上,有时候还会捞空”,心中一动,道:“南庆,你这个主人若是拘束,我这个客人不是更放不开么?
南庆微楞,终于还是举起筷子,往盛着捞面的碗里捞了几根面条。他吃得很小心,并没有什么酱汁溅出来。
明蓝感觉得到,他其实是个自尊心很强的男人。因为目盲,所以更在意自己的仪态。她又一次觉得自己的心揪了一下,可又不是普通的同情,而是一种糅杂着欣赏和惋惜。
“南庆,”她托着腮,说,“你吃饭的样子很好看,真的!”
南庆放下筷子,用餐巾抹了抹嘴道:“你不吃饭,一直在看我吃饭?”
她羞道:“我……我不是故意的。”她的确不是有心的,可就是傻愣愣地看着他吃捞面、吃云吞,看了足足有五六分钟。
“我居然觉得,你说的像是真心话了。”他夸张地用手指挠了挠耳廓,“该不会是我耳朵也出问题了吧?”
“是真的!南庆,你吃饭一点都不狼狈!”她急着道,“在你面前说谎才不容易呢,我哪有那本事!”
南庆先生微笑,慢慢地,似乎因为联想起什么沉重的事,他的脸上起了些微的变化:“明蓝,对谁说谎都不是最难的,说谎最难的是骗过自己。”他的声音有些低沉。
她察觉到了。“你常说谎么?”她问。
“不常。”他说,“可有时,也会说的。”
“骗过去了么?”她问。
“不知道有没有瞒过别人,反正,没有一次能骗过自己的。”
她望着他脸上的表情,内敛之下是绷紧的痛楚,睫毛投下的阴影令他的表情增添阴郁。
“我们认识时间虽不长,你的劝导却使我获益良多,在你面前,我还算坦诚吧?连我最难以面对的秘密我都与你分享了。南庆,如果你相信我,像我这样的相信你,你也可以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我虽不能实际做什么,却也愿意做你的好听众。”
他的头垂得更低了:“你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我是被我阿姨收养才来到越南生活的。”
“记得。”
“十五岁之前,我的家在中国。我有父亲,也有母亲,还有一个妹妹。”
明蓝静静地等待他说下去。
“我的母亲早在多年前就去世了。我的父亲……准确地说,是我的养父,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把我送给了我阿姨,自此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我。可就在昨天,我突然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接到了我同母异父的妹妹的电话,她告诉我很多事,包括我的父亲是如何地懊悔、如何想念我,而我……我的直觉居然是相信她的话!我忽然觉得,过去那种被人抛弃的感觉才是我的错觉,现在这种被呼唤、被需要的感觉才是真实的!”
明蓝的心被他所诉说的事震撼了,他的周身笼罩着一种冰凉,而他也的确在轻轻颤抖。她霍然起身,把手搭在他的脸庞,将他轻柔地按向自己:“因为那是你一直希冀的感觉,对吗?”
她的身体柔软温暖。他有些依恋地朝她蹭了蹭,深吸了一口气说:“我说过,我也是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这不止是因为失明,更因为我尝到过一再被人放弃、亦或是沦为次选的悲哀。这些年,我总是努力让自己心情平复,不要去钻牛角尖,不要怨天尤人,可有时候,我忍不住……”
她从来没见过他情绪这样失控的样子。她感到慌张和心痛,可又莫名地因为自己被认可和信赖而生出一种欣慰来。她像对待一个小男孩一般揉了揉他的头发,道:“南庆,既然你的父亲呼唤你,你会回应他吗?”
他似乎失了方向,迷惘道:“我应该回应么?”
“你有理由不回应,”她说,“毕竟是他先放弃了你,你当然有充足的理由不原谅他。”
南庆摇头:“其实当时的情形也不能怪他。我失明后,我的母亲经受不了打击,也过世了,而我也从此对我的父亲一句话也不说,我还被送去看心理医生。可是没有用,我和父亲的隔阂始终无法消弭。时间久了,没有人能继续忍受这样冰窖一样的家庭。而且,心理医生说,这样的环境,对我妹妹的成长也不利。我想,我和他闹到这样的僵局,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我也难辞其咎。”
“你在为他辩解,你意识到了吗?”明蓝捧起他的脸。
“我并没有完全原谅他。”他闭上双眼。
“我了解。”
“他得了重病。我……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回去见他。”
她的手指轻划过他紧闭的双眼。“南庆,你愿意花时间教一个认识不久的人弹吉他,也不愿意去见一个养育了你十五年的人吗?”
几天后,她接到了一通电话,是南庆从机场打来的。
她事先的确没想到,南庆会特地在登机前给她打电话,可接起后听到他的声音,她又觉得这通电话仿佛是意料之中的事。
他说:“明蓝,我现在在机场等候登机。你说得对,我该回去看看,我也……想回去。”
“嗯,听自己的心就好。”她不自觉地微笑起来,“对了,昨天我收到演奏会的票了,谢谢你,我会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