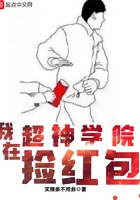人群中起了低低的赞叹,邢子婧竟就那样当着众人掩面而泣。
“哭什么?这不是来了么?”
白亦诚依旧是平日的模样,风采熠熠,虽不说有多么强势的魄力却举手投足间都看的出极好的修养。
他上前轻轻的环了环邢子婧的腰,低声安慰着。“喏,生日快乐。”男人递过去了一把切蛋糕的刀子,上面用极细腻的蕾丝系出了一个结。
原来那一车玫瑰,竟是一块硕大的工艺蛋糕。
“快别哭了,妆花了。”白亦诚低声附耳提醒,邢子婧的脸当即就窘迫的红了。如此,远远看去,这只是情人间的甜蜜温存。
切蛋糕,开香槟。宁夏终于见了邢子婧神采斐然的模样,她轻轻的斜靠在聂少的怀里,和来来往往的宾客一一碰杯。
这怎么看,都好像两个人是一对新婚燕尔。
有些人的幸福,就算流泪哭泣却依旧甘之如饴。
“没想到,让这小子这么一弄到还挺感人的。”乔湛良在一旁哼笑,饶有意味的瞧着邢子婧与白亦诚。“那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么?花花公子!”宁夏塞了一句回去,他们这些人啊,自己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竟还见不得别人幸福,真是有够‘无耻。’
“我什么样?我怎么不知道。”乔湛良似是有些不服气,虽说那花花公子一词形容的颇为贴切,与他平日的作风不出一二。“您这么聪明能不知道?”宁夏一眼白了过去,“乔少您跟我装傻可真就没什么意思。不陪你玩了,我要去找子淇碰杯。”宁夏挪步从乔湛良身边走开,只剩下乔湛良定在原地,脸上浮现出蓦然的笑意。
“怎么样,够辣的吧。”
乔湛良正望着某个身影走向邢子婧,身旁却已经靠过来了人。方时佑掌中酒杯轻扬,向乔湛良略略示意。
“还可以,我平常口味比较重。”乔湛良微笑着,抬手与方时佑碰杯。“所以,这在我看来无疑是甜。”乔湛良脸上的笑意渐浓,目光望向方时佑,总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两人之间默默散开。
方时佑不再答话,亦笑着作为回应。他心道却倒某人嘴硬,明明被骂了是猪却还能如此平和。
不过,如此看来他倒是铁了心要玩了。
方时佑握着酒杯走开落座在休息区的沙发上,目光在光流婉转间缓缓散开。
“感情是这主人的朋友,难怪不曾见过,还不知道是哪家的千金。”女伴已经顺势坐在了方时佑的身边,语气里着重了‘千金’二字,那番轻蔑已经盈盈绕绕的出了口。
轻哼着低笑两声,却没得到方时佑任何的回应。女伴有些疑惑,男人明明刚才冲着乔少和那个女人明朝暗讽,为什么此刻又一言不发?其实,男人极少把针对一个人的种种表露在外的,那么他但凡是表现出来,便必定是另有一番意思的。
女人的心思向来是深的像那海底的针,而她们揣摩的是一个同样心思城府深沉的男人。相较于有目的的投其所好,女人和男人的过招便注定是惨败的。
女伴的眼角便懦懦的瞥向了方时佑。她一向都是顺着男人的,在某些方面更是刻意迎合。可明明自己迎合了,却发现今天的男人并不买自己的账。
方时佑如何听不出女伴口气中的明升暗贬的意味呢?他的目光由于女伴的指引再次看向了某个站在邢子婧身边的背影,齐齐的发尾飘摇在脖颈随着身体的运动一甩一甩的。
“你自己玩儿,我在外面车上等你。”突觉得无趣,男人向女伴支会了一声便起身离开了沙发。
地下停车场里森冷的灯光笼罩在一辆黑色的大奔上,淡淡的雾气正从男人指尖的火星上缭绕而起。方时佑就那样仰靠在驾驶位上,西装领带的早已经扔在了车后座上,袖子散乱的撸到了手肘处,而领口更是散开着,竟有几分凌乱的魅力。男人星眸微敛,许久才提起手里的烟吸上一口。
烟灰一点一点的散落在窗外,良久的无言换来心中的平静。男人终于掐掉了烟,却喉咙中一阵不适袭来,俯下身子低低的咳了两声。
生日宴是要进行到很晚的,只是宁夏第二天还要上班,便提早向邢子婧告别说要先回去了。邢子婧知道宁夏的性子,自然在这件事情上不会挽留。他们有的是时间玩闹,又哪里像别人偏偏去在乎是分分秒秒的。
宁夏要回去了,自然有人是要跟着一并离开的。宁夏已经不再扭捏,与乔湛良并肩到了地下停车场。
“冷了吧,来。”乔湛良利落的拖下了自己身上的外套架在了宁夏的肩头。他已经发现了她的微微颤抖。
秋夜的风凉了许多,加上地下车库空旷,风劲,宁夏冻的不由得搓手。其实她更冷的地方,是膝盖。在宴会厅里坐了那么久,人早就没了活力,更别提还穿成了这副模样。
外套上还残留着男人的体温,突然降临,着实让宁夏从肩头暖到了指尖。
某人的车就隔着过道停在了方时佑的后面,很自然的,男人通过后视镜将一切看得一清二楚。
脸上的微笑,肩头的暖衣,竟连上车时亦周到的为其开门…
方时佑的目光皱然聚起,就那样瞧着他们。他们就那样上了车,不一会儿发动机的声响就回旋在了停车场里。
灯光极好的将方时佑的脸分成了明暗两截。一片漆黑里是他深不可测的目光,而森冷的白灯光下,是他性感削薄的唇。
黑与白,明与暗,就在这样一个时刻交融在了一起,其间纠葛繁杂又一两句话可以表述的清楚的呢?
或许,迄今为止方时佑的这位女伴做的最令他大少爷满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她在这场生日宴会上未散场就离开了。
女伴刚刚坐定,方时佑就发动了车子,几把倒出车位,竟在车库里面就将车子驶的超了速。女伴的安全带还没系好,由于动力冲力过大一头扎在了前挡风玻璃上。女人疼的闷哼,刚想说点儿什么撒娇的话来博得男人的爱怜,却刚抬头就发现男人的眼睛直盯盯的望着前面的挡车杆。到了嘴边的话就女人就那样咽了回去,聪明的女伴才能呆的长久,这点并不是女伴的自以为是。
汽笛滴滴的叫嚣着,只怕是慢上几秒男人都要撞过去一样。车杆开启,汽车嗡的一下就冲了出去。男人脚下的油门,压了又压。
以男人的性格,飙车这事还是极少发生的,至少现今的这位女伴以前从没见过他这样。
女人的直觉向来是比较灵敏的,女伴的手死死的抓着头顶的把手,怯懦的眼神一次次的飘向男人,最终变成了惊恐。
方时佑的车是在一个路口突然减速的,而前面一辆白色的宝马车刚刚越过白线,飞驰而去。
两辆车,只隔着一个红灯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