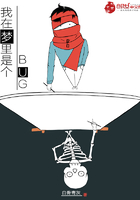是我爱错了人吗?忍了一早上的眼泪却在他面前流了出来,所有的软弱都在这一刻显现,“十年……”我呜咽着掩面而泣,“我爱了他十年,可是到头来却发现,原来我一无所有。”
“别哭了!”他蹲在我面前,拿出一方素锦的帕子放到我手里,我毫不客气地抓过来捂在眼睛上,眼前陷入一片黑暗,只余鼻端萦绕着的淡淡檀香,眼泪迅速浸湿了帕子,我却仍止不住地抽泣。
他轻声地安慰我,“那就庆幸你已经拥有了十年的爱恋,在他不爱你的时候,又能及时发现。你并不是一无所有,你有十年的美好回忆,有希望,有未来,还会有很多美好的人,美好的事在前方等着你。”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股让人安心的力量,我渐渐止住了哭泣,用他的帕子搓了搓鼻子,一时觉得难堪,又觉得自己很可笑。我扬扬手里的帕子,“脏了,洗完再还给你。”
我忽然意识到我刚才伤心欲绝时说了什么,我说爱了叶澜修十年,夏青芜今年才十八岁,爱了十年岂不是从八岁就开始了,我慌忙地想弥补这个失误,“呃……十年就是个范范之数……”
“嘘……”他竖起食指放在唇前,“我知道。”
我没有再越描越黑,不管他知道什么,我都已经不在意。在他面前,我没来由地觉得安心,即便他知道什么,也不会伤害我。
“有什么打算?”他问我。
“我要离开这里。”虽然带着浓重的鼻音,我依旧说得无比坚定。
“你想好了?”他挑眉再问,“你知道出了太子府你会面对什么吗?你的身份为世人所不容,只能隐姓埋名地过日子,而就我冷眼看来,我那大外甥还是心里有你的。你会不会后悔?”
我义无反顾地摇头,“不悔!”
“不是一时意气?”
“不是。我想得很清楚,他给不了我想要的情有独钟,我宁可什么都不要。”
他点点头,“好,我助你离开这里。”
我没想到他这么痛快地答应帮助我,“那太好了,我正发愁怎么出去呢,门外都是太子府的侍卫。”我高兴之余,情不自禁地抓住他的衣袖。
“啊!手!手!”他呲牙咧嘴,我这才发现自己正用受伤的那只手抓着他。
我慌忙放开他,“对不起,一激动又忘了。”
他止不住地向我抱怨,“爷这浑身都疼了一夜了,好歹让我消停会儿。”
浑身疼?想到昨晚差点儿和叶澜修成的事儿,我更是心虚不已地偷窥着他,此地无银地清清嗓子道:“除了手,我别处可没受伤。”
他白了我一眼,“说起来倒要谢谢你,不过我想问问怎么就半途而废了呢?”
我这脸烧得都能摊鸡蛋了,“他说……‘恶心’。后来又知道了骆寒衣有孕的事儿。”说出“恶心”这个词儿,我忍不住撇了撇嘴角,又有要哭的感觉,忍不住泪眼汪汪地问他:“恶心吗?”
他歪头仔细想了想,须臾笑道:“是有点儿。”
他的笑容温暖又带着一丝促狭,让我本来觉得委屈又屈辱的心忽然就释然了。是啊,在这件事儿上,最感到恶心的人应该是他。谁愿意睡得好好的突然就产生一种被强了的感觉?
这只能说是我的错,我不该无视云谨言的感受去招惹叶澜修,我这是将云谨言置于何地呢?
“对不起,我昨天晚上昏了头了,只想用这种方法留住他。我不该这样毫不顾忌你,你骂我吧,是我该得的。”我诚心诚意地向他道歉,却也知晓,别说骂我,换了我是他,杀人的心都会有。
见我面红耳赤,无地自容的模样,他倒反过来安慰我,“别担心,我只能感应到你的疼痛,其他的可感觉不出来。”
我依旧羞愧,向他起誓道:“我这辈子不嫁人,大不了绞了头发做姑子去,绝不让你再受这等侮辱。”
他哭笑不得地看着我,“怎么说的爷跟个黄花大闺女似的,还需要你来保护我的贞洁了。”
眼见日上三竿,已近午时,算算叶澜修和骆寒衣此时在宫中谢恩,皇后娘娘肯定会留他们一起吃午膳的。大约午膳过后,他们也就该从宫里回来了,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他们,问云谨言道:“你什么时候能把我弄出去?”
云谨言起身,从衣襟里掏出一大堆瓶瓶罐罐,一边向我解释道:“都是莫伤给我的,说是以备不时之需,没想到今天真用上了。”他挨个看着瓶子上的签子,“这是玉露生肌膏,治外伤的、这个是百毒解,这个嘛……是迷药,这个是……人渣。这个是回魂丹,哦对,是这个,归西丹。”
他递给我一个拇指大的白瓷瓶。我狐疑地看着他,“这个有什么用?”
“这可是好东西。”云谨言一脸的神秘与得意,“吃下去,两个时辰后,脉搏全无,呼吸也会停止。”
“毒药?”我一惊,手抖了一下,那个瓶子直往地上坠去,被云谨言一伸手抄住了。
我哭丧着脸,“我只是被甩了,还不想死。”
云谨言一脸的恨铁不成钢,“看你那点儿出息,连一哭二闹三上吊都不会。怪不得我那大外甥移情别恋,他就是算准了你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我嘴一扁低下头,心中无限的委屈。一哭二闹三上吊,不是不会,而是不屑。如果感情中夹杂了这样的手段计谋,那么情感也就不再纯粹。再者,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挽留一个人呢?如果爱已不在,我宁可留给他一个笔直的背影。
见我低头,云谨言重新将瓶子塞到我手里,“算了,不说你了。这个不是毒药,过三日,你自会醒过来,活蹦乱跳的跟以前一样。”
我赶紧看了看瓶子上的黄签,原来是“龟息丹”,而不是“归西丹”,我松了一口气,“直接说是‘假死药’不就得了,我还以为吃完后就真的吹灯拔蜡,驾鹤西去了呢。”随即,又不放心道:“万一真死了呢?”
云谨言笃定道:“不会,莫伤说了,这个药他自己吃过,当年他师叔鬼手崔心想要他的命,他就是靠这个龟息丹躲过一劫。”
虽然神医自己做过小白鼠,我还是不放心,“万一没等我醒过来,就被埋了呢?”
云谨言一拍胸脯,仗义道:“那爷就带人挖你去!一定能把你从土里刨出来。”
我略略放心,忍不住叮嘱道:“一定要看准了我埋在哪儿啊,一定要及时挖啊!万一我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棺材里,还被埋在地底下,那多恐怖。”
云谨言郑重点头,“你的命就是我的命,只要我不想死,就不会让你出事儿。”
我想想也对,我们两个是一条线上的蚂蚱,我若是挂了,可以说是买一送一,还得饶上他这个国舅爷。
我小心地把药收到怀中,“其实我只想离开太子府,倒没想着整出假死这么大动静来。不过这个龟息丹我留着,就当备用吧。你这些天也留意下太子府,万一有丧事传出,一定在第一时间带着铁锨去刨我啊!”
云谨言指天赌地表示义不容辞,方离开了太子府。
我继续想着我的逃跑大计,虽有了龟息丹,但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想用,万一出了什么纰漏呢,我这不是假戏真做,不想死也死了。比较稳妥的做法是找机会溜出府去,或者我可以像上次与妙霜赏梅那样,扮成仆妇混出去,又或者我可以让于烈夫人带着一个侍女来探望我,然后我扮作她的侍女,来一个金蝉脱壳。我胡思乱想,心烦不已。
下午时分,叶澜修自宫中回来,先到了长熙阁,我闭目假寐睡在床上。该说的都已说尽,若让我张口,只能是求他放我走,但我也知道,他必不会同意的。所以我们两个已经是无话可说,此时此地,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他来到床边弯下身为我掖严了被脚,久久地凝视着我,我闭着眼也能感受到他炙热的视线胶着在我的脸上。他伸手想抚上我的脸,我的面颊都能感到他手掌带来的一丝风,然而他的手伸到半空,终是叹了口气又缩了回去。我眼中漫过湿意,虽是闭着眼睛,眼眶中却蕴满泪水,随时都会从紧闭的眼线中滑落出去。
叶澜修并未久留,他叫来沐莲,问了问我今日的起居,留下句:“照顾好你们姑娘。”便离开了。我悄悄睁开眼睛,透过泪水,只能看到他模糊的背景疲惫而悲伤。
我再次闭上眼睛,感觉到眼泪顺着我的面颊滑落到枕头上,很快就晕湿了一片。我悲哀地意识到,其实我们两个都知道,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既然如此,何必还苦苦拉着对方不肯放手。不如离去,给他也给自己一条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