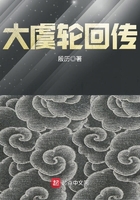翌日清晨,当阳光爬上窗棱,我转动着肿涩的眼睛,这才发现一夜未眠,连眼睛都不曾闭一下。我起身拥着被子坐在床上怔怔地发呆,昨晚发生的事儿是那样的遥远而不真实,仿佛大梦一场。
沐莲小心翼翼地站到门口,“姑娘醒了吗?现在梳妆吗?”
她声音怯怯不安,肯定是已知道了太子妃有了身孕,而昨晚叶澜修从我这里走出去再也没回来。我暗自苦笑,果真我在其他人眼里,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弃妇。
“好。”我应了一声,无论在别人眼里我是什么样子,我还是需要维持自己最后得那一点可怜的自尊,只是声音一出,我自己也吓了一跳,竟是粗噶得吓人。
我穿上里衣,看到被剑割伤的那只手,掌心的血已经凝固,伤口处木木的发紧。我赶紧让沐莲和沐槿帮着我重新清洗了伤口,厚厚地涂上莫伤配制的伤药,又用干净的白布细细包起来,这才松了一口气。
因为手上有伤,不能碰水,沐莲绞了布巾递给我,我用那只没受伤的手接过布巾敷在脸上,湿热的布巾贴在面颊上,服帖了每一个毛孔,酸涩的眼睛也得到了缓解,我仿佛从沉睡中又活过来一般。
这一刻,我已想明白了我的归宿,这个地方我已经待不下去了,这里承载了我太多的悲伤和屈辱,无论如何,我一定要离开这里,离开他。
沐莲窥着我的神色,见我只是淡淡,并没有满脸的伤心失落,悄悄地松了一口气,手脚麻利地为我梳了一个简单清爽的发髻,沐槿过来将一个梅花形的红宝石发簪插在我的头上,那红艳艳的颜色灼痛了我的眼睛,因为我身边再也没有人可以陪着我携手赏梅。我抬手拆掉那个红宝石梅花簪,在妆匣中翻捡了一下,随手拿出一个样子朴素大方的珍珠钗子。
沐莲在一旁为难地小声说道:“姑娘,大过年的,府里又有喜事,这个是不是太素净了。”
我的手一下子顿住,是啊,骆寒衣有喜,对于整个太子府乃至整个天煜国来说都是天大的喜事,我这里雪衣素钗的,不是给人家添堵吗!在大家的眼里,我这个没有名分的太子屋里人,在这个时候更应该表现出恰如其分的喜悦才是最和适宜的。我放下那枚珍珠钗,莹润的珠光被一匣子的珠光宝器映衬得顷刻黯淡下去。
沐槿见我怔住,偷偷用肩膀撞了一下沐莲,圆场道:“姑娘容貌清丽,本不需太过艳丽妖娆的饰物,简单清雅的更能衬托姑娘玉质。”说着从妆匣里拿出一个碧玉桃花簪插在我的头上,又为我戴上两个水晶珠花和一对绿玉缠银丝的耳坠,方小心翼翼地问我,“姑娘看,这样行吗?”
我虽无心思打扮,但更不愿以一副憔悴面貌现于人前,仿佛在向世人彰显自己的落魄失意。反正已经要离开了,何必给众人留下一个黯然失意的背影。我看看镜中的人影,点头道:“挺好,就这样吧。”
沐槿拿来一件淡绿色以白和樱色丝线绣着桃花花瓣的外衫帮我穿在身上,清新雅致又不过于素淡。我自己披上云水碧镶白狐领的厚披风,披风里有我刚刚放进去的几千两银票,我还没有蠢到把自己完全地净身出户。
我想了想,又从卧室的枕头底下拿出星冢挂在了脖子上,贴身藏在了衣服里。想来叶澜修在这个世上,有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不再需要这个了吧。穿戴整齐后,我向沐莲沐槿二人道:“我一个人出去走走,不必跟着我。”
二人对视了一眼欲言又止,终是拗不过我,沐莲满脸担忧道:“外面天寒地冻的也没什么好看的,姑娘出去透透气就回来吧,免得着凉病倒,太子殿下又要担心了。”
听她提到太子,沐槿唯恐戳到我的痛脚,偷偷又撞了沐莲一下,沐莲反应过来,赶紧闭了嘴。
我扭头快步出了门,感到自己再多待一秒都会崩溃,无法再维持表面的平静。我宁愿一人独自舔伤,也不愿看到别人同情的目光。
因为叶澜修在府中,侍卫并没有封锁长熙阁,我出了长熙阁的大门,直奔太子府的侧门而去,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离开这里,至于出了这个大门何去何从,我没有精力去想,天无绝人之路,我又有银子傍身,总不至于饿死!
穿过花园时,我不经意抬头看了一眼,冬日的花园万物萧瑟,本没什么好看,不知何时装点上了五色绢花,挂在枝头,猛一看真如一夜春风,百花竞开。我目中一酸,是为了贺喜府中喜事吧。
刚走到湖边,眼见穿过长廊就能到达东角门,却被斜刺里伸出的手臂一把握住了我的手腕。“你这是要去哪儿?”声音如我今早一般的粗噶难辨,我扭头看见了叶澜修布满血丝的双眼。
我拨开他的手,淡然道:“我要离开这里。”
他痛苦地以手捶了一下旁边的树干,震落了树上的几朵绢花,他压抑着低声恳求,“别闹了,回去吧!我这些日子真的很难,别在这个时候跟我耍性子了。”
他以为我在耍脾气,在使小性子吗?我忽然觉得好笑,原来不光是我不再了解他,他也并不了解我。
见到我的漠然,他的眼中透出深深的恐惧,“你到底让我怎么做才肯原谅我?好,我发誓,等到骆氏倒台,我就杀了骆寒衣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这样总可以了吧!”
他的话让我震惊不已,短短的一天,他给我的冲击真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强烈。我看着他,仿佛看着一个陌生人,“我没有要你为我杀任何人,你自己犯下的错误,不要用别人的生命来洗刷,那只会让你背负更多的罪孽。如果你对我还有一丝的爱恋与尊重,就放我离开,让我躲得远远的。”
“不,我昨晚想了一夜,我不能就这样失去你。没有你,我所做的一切都不再有意义。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用我全部的身心对你好,再也不会有其他人,相信我……”
“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我悲哀地看着他,“有些事情,既然发生,就没法回头了。我回不去,你也不能。”
游廊那头跑来叶澜修的随从侍卫,“禀报太子殿下,宫里的赏赐到府外了,随来的公公说请您携太子妃进宫谢恩。”
我冷眼看着叶澜修,他挣扎了一番,晦涩道:“我去去就来,你哪儿也不要去,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你离开我,哪怕是绑也要把你绑在我身边。等我回来咱们再好好谈谈。听话,没有我的许可,这个府门你也出不去。”
他匆匆而去,留下我一个人在寒风中气急而笑,这算是给我的威胁吗?还是说将我软禁起来了。
看来是我太天真了,以为他还是那个对我百依百顺的爱人,而现在的他已经是别人的丈夫,还将为人父,早已不会只在意我一个人的喜怒,或者他还是在乎我的,因为在乎所以不让我离开。而这样的他,又是多么自私!将我的自尊和对他的感情弃之如敝屐,又苦苦纠缠着我留在他身边。
我忽然想起了那日云谨言所说的男人的劣根性,不禁苦笑,也许吧,男人都是这样的,只要有了合适的土壤,忠诚不过是口头随便说说的甜言蜜语。最让人齿寒的是,他对忠诚的理解仅限于对女人的要求,而对于自己却是双标的,在他的观念里,给了我爱,就可以随意地背叛我。又或者说,他觉得只要没有爱上别的女人,就已经是对得起我了,身体的出轨并不值得一提,我如此在意此事,倒是我不懂事,不知体谅。
我兀自伫立在湖边,对着冰封的湖面发呆,廊柱后面转出来一个人,默默地站在我身后。我微微侧头,眼角的余光看到一角雅青色的袍角,我重新看向湖面,低声问:“苏先生怎么也在这儿?”
身后的人静默了一会儿,才开口道:“跟你一样,本来也是要走的。”
我一怔,随即释然,骆寒衣和叶澜修已然锦瑟和谐,又有了身孕,苏宴几也应该放心了,没有再留下来守护骆寒衣的必要。我点头道:“外面天地广大,苏先生必能有所作为。”
“可是现在,我不能走了。”他的声音中透出一股执着。
“为什么?”我诧异地回头,这才发现他随身带着一个小小的包袱,貌似也就是几件换洗的衣服,此刻松垮地拎在指尖,包袱都快坠到了地上。
我试着劝说他,“苏先生辅佐太子的使命已经完成,现在说白了,先生留在府中也难以得到太子的重用。再说,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太子妃已经……”我深吸了一口气,还是觉得说不出来,只能含糊地带过去,“先生心愿已了,不如及早抽身,离开这是非之地,何必还要留下来自寻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