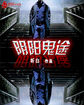无独有偶,这一天晚饭后,秋风送爽,圆盘的大月亮升起在东南方,月光如水。把门前的街道洗刷的白净白净的,街旁的树影让月光的画笔在地上任意地描摹,浓淡相宜。使整条街道显得即神秘又温馨,若是月亮上的吴刚嫦娥月树上的最美的花粉抖落在大地上了。石花在街门口与邻家女伴跳起了方格子,她们在地上用滑石划一了一个个方格子,圈起一条腿,来来回回地跳。跳烦了,又踢毽子。后来,女伴的妈妈叫她的女儿回家了。石花仰头相了一下天,这月亮精神十足的悬在正南的天穹上方,这么早上炕睡觉真是太可惜了。不如再玩一会儿和天上的明月做个伴。她又开始踢毽了,一边踢一边数:一、二、三、四……
“呜哇,呜哇。你……你……真会……”
石花正踢得有趣,数得投入。听到有声音漫过来。她猛得一下顿住。旋转着灵活的身子寻找着声音的发源地来自何方。
街口愔愔的。她的双眼迷惑地对着整条月带的小街梭巡了过去又梭巡了过来。一条灰暗的狗迈着碎步溜达过来。到了她跟前突然加快了步伐,从她的腿边擦过。一片树叶悄然从树上的降下,它不甘心地就这样地离开无限依恋的母亲和同伴,在着地的一刻,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做了四五个漂亮的滚翻动作,又借着微风的推力,来了一个紧急刹车,身体的边缘与平整的地面进行了磨擦,生发出了“沙沙沙”的声响。石花欲拾毽子,那声音再次响起,稚嫩,脆生,似曾相识。
“呜哇,呜哇,你……你……真……呜哇。”
声音来自天穹,是来自月亮的声音,是来自星星的声音。莫不是来自人们传说的月亮上的吴刚和嫦娥吧。
靠近院墙边的一棵粗粗的槐树有了动静,一只硕大的黑猫顺着树杆滑了下来。落地时,团团的,圆圆的。石花见那物三窜动两鼓涌。一下子拔高了两倍,竞然直立着对着她过来了。
“妈呀!鬼来了!鬼来了……”石花大叫着,咕咚咚跑进了院子,连街门都来不及关。
在灯光下纳鞋底的石花的母亲听说有鬼。头皮也是一麻一麻的,但出于一个母亲保护自已孩子的本能,抄起一张铁锨冲出了门外。街上早已空寂寂的了。
这样一个鬼的事件,石花总忘不了与草灵姐姐第一时间分享。当石花流着鼻涕,心有余悸地把新闻报告完。草灵姐姐并没有石花想象的眼睛瞪大十分悚然的样子,而是听了一个平常的故事的样子说:那不是一个鬼。
“不是鬼是什么呢?我当时吓得差点尿了裤子的。”
“要真是鬼呀——草灵调皮地张大了小嘴,做了一个咬的动作:鬼就会扑上前去,咬断你的脖子啦。”
“妈呀!不管是不是鬼。我黑夜再也不敢到街门口去玩耍了。”
接下来的日子,村里有关鬼的传言潮起,说叶花村来了一个小鬼,浑身都是黑毛。说鬼话,食人食。此鬼形踪不定。白天遁入了地下,夜间在村里显身。能飞椽走壁,能上房爬树。能入水进洞,能变大化小。还能惩恶习扬善。据说,领村一个叫包秃子的偷鸡贼,夜里来叶花村的皱老三家偷了五只鸡,刚出村外,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待他哼哼呀呀慌里慌张地找鸡时,哪里有鸡的毛毛。盯睛一看,前面跳跃着一个怪影子,还发出一声声的鬼叫,吓得包秃子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抱头鼠窜了。村子北头的武老奶奶,孤身一个独居在村边的三间小旧屋。那两天秋雨连绵。半夜时,她就寝的东间屋塌了,椽子檩子瓦块乱七八糟地砸在了老人的炕上。老人严严实实地裹在了里面。老人又喊又叫。可村里人听不见。可鬼听见了。嗖的到了眼前,又搬瓦块又搬桷子的。把她救了出来。第二天,她向人们诉说了这个事件,人们觉得不可思议,又感到钦佩。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好鬼。
近日,草灵的妈妈对家里的食品开始了担忧。前天她烀好的一锅饼子,放在挂在墙上的柳条篓子里,今天她熥饭时,咦!怎么就剩了一个了。而她记得非常清楚,还有两个呢。她问在烧火的闺女:这饼子咋就少了一个呢?草灵低着头说:我哪里会知道?妈妈问儿子:“小海,你吃了一个饼子吗?”小海回答得更干脆:“没有。我两天没搬零食了”。妈妈自言自语地说:“大慨我记错了。”晚上妈妈又烀了一锅菜饼子。因这菜饼子中间夹着馅,这馅是花生面和白菜搅和的,很是可口。剩下的,妈妈又放在柳条篓子里,在做饭时,都要进行数目的检阅以保证数目的准确和贷源的充足,不让它断了流。这个早上,她熥饭时,她的手在篓子里摸了半天,就摸到了一个,还是一个瘪的。她明明记得是三个,咋就仅有一个呢。她咋呼起来:“谁夜里又吃了两个菜饼子,赶快坦白。”没有人应和。她又问草灵:“怪了,昨夜里咋又少了两个?”草灵的头让锅头给挡住了:“我不知道。或许是你记错了吧。”妈妈说:“记错了?我又没到七老八十,老眼昏花的时候,咋会记错呢?”妈妈的脸一转:“小海,你是不是又吃菜饼了?”小海反驳:“妈妈,你咋就知道赖我呢。我睡觉能吃饼吗?”妈妈的眼睛眨巴了一气:“是啊,那这饼叫谁吃了?”小海嘻嘻一笑胡诌道:“说不定叫鬼吃了呢。”妈妈一愣:“说不准,鬼什么时候进来的?”
难道从窗缝里拱进来?
夜里睡觉前,女人对男人说:“秋天忙活活的,家里也开始闹鬼了。”
男人说:“听说这鬼是好鬼。专门帮穷人惩恶人。北头的武奶奶的房顶塌了,要不是鬼发现了。她早已死了。还有……”
“你说的我都知道。可这些日子,这鬼总爱上咱家来转转。我怕……”
“咱家不也是没丢东西吗。可见这鬼也不为难咱家。何况,咱家从上辈开始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吗。”
“话是这样说。可要是半夜起来到厕所,一出门一抬头,一个黑发黑毛的小鬼挡在你的前面,两眼放光,呲牙咧嘴,不把人吓得屎拉裤筒才怪呢。”
“你说得太吓人了。”
“铁锨我拿进来了。今夜换班睡觉,要是这小鬼再来花生垛前吃花生,你就拍它一铁锨。”
“拉倒吧。男人边脱衣裳边说:我明天还要赶着毛驴去驮谷子呢。”
“哎,怪啦,你这人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是吧?”女人圈起一条大腿,向外一蹬,男人像一袋粮食跌在了炕旮旯里:“我的缰绳松一松,你就开始尥蹶子。出去,到院子里去睡!”
这沉重的咕咚声响,把殷孩子惊醒了。小海的头从另一头探出被窝,睁着惺松的眼睛问:“爸,你咋掉炕旮旯里了?”
女人立马说:“你看你看,你咋这么不小心呢?毛里毛燥的。掉下去了吧。”
儿子又躺下睡了。老婆逼道:“想通了?”
男人点了点头。
女人柔声说:“这还差不多。上来压压我吧。趁小鬼还没来。”
下弦月还抖足精神地贴在灰蓝的苍天上,院子里隐上来一大块的黑影子。外面街上的一棵高高的杨树上,叶子密的就是一堆挑在半空的黑色棉花垛。一只大的鬼勾鸟鸟怯怯地叫了三两声,又怯怯地飞去了。草灵家的墙头上凸出了一个黑黢黢的怪物。向着窗户偷窥。女人的眼尖,一只手胡乱地捅了捅还在打鼾的男人:话语变声变调的;“鬼来了……来鬼了……快……”
男人在黑暗中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地用两条腿往裤筒里硬伸,嘴里还不闲着:“这个鬼呀,真是的,为什么就那么看好我家呢。使我捞不着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