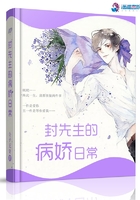异地小城,每一处画面都像一滴泪,聚焦起来,变成伤感的海洋。
一路行走,却让人感受生命的气息,触碰到生活里的一度温暖。
第二天早上夏欢喜是被窗外的鸟叫声唤醒的,阳光斑驳的透过落地玻璃窗照进来,缓缓睁开眼睛。空气氤氲着尘埃的光,有一种混沌感。玻璃门大概是昨晚在阳台回来的时候忘记关紧,开了一小溜,新鲜的空气伴随着植物的味道迅速串满全身。我爬起来走到阳台,被雨后的石狮美景深深的震撼了。
而夏欢喜的伤风感冒竟然破天荒的好了,收拾好的心情,准备认真走走这座宝盖山。
石狮这座三十万人口的小城,来自菲律宾、新加波、越南等地的华眷就占据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和台湾隔海相望,有着悠久的地缘血缘关系。据说石狮市的台胞就有三十多万人,居住在台湾的同胞有二三百人。浅浅的海湾阻隔了亲人们的相聚,却斩不断深深的思念。《泉州府志》有记载“关锁水口镇塔也,高出云表,登之可望商舶往来。”可见它是一个航标,是远行人们的一个指路的灯塔,照亮了他们回家的路,而远航的家属们也会来这里等候他们的归来。而在人群中走散彼此的人们,会不约而同的来这里等待彼此。
有人说,所有等候的人都会去姑嫂塔,所以寻人的人也会去那里,很多失散了多年的爱人、亲人、朋友都在那里重聚,而夏欢喜,带着一段清晰的记忆去姑嫂塔,在那里能找到她的小北吗,那个心里只有夏欢喜的小北。
因为今天不是周末节假,来这里的人不多,一路往上走,不高。夏欢喜却被一路的黄色小花朵吸引,驻足在路中间,呆望着它们。
“姑娘,这叫相思树,这刚好是它开花的季节。”从夏欢喜身后传来一串声音。她转过身去,只见后面站着一位老太太,佝偻着背,拄着拐杖。
“老奶奶,你好像很熟悉这里。”
“老婆子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了,我是看着它们长大的呢。虽说这相思树是闽南一带极为常见的乔木,却寄托着我们许许多多人的守候和思念啊。它春天长出眉一般的绿叶,夏季开出带茸毛的小黄花,结成细长的豆荚,到深秋,便把红褐色的相思籽撒落一地。”老太太一边往上走,一边介绍。
“奶奶,你是在等人?”职业病总是驱使夏欢喜去对各种人事做猜测,并且总有一种刨根问底的好奇心。对于她突然冒出来的这句话,这位老太太似乎很惊讶,透过老奶奶眼中散发出执着而力的目光,能让人感到她年少时候那种不寻常的际遇。
“姑娘,不瞒你说。我是在等人。那年我十九岁,老头子就跟着国民党的部队四处打战,临走前我们约好,如果失散了就每月的十五号在姑嫂塔下等。后来听说国民党打输了,迁去了台湾,可是我一直相信他会回来的,一等就是七十年,住的地方都换了好几次了,老头子再回来也认不得了,我一定要在这里等他。”
夏欢喜突然想起爷爷奶奶那一代的爱情,你翻一座山,我越过一条河,二人见了面。男的不秃不瘸,女的不懒不馋便在一起了。物质匮乏,愿望简单,可是一见面就是一辈子的执着与坚持,而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的爱情从滋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这个时代赋予了压力和特点,计代价算得失,四周充满了诱惑,爱情是自由了,却比从前脆弱得多。
赵小北,一直认定了就是我夏欢喜这辈子正确的人了,可是事实证明他就是错误的,可既然是错误的,为什么回忆总是分分钟都要窜出来轻而易举的就把那些细节抽丝剥茧般在我心头放映一遍一遍。夏欢喜心里想着,而现在,她只能一个人把这场苦情大戏的后半场演下去。
“奶奶,你每月都来吗?”夏欢喜扶起老太太,聊了起来。
“是啊,七十年了,风雨无阻,只是有一次病发去了医院没有来。对了,小姑娘,怎么称呼你?是来这旅游的?”
“我叫夏欢喜,来这里打算小住一段日子。”我简单的一语带过,老太太还想问点什么,突然呼吸急促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喘息有些困难。“我……我有心脏病,药……药,在……在袋子里。”老太太艰难的吐出这一字一句。夏欢喜赶紧从老太太的口袋掏出一瓶白色小药瓶,掏出一颗给她服下。顺手从包里掏出一瓶水,给老太太送药。
“老奶奶,我送你去医院。”老太太的情绪开始一点点平静,呼吸也开始放缓。“欢喜,谢谢你,老毛病了,没事的,我还要去等老头子呢。”
“您这样的情况,今天别去了,你看上面也没人,我送你回去,要是身体垮了还怎么等。”我劝道。“哎,人老了,你说的也是,万一我出事了,怎么等老爷子回来。”老太太似乎对夏欢喜的话很听从,并且很乐意接受她的帮助。
送老太太回家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她一个人住,孩子们都在厦门,很有出息。据说后来也帮老太太去台湾找了很多次,始终没有音讯。十年尚且不好找,何况已经过了几十年了。
夏欢喜帮老太太做了几道家常菜,她想这些真的要感谢赵小北,和他在一起这么多年持家的本领真的是分分钟都在增加。能烧得一手好菜只是因为小北说过“欢喜,你烧一辈子的菜,我就帮你洗一辈子碗。”说的多动听啊,赵小北,我还在烧菜,你也还在洗碗吧,只是不是帮我洗了而已。如果此刻这样的画面他也在的话,怕是他最想做的就是拿一块记忆的橡皮擦,把那些他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一字不落的从我脑袋里抹掉吧,包括他曾在我生命中出现过这件事。
“欢喜,你真是好姑娘,从看到你那时候起,就感觉你特别像我年轻的时候。”老太太开始打开话匣子。夏欢喜也从回忆里出来,顿了顿神:“奶奶,这是我们的缘分呢。快来吃饭吧,可以吃了。”
“欢喜,真看不出来,你的厨艺真不错。”几道家常菜让这位多年守候的孤独老人感觉到家的温暖。
“奶奶,你要是喜欢,我经常来烧菜给你吃。”
“好好,你来,奶奶高兴。就怕你嫌我老人家烦。”
“怎么会呢,奶奶,我很喜欢你。你是我在这里的第一个亲人。”
老太太抬头看着我,似乎眼里泛光。老人们总是容易感动,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小小的动作,都会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欣慰。她突然抓住夏欢喜的手,“欢喜,要是没别的事,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奶奶给你讲故事。”
那天晚上,奶奶和我讲了姑嫂塔的故事。
从前,宝盖山下居住着一对穷夫妻还有一个小妹妹,一家三人,生活困苦。俗话说:“盐水也有口渴的人喝。”大兄只好离别年轻的妻子和妹妹,孤身一人,往南洋谋生去了。
大兄去了南洋,几年没有回家,也没有寄来一枚钱一封信。他到底是死是活,是好是歹,真叫姑嫂两人牵肠挂肚,日夜思念。他俩经常登上宝盖山顶,对着大海看啊看,可是每次却只能看到一个灰蒙蒙的大海,哪有大兄的归帆呵?为了能看得很远很远的大海,她们一次又一次的扛来石头,堆迭起来,年久月深,成为一个高高的站台。她们站在石台上,踮起脚尖,不停地看啊盼啊,可是一月过了又一月,一年过了又一年,大兄还是没有回来。
有一天,姑嫂俩看到孩子们在放风筝,她俩心想,我们写封家信,把它绑在风筝上,让它随风飘到南洋去吧。可是放风筝,得有风筝绳索呵。她俩就剪下自己长长的头发搓成风筝的绳子。这系上家信的风筝,就这样飘起来了。那头发编织的风筝,绳子也越接越长,突然一阵大风,绳子被吹断了。那风筝飘在南洋上空落下来了,系在风筝上的家信被番客们捡到了。这信终于传到大兄的手里了。
原来大兄到了南洋后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利路。他落泊在外,没什么好消息可告慰妻妹,连家信也懒得写了。如今,他读着姑嫂俩这血泪写成的家信,悲痛得大哭起来,就急急忙忙收拾行装,赶回唐山,以安慰亲人的思念。
这日,天气晴朗,姑嫂两人又登上宝盖上顶的站台,对海眺望。一会儿,只见她俩眼睛放亮,兴高采烈喊着:“啊!来了!真的来了!”大兄正驶着小船回来了,亲人相聚就在眼前了。可是,就在这一霎那间,狂风大作,海浪滔天,一个浪头打了下来,小船翻沉海底了。姑嫂眼睁睁看着即将相会的夫、兄顷刻间又葬身大海,呼夭抢地的惨哭几声,也相抱跳崖自尽了。
后来,乡亲们为纪念这对姑嫂,就在她俩迭石堆台的地方,建筑了这座石塔,叫姑嫂塔。塔里还雕着姑嫂的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