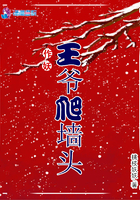山上传来敲钟的声音,连绵不断,厚重而悠长,仿佛在叙说着这座百年学府背后的故事。兴许曾历经数次风雨,也曾誉满天下,可最终皆归于平静。
安然地处在深山古林之间,培养一代代兴邦治国,念及苍生的学子。
随后,便可听到从院子里传来的欢歌笑语——这是学子们课间歇息的时间。
沈昭被钟声惊醒,仔细看了看那盘烂柯图,又看着宋衍凝眉沉思的模样。蓦然发现,这个人早已不再世间。她到底没有再露出怨恨的神情来。
大楚已灭,曾经的将军府亦已消失在历史长河。甚至,宋家的后人身处何处她都不知晓,沈家的后人也未必记着这一段仇,她又何必再心怀怨念?
豫东学府的山门并不如何雄伟,可自有一股古朴厚重之感,哪怕历经风雨,亦不减丝毫风采。只是单纯地看一眼,便让人心生敬畏。
这是世人对学府生出的由衷敬仰。
山门之上,写着几个苍劲有力地大字——豫东学府。而山门两边的石柱上则刻着八个大字——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简单的八个字,却概括了豫东学府教书育人的基本原则。
天地同卑,山泽齐平。其意在世无高低亦无贵贱。
豫东学府教书育人,从不看出身之高低贵贱,只看他本人是否有学习之心,上进之心。因此,豫东学府招收的学子多出身寒门,最终亦学有所得,福泽一方。
兴许这便是豫东学府屹立百年而不倒,且闻名于世受众人敬仰的原因。不愧是能与国子监齐平的学府。沈昭瞧着,忍不住在心里感慨一番。继而领着罗会拾阶而上。
傅礼九早已收到他们前来拜会的消息,因此沈昭刚同学府的守卫说明情况,对方便带着她前往傅礼九所在的鹤鸣居。
鹤鸣居位于学府后边,从前院过去,要穿过数间庭院才行。其间沈昭虽是匆匆而过,却仍可感受到学子们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意气风发。这才是少年郎该有的模样!
傅礼九喜静,因此鹤鸣居里学子习书的庭院较远,便是学府的守卫亦不敢上前过多打扰。只将沈昭送到院子外头,便自请离去。
沈昭无奈,只好亲自上前敲门。才几息的时间,木门便被打开,发出吱呀的声音,并不让人觉得刺耳,反而多了几分人烟味,而不似之前一般冷清。
开门的是一个青衣小童,年纪不大,才八九岁的模样,梳着小髻,但举止言谈间透着矜持,他面露微笑,温和有礼地问道:“请问可是余公子?”
“正是少明。”沈昭亦朝他微笑颔首,“不知老先生可在?”
“余公子,请随我来。”
青衣小童虚手一指,示意她请进,沈昭便跟着跨门而入。相对于院落外的冷清,院落内就显得热闹许多。
角落里肆意生长着各种花草,却非文人墨客喜欢的梅兰竹菊等,只是叫不出名字的野花。高大的银杏树长得郁郁葱葱,投下一大片绿意。三三两两的麻雀立在枝头,不知停歇地叫着,
甚至还有一只毛色褐黄的猴子——卧在庭院里,见有陌生人过来,便如一道流光,飞快地跳到树上,眼睛却滴溜溜地转个不停。
沈昭忍不住呆滞了一瞬,倒不是未曾见过猴子,只是不想傅老先生竟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在院子里养一只猴子。在她印象里,大儒名士或者隐者雅士并不养小动物,便是有更多地也是养鹤。
而非这样一只猴子。这傅老先生倒与她印象里十分不同。
她将周围的景致匆匆扫过,把罗会留在外边,自己则跟着青衣小童一同进了一旁的房间——是傅老先生的书房无疑。
小童刚撩起竹帘,她便透过缝隙看到一个眉发花白的老者盘腿坐于窗边案几之后,穿着一件灰色道袍,头顶绾着髻,随意插着一根木簪。案几上点着的沉香木升起寥寥青烟,更显得他面容清癯,眼眸深邃。
青衣小童向他行礼,沈昭也紧跟着,双手作揖,弯腰行礼。
“学生余怀昭见过老先生。”
傅礼九微微抬眼,青衣小童便领悟其意,当即退下。沈昭则站在原地,不敢有半分动作。对方的眼神透过淡淡的烟雾,落在她身上,虽然十分温和,可温和之中又隐藏着一股不容忽视的压迫。
“你便是子谦向老夫引荐的后生?”
“正是学生。”沈昭微微颔首,又从袖中取出一封书信,双手托着呈上,“这是苏公子亲笔书写,还望先生亲启一观。”
傅礼九早就料到有此一封书信,便示意她上前几步,从她手上取走书信。不紧不慢地拆开,无外乎是此人的身份来历,引荐缘由以及恳请他收下此人云云。
他随意扫了一眼,又忍不住细细打量起沈昭来。他的学生性情如何,他自然是清楚的。看似温和有礼,恭谨谦逊,实则寡情薄意,拒人于外。实在不知眼前的后生如何让他那性情淡漠的学生花这样的心思。
他思量片刻,便淡淡地道:“老夫这一生虽传经布道,门生众多,但真正传其衣钵的弟子却只有两个,你可知晓?”
此事沈昭确有耳闻,只是具体是何人却并不清楚。听说皆是才学出众,出身不俗之人,只是为避免世人过多打探,便隐姓埋名求学于傅老先生。
“学生早有耳闻。”沈昭再次向傅礼九躬身行礼,神色凝重,眼中尽是诚恳之意,“学生今日前来只望先生能允学生待在豫东学府读书,不敢多求他事。”
傅礼九闻言,顿时面露讶异之色。这后生所言显然是不欲拜他为师,真正成为他门下弟子。
“此言何意?”
沈昭复又行礼,神色真挚,言词恳切,“学生曾拜于他人门下,一日为师终生为师,故此后学生不能再拜他人为师,还望先生谅解。”
这意思便是只做其门生,听经闻道,却不传其衣钵。沈昭此举其实有利用傅礼九身份之便的嫌疑。对人而言亦称不上尊敬。
因此,尽管她面上看着镇静,心里却不免有忐忑。她这般行为于情义方面虽过得去,于情理而言却有些过分。性情豁达些兴许不会多言,可换成别人,只怕当场就会沉下脸。说到底,对方还是德高望重的前辈。
傅礼九倒没有因此而生出不悦,只是打量她半晌,最终露出淡淡的笑容来,眼底闪过赞赏之色,“是为忠义之辈,难能可贵。”
“先生过誉。”沈昭抬手行礼。
傅礼九觉得这个后生很是谦逊,国朝现存的大儒名士,他谈不上最好,却也不差,多少学子慕名而来,欲拜在他门下。而眼前的晚生却将他拒之门外,不论他之前的先生为何人,都是极为难得的事。
他的学生到底是懂得分寸的,并未引荐不堪入目之辈。品性出众,却不知才学方面能否入眼?若是胸无点墨之辈,也难免叫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