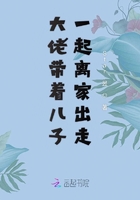那是永明三年的初春,他五叔刚刚升任潮州府同知,老太君请了戏台子唱戏,与孟家有来往的人都来祝贺了,自然也包括与他五叔交好的沈家。
他早就知道孟家族学的沈先生有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儿,但是从未见过,他只跟她的兄长沈清远有过几面之缘,还是在他六弟的引荐下认识的。
他六弟是五叔的嫡长子,跟沈家也是相熟的。
那一日,他按照祖母的吩咐去听雨阁把他的那些弟弟给喊回来,听雨阁毗邻荟蔚园,园子里坐的都是各家的姑娘,他们这么冒冒失失地待在听雨阁难免会冲撞。
从正院出来,过中庭后,就会有两条青石小道,一条通往听雨阁,一条通往荟蔚园。
他刚走到岔路口就小道旁边的小花园里传来姑娘说话的声音,听上去年纪不大,应该是哪家的女眷吧。他想。正打算离开,又听到有人说话了,声音有点气急败坏,这次应该是丫鬟。
不知怎么的,本该去听雨阁的他居然走到了另一条小道上,他只是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人把自己的丫鬟气成这样。
他绕过青石道旁高高低低的冬青树,走到园子里才看有两个小姑娘站在那里。
小的那个才六七岁的样子,穿着白底绣五瓣梅纹的短袄,素白澜裙,头上扎了小小的髻,绑了两朵粉白的珠花,可能因为年纪小的缘故,脸上还有点婴儿肥,更显得粉雕玉琢。
她此刻正站在一块作为景致的怪石上,伸手去勾墙边的一枝雪白的杏花,那是从荟蔚园里伸出来的。
下边站着一个作丫鬟打扮的姑娘,年纪要大些,一脸焦急地喊着,让她下来。
她却不管不顾,一边踮着脚去勾花枝,一边扭头笑嘻嘻地跟丫鬟说话,一点都不怕的样子。
他看着都有着急,那怪石凹凸不平的,虽然不算高,可底下还有许多碎石,真要摔下来是很危险的。
他正胡乱想着,也不知是不是他乌鸦嘴,那小姑娘哎呦一声,好像真摔下来了。
他一惊,正想上前去看看,却见小姑娘没事人似的站起来。
还朝她的小丫鬟笑,我骗你的,这么矮的地方,我怎么可能摔着。你真是太好骗了。
他伸出去的脚又收了回来,心想这小姑娘胆子真的很大啊。这个时候恰好他身边的小厮找过来了,他只好转身离开,心里却想着他还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姑娘呢。
后来在永明五年的时候,他准备参加秋闱了,听说族学的沈先生是太康年间的探花郎,就想去请教制艺。
他正待在沈先生的书房读书,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只圆滚滚的猫跳到沈先生的书案,不仅打翻了笔架,还踩了石砚,又在沈先生的画作上印了许多脚印。
紧跟着又跑进一个小丫头,哭丧着脸喊,“姑娘,朽木又踩坏了老爷的画。”一边说着又一边去捉那个猫。
后面就传来一道笑嘻嘻的声音,“真是朽木不可雕也,看到父亲的画作也不知道避开。罚你去跳大绳。”
那个小丫鬟就喊,“明明朽木的错,为什么要罚婢子!”
他十分惊讶,谁家的猫还叫朽木这种名字啊。
然后就看到一个面容精致的小姑娘走了进来,才发现原来是他在两年前看到的那个小姑娘。
她长大了些,脸上的婴儿肥已经没了,不过还是一样的好看。原来她就是沈先生的小女儿,他心想,果然长得跟娃娃似的。
这个时候主仆俩终于发现书房还有个陌生人。
不过那个小姑娘好像猜到了他的身份似的,一点都不惊讶,倒是她身边的小丫鬟满脸警惕。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去向沈先生请教制艺,可惜却再也没有见过她,只能偶尔听到她的笑声从后院传来。
身边的小厮提醒了一声,他才回过神来,正看到沈昭在一盏六扇雕花镂空走马灯前犹疑不止,仰头跟沈行书说了几句话,也不知是说了什么,总之片刻后就转身离去,那花灯也没要了。
见此,他忍不住对着身边的小厮低声吩咐了一番。
小厮小跑过去买下了花灯,又追上沈行书他们,将花灯递过去。他不知道小厮是不是按照他的话说的,总之沈昭没有伸手,是沈行书接过的。
不过,他好像看到她抬了头,隔着层层帷帽,交织不断的人群,他根本看不到她的表情,但能感觉到她的视线落在他身上。
于是,脸上的笑容就更温柔了。
直到她的身影隐入人群中再也见不着了,他才转身上楼。
一进雅间,就看到季槐半卧在软榻上朝他笑得意味深长,“孟兄,沈行书那女儿闺名为何?”
孟湛听闻,忍不住皱眉,“你问这些做甚?她一个姑娘家,要是让别人知道了闺名,岂不是有损闺誉?”
季槐闻言就笑了起来,“问一下都不可以。怎么,怕我跟你抢人啊?你方才吩咐小厮做的事,我们可都看到了。”
孟湛一愣,反应过来才发现苏修允也是笑容满面地看着他,带着几分打趣的意味。
他有点恼怒,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还不是你说话没有分寸,惹人家生气了,我自然要赔礼道歉的。”
季槐见他欲盖弥彰的模样,便忍不住笑得更欢了,认识孟湛这么久,他还真是头一次见他这个样子。
之前在京都的时候,那么多名门闺秀对他暗送秋波,他都不假辞色。偶尔去茶楼画舫听听曲,他也是孤身一人,从不让人伺候,干净得跟个和尚似的,原以为是不解风情,却不想心里早就藏了个人了。
还是这般明艳的美人,就是年纪小了点,也太聪明了点。
“这沈行书倒真是养了个好女儿。”季槐意味不明地笑了笑,又道,“不过沈姑娘这口齿也是真的伶俐,对我父亲和舅爷爷的事也是张口就来,平日里怕是读了不少书吧。”
说到这,他停顿了一下,“不过,女子无才便是德,知道太多总归不好。”
孟湛不太喜欢季槐这么说话,这会给他一种季槐觊觎他喜欢的姑娘的感觉,而且他这些肆意评论的话也确实不好听。
孟湛不咸不淡地道:“沈先生满腹经纶,沈姑娘自然也弱不到哪儿去。庭植,我怎么觉得你有点针对沈先生。”
“谈不上针对不针对。”季槐淡淡的笑了笑,“就是想看看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人家念叨的。不过说起来,他真的甘心在这种地方待一辈子啊。”
孟湛觉得季槐这句话有点讨打的嫌疑,当年那些事虽然都被压下了,但像他们这些有自己的消息渠道的,哪能不知道一点事。
沈行书今天会待在岭南究竟是为什么,季槐心里能没点数吗?还要这么直接说出来。而且这话也说得跟沈行书想要欺君罔上一样。
苏修允就在一旁轻声说道:“这是今上的旨意,沈先生自然是心甘情愿的。”
季槐便哼了一声,这话他可不信。“寻常的姑娘能对朝中大臣的事知道得这么清楚?这难道不是耳濡目染的结果吗?”
孟湛闻言,不由得皱起眉,“庭植,这事应该是你多虑了。何况现在的余家已经被彻底压下去了,单靠沈先生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季槐便不再说话,他当然也知道单靠沈行书成不了气候,不过这么一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