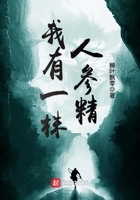微风轻扬,暖存的气息暧暧缱绻,物是人非,天地间仍是一片大好春光。斜阳普照,映不尽心愁寸断,鸟语依依,诉不满百转回肠。
天气晴好,蓝天澄净云丝绵连,灿烂的日光洒满大地,平等的温暖着世间万物,不多谁一分,不少谁半点。风吹林动,生机无限的茂盛枝叶沙沙作响,就像是不安分的孩子们在吵闹嬉戏。
朱雀推开窗子,正巧有一片鲜嫩的树叶随着清风,闯进了这件起居室。他捡起树叶,回身来到床边,将叶子放到了桑的手中,然后又为桑披上了一件长衫。
桑把玩着树叶,心里甚是喜欢,然后将叶子夹进了床头的一本书里。
托协看着一旁桌案上一朵折得活灵活现的纸百合,淡然露笑道:“桑,身体好些了么?”
“不碍的,劳烦主祭大人费心了!从昨晚一直酣睡到今日晌午,身子早已恢复了大半!”桑笑着说。
“桑!对于昨晚一战,你可理得出什么头绪?”托协看住桑的双眼问道。
“大人您太高估我了,依小可看来,那只是一场缺乏准备的突袭!至于其他,小可不敢妄加揣摩!”桑说。
托协语塞了片刻,然后看着朱雀长叹一声,他起身而去,信步间打开了房门,在门外石柱林立的宽广走道间左右观望了一阵,之后,他又从新回到房里将房门关紧,回到椅子上对桑说:“有些事,本不该向你们透露,但境况危急,我想听听更多人的想法。”
桑还是一脸阳光般的笑容,对于托协的话,他没有表现出反感,却也没有表现出半分期待。
“其一,东洲即将沦陷!”托协整理着衣襟说道,然后他停顿了一下,来观察桑和朱雀的反应,没想到这两个人谁也没有露出惊讶的神色来。托协不禁想起了珍瑟和剑少那一对儿师徒来,如果今天会做是他们听到自己说东洲沦陷的话题,一定会一惊一乍的又跳又喊。
于是托协继续说道:“我教东洲枢机遇害身亡,拘尾会东洲修正下落不明,根据东洲线报和往来烽火符函获悉,我教东洲主坛神庙,在一夜间被巨大数量的妖物攻克,妖物积千累万,同时围攻主坛周边的几大分坛,使我方首尾不得相顾。不过,这种有力的战术调度还在其次。东洲妖物素来啸聚繁众,因此我教派往东洲之人,历来都是修为扎实,术力上乘之辈,但令人称奇的是,只在朝夕间,所有教众被妖物屠戮得溃不成军一败涂地,让我方毫无招架之功反手之力。如若说东洲妖物中有一两个能量强悍绝伦之属,可抗衡我教精绝术法,这也情有可原,但如此之枭首巨魔,我教也定然会掌控其归属,洞察其异动,绝不至于被其类猝然来犯却毫无防备。怪就怪在这些肆虐的大小妖物,似乎不畏符道术法,符道乃是我教驱妖诛魔安身立命之法,遭此大变直教人悚然惶恐!”
朱雀对着托协落落间一个颔首,“主祭大人,昨日我等与那妖物接站时,已经亡故的白虎大祭司在仓促间对我讲了些许那妖物的情报,此妖物自称十芽风角,言语缠夹不清颠三倒四,心机智慧也是劣于其辈,但战力之强却是有目共睹。白虎大人曾说,此妖不时间常将一枚石果吞吐口中,便可干扰符术结成,却并非是将符道术力完全屏蔽,有型有质之符兽符偶接触其身,则尽皆溃散,光火雷电却能浅伤其体。依属下看来,想那干扰符术结成的石果,大概产于东洲,从未被世人所查!”
“石果?”托协拧起眉头,“白虎首席可说清了那石果是何种形貌!”
“浑圆无蒂,质如石土,近乎相类于蕃茄,形态略小,正可含置于口中!”朱雀想了想说。
“罢了!”托协拍着拳头间长叹道,“那是大屘灌,其产地并非东洲,而是中洲。大屘灌之红艳果实,若经非自然脱落采撷,便可化身僵石质地,鼓含邪气津唾,便可结成出扰符力场。前不久便曾听闻白虎代理枢机说过,悍角分身曾幻以撷电首席皮相,来殿顶宫阙纠缠。枢机大人称其是来窃此奇株而为,我当时还未放在心上,现在想来,大屘灌其功其理早已被芽兽知晓,觊觎之心已不在少日间!”
朱雀的脸色一变,他只知道,殿顶宫阙中栽种的大屘灌配以一些奇花异草,便能形成禁符领域,却从未听过还有这种新奇的使用方法和厉害的功用,这样看来,裹角部和拘尾会中的所有修术祭司,等于是没有了利爪和牙齿的老虎。“不过!既然不能完全屏蔽符术聚合,然则东洲陷落竟如此之快,却又不知是哪般缘由!既然光火雷电可伤其身体肌肤,东洲部众又为何没有自保之力?”朱雀不解的问道。纵使还击的力量再过微弱,但真的连逃脱也做不到吗?
托协正想着苦笑作答,却留意到了一直看似漫不经心的桑。桑一直在笑望着窗外出神,最近桑好像经常会陷入这种状态。托协清咳一声道:“桑,对此一说,你又有何种见解?”
桑缓过了神,谦笑着轻轻晃头,表示刚刚自己确实没有用心听他们两人的对话。
“白虎首席曾说,符术可粗伤含置石果之妖,若依此为推断,同样含食此种石果的东洲妖党,却为何又能对我符道众所向披靡横扫无忌。”托协定定的望着桑的脸重复说道。
桑侧头想了想,然后开口说:“殉职的白虎大人虽年纪轻微,但其修为之高,业术领悟之强,实为天下符道部众之翘楚良材,裹角部教众虽居广众,但又能找得出几人及得上她?以此看来,连白虎大人都只能做到粗伤妖体,那么其他人对妖物可造成的伤害,也就更加微乎其微了。试想一下,我教中祭司临战初遇这种平生仅见的扰术能力,心慌意乱的绝望之心自不待言。兵法有云,临战对敌,攻敌之心远甚攻敌之身,心意乱则气势竭,气势尽则战无力,攻之不成,守之不御。妖党发难猝然,却调度得法,兼有扰符之力,又有破竹之势,我方守备不溃则已,若溃,则必将一溃千里!”
托协苦着脸点了点头,朱雀也是连连称是。
“正如桑之所言,东洲之变,实在令人措手不及!而且,生变的不止是东洲。据砒蔴首席发函来报,近日前,南洲铿跌教在大兴筹备一个古怪仪式,欲以六百笙箫琴艺绝佳少年男女为牺牲,献祭于一位神明使者,此教中人广泛宣扬天下将倾,唯有屏退其他,投身此教方得保全,南洲遍布夜行人行伍杀伐肆虐,举洲陆土人人自危,皆与此教有所关联!”托协又是一声叹息,接着说道,“还有西洲,西土镇洲枢机骼烨?鄋畈大人疯了!西域沙匪番邦结成联军,欲将裹角部与拘尾会所有势力连根拔起,匪性难驯,绝不容我教中人晓以大义,妖邪作乱萌动繁复,天下兴亡危在旦夕,其辈尽皆笑称之曰危言耸听!”
“那么,是否连北洲也有所异动?”看着托协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朱雀淡淡的问了一句。朱雀大致看明白了,托协似乎在与其他高层商议这些事的时候,意见难以统一,实在把他憋得没办法,才来这里吐吐心事,但他又毕竟是掌管绝密的执教主祭,绝不会把所有事情全都说个分明。现在他就像是一管牙膏,挤一点儿才会说一点儿,实在挤不出来的时候,那一定就是事关绝对机密了。
“北洲没有妖祸,却贫发天灾,不是高地突起雪崩,就是冰峰喷发浆火,人员伤亡倒还不多,却毁去了不少分坛神庙!如果说这是妖物所谓未免牵强,因为由此谁也落不得任何好处!”托协说。
“也不是没有好处!”桑突然说,“如果加上昨晚的风角突袭,我只能联想到一个词来形容当今的局势!天下大乱!”
托协牙疼一般的托起了腮,天下大乱,似乎他早已心知肚明,但就这么被人直接说出来,他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东洲有妖,南洲有变,西洲有乱,北洲有患。裹角部、拘尾会通同天下,却又能同时兼顾得了几方?如果这些尽数是芽兽所为,对他们而言,如此这般无外乎只有三种可能,一,他们尚有惧怕两大宗室的地方,可能正是我们神星将,但也更可能不是,他们需要准备时间作为缓冲期,四处起乱正便于他们浑水摸鱼;二,他们在为复活冥伶做准备,现在可能是还缺少某种道具,或者是还缺少掌握着某种技术的人类或妖类,大概因为索取尴尬而又极其易毁,他们便利用这种方式来扰乱人们的视线;三,他们的大事早已完成,完全出于猫戏老鼠之心来蹂躏天下,奔波筹备了几千年,当然需要一些畅快淋漓的举动来庆贺成功了!”桑在说话间悄然的拿起纸笔来,信手涂鸦。
托协换手托起另一侧的脸来,似乎这次他是真的上火了,本来他就是想让桑来分析一下昨晚一战中,敌方的战略意图,没想到桑却简简单单说出了惊心动魄的“三大可能”,尤其是那听上去就令人绝望的第三种可能,真是让托协听着就牙疼。托协的嘴里已经没有几颗好牙了,但一上起火来就疼得邪乎。
桑在几笔间就勾勒出了一幅炭笔画的轮廓大概,画的是剑少搂着珍瑟的样子。画笔极其传神,将两个人那种凄然的笑容刻画的无尽唯美。
“主祭大人!”桑继续画着素描对托协说,“我心中有个问题实在压抑得紧,您今天来看我,是否能给我一个答复!”
朱雀极为不自然的咳了两声,然后在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向窗边,“气也通得差不多了,虽已是晚春时节,窗子开得久了,却也还是有凉风伤人!”朱雀说着,抬手关上了窗子。
托协赧然一笑,他没想到自己也会有被手下大祭司提点的一天。“尽管问来,若是别个星将,我定然会慎言慎行,至于你,我没必要说些谎话来诓骗。依照你的心智,即便我三缄其口,你也定然能推断出个八九分来,如此一说,却还不如爽快作答,咱们两厢磊落!”
托协表现得这么坦诚,反倒让桑觉得有些意外。桑也认为,主祭中还是川胁比较好说话,但也正是因为他为人随和,处事待人未免会欠缺果断,所以他应该不会掌握着所有至关重要的绝密掌故。
桑横扫着手中炭笔,描绘着珍瑟那只破败的岩土右臂。“我们所有神星将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桑说。
托协被问了个措手不及,几度想开口作答,却又似乎找不到贴切的语句来说明。他萎靡着脊背,淡淡的说:“你们是诛妖利器!”
桑悠然发笑,脸上的两条法令纹勾画出一个几近完美的弧线。“为什么将亡故的白虎大人用琉璃冰岩封在了总坛内?我看过裹角部的宗室典籍,殉教往生的教会人员,历来都是送与其家中待葬,宗室这么做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就是害怕剑少受到损伤!把白虎大人放在哪里,剑少就会守在哪里,如果将白虎大人送回家中,其父一定会与剑少作难,虽不至于伤其性命残其肢体,但以剑少那种心口不服的性格,一定会大问其父诸般缘由。两厢激蛮之下,一些不足予外人道的秘闻便会得以大白。”
托协寡淡的笑笑,桑这么说,好像是他背着所有人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一样。
“守护祭司,与所属星将之间,应该有着什么比较鲜见的相互牵连的术法吧?”桑仍是头也不抬的细心作画。
朱雀默默的闭上了双眼。
“白虎?冠澜先生在白虎大祭司那次中毒时,曾竟提起过,做守护祭司是换命的勾当。而且今日我也听叔宝兄说了昨晚在我晕倒之后的一些事,水主大人也曾失口说出,是剑少害死了白虎大祭司的话语,而且白虎大祭司所中的致命创伤,也和剑少的伤势如出一辙,但她却因此而香消玉殒,剑少却没有什么损伤。我便做出了个假想,是不是当我也遭受了致命伤害时,替我死去的人却是我的导师朱雀大人?”桑在画着剑少与珍瑟两人合手捻着的那枚瓶盖时,炭笔的笔芯却突然应声断折。
“这先不忙说!”托协挥挥手,“你能先分析一下,我教损失了白虎首席后,对敌方有什么直接帮助么?”
桑轻松的吐了口气,不由得暗暗感激着托协,是自己太冲动了,居然把话挑的那么明朗。他换了一支炭笔继续作画,笑着说道:“先不去想此事会对敌方有什么好处,我们先来想一下,教内一夜间少了一位首席祭司,按照常理,我们都该做些什么?”
托协会心一笑,他觉得自己果然是找对了人。
“我下面的推测十分无稽,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希望大人您就当听个笑话。首席祭司出现空缺,第一时间里,我们会找一个能力相当的人来进行添补,为了公平的选拔人才,上层应该会扩大选拔范围。不出意外,会有一个平时被大家所忽略的人物一鸣惊人,登台夺冠,他实力超强,术业精湛。宗室便会开始彻查这个人的来路底细,却又发现这个人有着许多难以解释的疑点,正值用人之际,却又出现了这么个疑人,当真是形同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但是不怕,现在正是四方有乱的时机,可以把这个人随意调派远方,安插在二线岗位中平乱镇边,并且时时防备,时时监督着他的动向。为此疑人,要至少安排三个以上与其实力对等的教内资深人员,这样,就直接造成,也深深加重了我方的战力涣散。”桑说。
托协一开始还真以为桑是在说笑,但听到最后,他才明白了桑的意图,这些话当真是无稽好笑的,就像是一个无聊写手凭空杜撰的三流小说,但是,这些事真的不会发生吗?而且,桑还只是提及了这么一个可能性,点破了涣散战力这一中说法。
“桑,不可对主祭大人无礼,你究竟想说什么便要直言相奉!”朱雀阴沉着脸对桑说道。
“芽兽要让天地混乱,但是,能乱得起来的,只有人心!人心一乱,再想从新凝聚起来可就晚了。不过现在似乎还未到那种紧要关头,我们当下需要做的事,应该是权衡取舍。东、南、西、北四洲已经不可能尽数保全了,要尽快选出一个不可或缺的洲土巩固防御,与中洲呈掎角之势相互守望,有张有弛进退有度,才不至于在将来太过被动!”桑放下画好的素描说道。
托协良久无语,然后站起身来叹息连连。桑看得太远了,远得有些叫人感到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