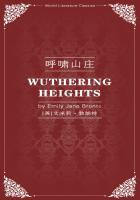“照你刚才这么说,家具里可能用来藏东西,可你们没法把这一切家具都搬开,拆开啊。比方说,一封信可以卷成细细的螺旋卷,样子,大小,跟大号编织针没什么差别,卷成这样,就可以嵌进椅子的横档里。你们没把所有的椅子都拆开吧?”
“当然没有;可我们干得还要高明——用架非常精密的显微镜,把公馆里每只椅子的横档,不消说,还有各种各样家具的接榫,都细细检查过。要是有什么最近动过的痕迹,不怕一下子查不出来。比方说,钻子钻出来的一丁点儿木屑,看出来就跟只苹果一样清楚。粘胶的地方只要有什么不对头的——接榫的地方只要有什么异样的裂缝——保险都查得出来。”
“想必你们注意过镜子,镜面和底版当中的地方,此外也总戳过床铺和被褥,以及帷帘和地毯吧。”
“那当然;我们把每件家具都这样搜遍以后,就搜屋子了。整幢屋子的表面都分成一格一格,编了号码,这样就没一处漏掉了;然后,照旧用显微镜把整幢屋子,一方寸一方寸地查个明白,连左右两幢紧挨着的房子也仔细查过。”
“左右两幢房子!”我失声喊道,“你们一定花了不少工夫吧。”
“是啊;可这笔报酬实在不小呢。”
“你们把房子四周的地面也查过了吗?”
“地面全是砖头铺的。这倒不费什么力气。我们查了查砖缝间的青苔,看出没挪动过。”
“你们当然也查过德××的文件,还有他书房里的书本喽?”
“那还用说,大包小包都打开过;不但把本本书都打开了,还把每一部书都逐页翻过,我们可不学有些警官的样,光拿书抖抖就算了。我们还用非常精确的测量仪器,量了量每本书封面的厚薄,而且还用显微镜仔细万分地照过。有哪本书的装帧新近拆动过,都绝对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有五六部新装订的书,我们全拿针在直里仔细戳过。”
“你们查过地毯下面的地板吗?”
“那当然。每块地毯都搬开过,还拿显微镜检查了地板。”
“那么墙纸呢?”
“看过了。”
“查过地窖吗?”
“查过了。”
“那么,”我道,“你搞错了,那封信并不像你假定的那样在屋里。”
“你这话恐怕说对了,”警察厅长道,“呃,杜宾,你倒说说看,我该怎么办?”
“把屋子重新彻底搜查一遍。”
“那倒大可不必,”葛××答道,“我可以拿脑袋打赌,那封信绝对不在公馆里。”
“那我没什么更好的建议了,”杜宾道,“你一定知道这封信的详细样子吧?”
“可不!”——说着,警察厅长就掏出一本备忘录,宣读那份失落的文件里面的详细样子,尤其是这封信的外表,他讲得特别详细。他详细念完这篇说明,就告辞了,神态沮丧,我可从没见过这位一向愉快的先生这么沮丧的。
过了一个月光景,他又来看我们,只见我们差不多还跟上回一样待着。他拿了支烟斗,坐了下来,谈了些家常。最后我说道:
“啊,葛××,那封丢失的信怎么样啦?想必你终于认定斗不过那位部长了吧?”
“哎呀,去他的,我按照杜宾的意思,重新调查了一遍——可就是白费力气,这我早料到了。”
“你说过这笔酬报有多少?”杜宾问道。
“嘿,这笔数目非常大——这笔酬报非常丰厚——我不愿说出到底有多少;不过我愿意说这样一句话,有谁把那封信给我找到,我不惜自己掏腰包,送他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说真的,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了;这笔酬报最近加了倍。不过,就算酬报加上三倍,我也只能这样,没别的办法了。”
“哦,是吗,”杜宾一边抽着烟,一边慢吞吞地说道,“我倒——认为,葛××,——你没完全尽到力量。我看——你还可以尽点力,呃?”
“怎么?——用什么法子?”
“哦——噗,噗——这件事吗——噗,噗——你可以向人家讨教一下,呃?噗,噗,噗。你可记得阿伯尼蒂的故事吗?”
“不;去******阿伯尼蒂。”
“好哇!尽管由你说去******阿伯尼蒂吧。不过,从前,有个阔绰的守财奴,竟想出条妙计,打算骗这个阿伯尼蒂白给他看病。存了这条心,他就在一次私人来往中,一边扯着家常,一边巧妙地把病状捏造成别人的毛病,讲给这个医生听。
“守财奴说,比方说,他的病状是如此这般;呃,大夫,你叫他找什么药吃?
“阿伯尼蒂说,找?嘿,当然是找人讨教喽。”
“可我不是甘心情愿找人讨教的吗,我不也情愿出钱吗,”警察厅长有点不安地说,“谁帮我办这事,我就真个给他五万法郎。”
“假如那样的话,”杜宾说着拉开抽屉,交给他一本支票簿,“你还是把刚才说的数目,开张支票给我。签好字,我就把信交给你。”
我听得大吃一惊。看模样警察厅长竟是吓得目瞪口呆。有半天工夫,说不出话,动弹不得,光是张大了嘴,瞪出眼珠,满腹狐疑地看着我的朋友;过后,才多少定下神,抓起一支笔,踌躇再三,怔怔地盯了几次,最后才开了张五万法郎的支票,签上字,递过桌子,交给杜宾。杜宾仔细看了一遍,就藏在皮夹里;再打开书桌,从里边拿出一封信,交给警察厅长。这个警官乐不可支地抓住信,颤着手拆开信,匆匆把内容看了一下,就来不及走到门口,招呼也不打,终于奔出房,跑出屋,一声都不吭,打从杜宾要他开支票,他就没开过口呢。
他一走,我的朋友就开始解释给我听了。
“巴黎警察办案本领倒非常高明,”他说道,“他们百折不挠,机灵狡猾,完全精通本行业务。因此,葛××把搜查德××公馆的详细经过讲出来,我就完全相信,他已经尽了力,做过一番调查工作,倒也挑不出眼来。”
“已经尽了力?”我道。
“对,”杜宾道,“他们采用的方法,在他们是最好的一种,干得也面面俱到。要是这封信藏在他们搜查的范围里,这些家伙包管找出来了。”
我听了只是呵呵大笑,可是看他模样,倒是说得一本正经。
“既然方法在他们是不坏的一种,办得也不差,”他接着说,“他们的失败就在于这方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况,也不适用于这个人。警察厅长的一套聪明透顶的方法,就是一种削足就履的办法,他硬把计划凑合这个陈规。不过眼前这件事,他不是过之,就是不及,所以一错再错;连不少小学生也都是比他强的推论家呢。我认识一个八岁左右的小孩,他猜单双这门玩意,百猜百中,赢得人人折服。这个玩意可简单,是拿弹子玩的。玩的人一个手里捏着一把弹子,问另一个,手里的弹子是单数还是双数。猜对了,猜的人就赢一颗;猜错了,就输一颗。我说的这个孩子把全校的弹子都赢去了。他当然自有一套猜法;这只消注意到对手有多机灵,估计一下就行了。比方说,对手是个大傻瓜,伸出捏紧的手,问,是单是双?这个小学生就回答,单,输了;可是第二回他却赢了,因为他心说,这傻瓜头一回出的是双,凭他那份巧心眼,充其量只能在第二回出单;因此,我就猜单;——他猜单,赢了。呃,要是碰上个比头一个傻瓜机灵一等的人,他就会这么推论:这家伙看见我头一回猜的是单,第二回,他一时情不自禁,就会像头一个傻瓜那样,来个简单的变化,从双变作单;可是转念一想,就会觉得这种变化太简单,最后就决定照旧出双。因此我就猜双;——他猜双,赢了。这个学生的推论方法,给他同学称为侥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不过是推论者的心思跟对手一样罢了。”我道。
“是啊,”杜宾道,“我问过那孩子,凭什么法子才能跟对手的心思一模一样,赢了人家,他是这样回答我的:碰上我想看出人家有多灵,有多笨,有多好,有多坏,或者当时的思想情况,我就尽量正确地在脸上摆出跟他一样的神情,然后等着看我脑子里想起什么念头,心眼里涌起什么心情,就像特地去凑合,或者去配合这副神情似的。这个小学生的答复就是一切貌似深奥的学问的根源,罗什富科,拉·布律耶,马基雅弗利,康帕奈拉的学问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如果我没误解你的意思,”我道,“那推论者的心思要跟对手一样,全在于正确估计对手的心思。”
“推论起来,就靠这个办法,”杜宾答道,“警察厅长和手下一批警察屡次失败,一来是没有跟对方一模一样的心思,二来就是错误估计对方心思,或者不如说,根本没去估计。他们想到的只是自己对人家巧妙心机的估计;在搜查什么隐藏的东西时,只想到他们自己会怎么藏法。他们这一点倒并不错——那套心机正是一般人的心机;可是碰到一个跟他们路子不同的老奸巨猾,当然只有屈居下风。凡是碰到比他们狡猾的人,他们始终居下风,碰到不及他们狡猾的人,也往往居下风。他们的侦查法则始终不变;就算碰到特别紧急的任务,特别丰厚的赏格,还是不改法则,至多也不过把办案的老办法变通一下罢了。比如说,在德××这件案子里,他们干过的事,哪一件改变办案法则的?钻啊,戳啊,测深啊,用显微镜照啊,把房子的表面画成一方寸一方寸,编上号码啊,这一切算什么?这只不过是一种搜查法则,或一套搜查法则的变通办法罢了!他们就是根据那一套对人们心机的看法定出这种法则,警察厅长办案多年,早就习惯了这种老看法。难道你看不出来,他认为所有的人要隐藏一封信,虽不一定在椅腿里钻个洞,藏在里头,但至少一定藏在什么偏僻的洞眼里或角落里,这想法跟人家想到把信藏在椅腿洞眼里完全是一个心眼。难道你看不出来,只有一般情况,而且只有一般头脑平常的人才会藏在这种煞费苦心的角落里;因为,一般人家藏东西首先可能这样猜想,东西要藏好,要藏在煞费苦心的角落里;这样的话,搜的人根本不必怎么精明,只要小心、耐心和决心,就可以搜出来;碰上紧要案子——碰到有重赏,警察就会看做紧要案子——他们必定会小心、耐心和下决心。你这总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要是这封失窃的信藏在警察厅长调查的范围内——换句话说,要是藏信的办法,凑巧跟警察厅长那套原则相符——那么要找出来根本就不成问题。可是,这个警官完全给弄糊涂了;他失败的原因就是把这位部长当做傻瓜,因为这位部长素有诗人的名望。警察厅长认为,凡是傻瓜都是诗人;因此推论,凡是诗人都是傻瓜,在这方面,他只不过错在违犯了不能因果倒置的原理罢了。”
“可是这一位当真是诗人吗?”我问道,“据我知道,他们有两兄弟,两人都是以博学多才出名。这位部长的的确确详征博引地写过专论微分学的文章。他是位数学家,不是诗人。”
“你搞错了;我对他倒非常熟悉;他不但是诗人,也是数学家。身为诗人兼数学家,必然精通推论;单单是数学家,根本就不会推论了,那就要落入警察厅长的掌心了。”
“我真没想到你有这种看法,”我道,“这跟世人的意见相反。你总不见得小看千百年来举世公认的看法吧。数学上的推论老早就被一致认为是最完善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