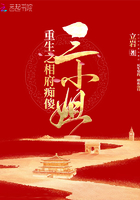时千抱了抱她,“早点睡吧,我很快就去。”
“你的那位叫薄成的朋友是不是不帮你?”
陶夭咬着唇,不是很懂这方面的事情,但想来他应是遇到了难题。
“真没遇到事。”
时千还是坚持说。
两人对视十秒。
他觉得她眼睛很亮,可以探测心里去。
实在受不住,直接招了,“就是吧,要建一个娱乐广场,上面还没批,大哥为首的股东们人心惶惶觉得会亏损。”
不是亏损不亏损的事,而是时千接任以来第一个做的大项目,开头炮一旦打响基本没什么后顾之忧了,时晏自是反对。
“那找薄成做什么?”
“他做银行这块,资金足,上面也有点人,多少能尽快批下来。”
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起不少用。
陶夭有点懵懵然,这件事听了后她也帮不上忙,不如不听,心里还能少点愧疚。
毕竟他帮她那么多,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她声音细小很多。
“能怎么办,得空就去骚扰他,好事多磨。”
“薄成和你有矛盾,万一要是和时晏联合在一起欺压你……”
“得了,你想那么多干吗,我不至于这么容易拿捏。”
时千波澜不惊,眸子里流淌暗流,愈发狠绝,嗓音却是轻描淡写,“他们真有什么行动,大不了做了算,一了百了。”
陶夭心里咯噔了下。
他转过来吻她,“吓坏了吧,哈哈,刚才我说话的时候特man?”
“不觉得。”
“欠虐是吧。”
他扔开手机,把她的腿压着,欺身而上。
…
陶夭上班的一大早经过办公室走廊,发现不少同事的目光盯着自己看。
她看了下手表,昨晚睡得迟,今天来公司的时间的确晚那么两分钟。
但不至于都看着她吧。
于雅凑过来,“陶姐,你看见窗口边的花了吗?”
“什么花,我的窗口?”
“不是,你的办公室是锁着的,花放在大办公室那里。”
陶夭诧异了会,跟着她一起去大办公室,果然看到窗台上放着一朵黑色的花。
妖娆又漂亮, 像是月季,但比月季花更鲜艳。
有人开始羡慕的恭维
也有人不偏不倚泼水,“这是黑色妖姬吧,现在市场上不是没培育出来这个颜色吗,都是药水染的。”
陶夭没说话,花上只有一张送给她的名片,还是打印宋体的, 根本不知道是谁送的。
蓝色妖姬代表了爱,黑色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管是谁送的,她先找了个花瓶把花放进去,这个颜色太过黑暗,当做摆设的话未免不合适。
是谁送的呢,时千?
他那样的人,怎么可能不留姓名。
那还有谁,江心和吗,他是个罗曼蒂克的人,就算送应该会送粉嫩点的花。
陶夭回国后没什么明质的追求者,真想不起来还有谁。
工作之余又继续想,时晏这个名字突然冒出来。
他的话……有可能,阴森森的可怖,送这朵花也不知什么意思。
下班后,陶夭很快就把这件事情抛向脑后,和时千出去吃饭,去了发现多处两个男人。
大嘴和薄成。
意外过后,她镇定下来,微笑自我介绍。
大嘴还算客气,报了个大众的名字,她没记住,但记得这人的嘴的确蛮大。
“时千,我还以为你就约了我们叙旧呢,没想到把媳妇也捎上,什么意思啊,请我们吃狗粮啊?”大嘴戏谑道。
“谁说的,还有郁少。”时千皮笑肉不笑,“一起吃。”
薄成一直没说话,眼睛深不见底,睇着他们。
郁之深最后来的,还多带两个妹子,分别去伺候那两大爷。
入座后,气氛倒也没冷。
“来说说,老时请我们吃饭是为了什么?”大嘴性子急,恨不得尽快把压轴戏放出来。
时千笑眯眯,“你猜猜。”
“秀恩爱?”
“可以这么理解。”
大嘴一听,搂着妹子啪嗒亲了口,“你哪算什么恩爱,哥也有妹子。”
时千不急不缓地剥了只虾,放入陶夭的盘中,擦了擦手,举起酒杯,“这顿饭当是迎风,这么久没见,连吃顿饭都磨叽?”
他慢条斯理地说这么一番,大嘴也不好意思逮着问。
话题渐渐扩展。
薄成很少说话,对送来的妹子碰都不碰。
酒喝得正是时候,郁少开始进入主题,先是问时千关于集团的事,揪出话题。
这顿饭一开始就是带有目的性的。
谁都知道,但谁都不说。
陶夭静静地挑着盘中的螃蟹吃,九月的螃蟹肥,但蟹八件用的不是很熟练。
他们说的正起劲,薄成淡淡地打断:“你们能别和夫妻一唱一和的吗?华千集团的事我不是不清楚。”
空气沉寂片刻。
陶夭掰螃蟹钳子的声音显得格外响亮。
感觉到众人的目光,她讷讷地笑两声,“继续。”
薄成也不继续说了,饶有兴致,“时千,你告诉你媳妇以前的事了吗?”
时千放下酒杯,似有似无地笑,“她都知道我以前做过的事,谁没有个过去啊,自己提前交代总比被发现好。”
说罢浅浅喝了酒,等待薄成继续说。
薄成适可而止住了嘴,笑,时千这家伙精得很,为什么把女人带来,不就是怕他们这些兄弟在背后嚼舌根吗。
背后嚼的舌根未必是真的,但当面坦白,哪一点不真,就有人给指出来。
“陶夭,是吧。”薄成顿了好些秒,“想知道……”
“薄总。”
时千适时地打断,唇际的讽刺埋得越来越深,直接改了称呼。
“华千集团的事呢,你再考虑考虑,毕竟同为兄弟,我也不会赖掉利息,钱给谁不是给啊,朝我这儿送不是更有保障,毕竟认识几天的和认识几年的不能比。”
说辞颇具诚意。
其他人皆不吭声。
薄成慢慢地背靠在椅子上,“可认识几天的狼和认识几年的虎对我来说都一样。”
这话一出,多少会撕破脸皮。
时千脸皮厚着呢,“怎么能一样呢,我比我哥帅。”
“……”
大嘴和郁之深顺着微微缓和的气氛接嘴,岔开了话题。
饭局结束,事情仍然拖拖拉拉没谈成。
陶夭有点担忧,自己也没派上用场,坐在副驾驶上偏过头看自家男人,“怎么办?他好像故意拖着。”
“拖着是好事,证明他还没有彻底被时晏拉拢。”
“在思量踌躇?”
“谁知道呢。”
陶夭见他漫不经心没有太想搭话的意思,体贴地不再问。
经过超市,他停了车,说去买杯水。
饭桌上基本没动筷子,都是动嘴。
“我去吧。”她按住他,直接拉开了车门,提着包包便走。
时千耐心地在边上等她。
百无聊赖地点上一根烟,车厢闷人,干脆出来透透气。
经过人行道的时候听到旁边呜呜的机动车响,条件反射地避开,却是两边夹击,整个人毫无意外地被撞上。
…
陶夭拿着水出来后没看见车里的人,纳闷地环顾四周,也没有人影。
超市人多,买个水都排了那么久的队,没想到出来后他人就没了,只见车门半敞,钥匙随意搁放。
拨电话过去,档位处却响起手机铃声——他的手机也没带。
心思不由得慌张,好好的人说不见就不见,正担忧时,旁边的乞丐凑过来问:“小姐,你是不是找从车上下来的那位先生?”
“你知道?”
“他被踏板撞了,被人送去医院,往那个方向。”说着指了个方向。
陶夭眉头蹙紧,怎么会这样,不过几分钟的功夫就被撞了。
“谢谢了……”她说着把包扔进车里。
乞丐讨好一笑,“不用谢,给我几个钢镚就行。”
她钱包里没有硬币,抽出了一张红票子递过去,又问:“那撞人的车主呢,逃逸了?”
“逃了,那位先生的保镖分了两拨,一拨追过去,一拨去医院。”
乞丐眼睛冒光,这般说着,又使了个眼色,“小姐你还是快走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车是故意报复的,有钱多作怪,惹祸上身啊。”
陶夭连连道谢,发动殷勤,迅速往医院的方向开去。
时千倒是随身带保镖,但他并不是小心翼翼的人,总不能下车就让保镖盯紧吧。
她在急诊眼熟一位保镖,忙跑过去询问具体的情况。
保镖们面露愧疚,毕竟是他们失职,“时总停好车后出来透透气,没想到转眼间就有踏板开过来,我们当时都在车上,根本来不及阻止。”
“他情况怎么样?”
“伤着腿了,出血过多,具体的就不知道。”
人还在里面呢。
陶夭没再开口,听说没有生命危险,悬着的心总算放下。
不知不觉中,她没发现自己担心时千的程度,不亚于之前母亲做阑尾炎手术的时候。
作为家属签了字,又去缴费,忙活一阵子,歇下来时看到其余的保镖也过来了。
“时太太。”保镖恭敬叫了声。
“逃逸的人抓住了吗?”
“他们骑的踏板比轿车灵活,专挑小道走,熟练得很,把我们都甩掉了。”保镖难为情地道,“警方已经介入了,可以调监控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