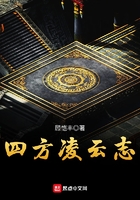郝先生被她的话一噎,神色古怪,“你不和我结婚过来相亲干吗,我告诉你,像我这种研究生毕业工资稳定还孝顺的男人不多了。”
“何止,像你这样的都绝种了。”
郝先生没听出她话里的讽刺,还自顾自接了下去,“真的不多了, 我一不抽二不喝酒也不嫖,不像那些男人,抽烟的钱都可以买宝马了。”
“那你有宝马吗?”
“没……以后会有的。”
陶夭一点都不想和这个男人继续呆下去,只觉得头疼,却不能擅自离开,盯着他鱼嘴一张一合叨叨说下去。
可能是听到“以后不管我们有几个孩子,都必须跟我姓”时,她终于憋不住了,找了个借口去洗手间。
出来的时候,郝先生也终于要走的意思,站起身,扒了扒钱包。
陶夭脸上仍然带着笑,出于在美国生活的习惯,“我们AA吧。”
郝先生意味深长地瞥了她一眼,“我们都是要结婚的了, 不用在我面前装样子,其实你一点都不想付账,这里的东西很贵。”
“……”
…
路上的车堵了很久,陶夭回到家已经七点多,从玄关处换鞋的时候看到餐桌上收拾干净。
陶母这时从楼上下来,看到她风尘扑扑的,“吃过饭了吧,没给你留。”
“嗯。”
“今天见的这位怎么样,我看人才还行,家境贫寒但人很努力,你要是看对眼就……”
“随便吧。”
陶夭敷衍着,去卫生间卸妆,仔仔细细回想起发生的事,以及那个玩游戏的男人,还真是尴尬啊,所幸只是个陌生人。
晚上躺在床上玩手机,和曲欣提及这事,把郝先生的语调模仿得惟妙惟肖:“我告诉你,像我这种研究生毕业工资稳定还孝顺的男人不多了。”
两人同时在电话里笑,曲欣问她:“你有告诉他你是海归吗?”
“没有,说了干嘛啊,回国也还是在一家小公司。”
“夭夭,说真的,这一个在你相亲对象中算是好的了,之前那一个,上来就说,我没房没车但我有一颗爱你的心,你愿意结婚吗。”
曲欣说起的这一个才是极品,弄得陶夭就差反呛他一句,我矮我丑胸小脸上还有一颗大痤疮但我有个爱你的心,你愿意娶我吗。
陶夭想起还有些工作没处理,把手机开了免提,翻开笔记本核对账目。
那边曲欣还滔滔不绝,“我跟你说啊,今天我们那个讨厌的店长突然宣布一件事,说他可能不再是我们的店长了,把我一激动,终于逃离恶魔的掌心了。”
那个店长,陶夭知道,曲欣没少在她面前抱怨。
“然后,你猜,他又说什么?”曲欣语设悬念。
“说什么?”
“说他由店长升级为经理。”
陶夭便隔着无线电波在那头笑,意外这个富家小姐能坚持这么久当服务员,想着想着不小心核漏了一个数字,又仔仔细细地找,突然无厘头地说:“我可能要订婚了。”
“哪一个,就今天这个?”
“嗯,我妈说双方都挺满意。”
曲欣却是极为敏感地察觉出不对劲,“夭夭,你真的想好了?”
陶夭沉默不说话,静静地呼吸,唇间的热气呼在电脑屏幕上,她望着那些小数点的数据,寡淡一笑,“嗯。”
“想好就行了,我还以为你一直会沉浸那年前……”
曲欣话到这儿止了口,抿了抿唇,一时想不起拿什么话再搪塞。
然后是两人之间的沉默。
“他回来了。”陶夭打破了沉静,率先开了口,又静静地陈述,“就在前几天。”
曲欣知道她说的他是谁,斟酌一番,小心翼翼地问:“一个人吗?”
“不知道。”
这时房间的门被敲响。
是陶母,她手里拿了一把旧的小提琴和薄薄的乐谱,放在了桌上。
“前些天收拾屋子找到的,没有征求你同意。”陶母陈述说。
陶夭静静地看了眼,敷衍地说没关系,然后看了下表,说晚安,两个字代表礼貌的驱逐。
一个人的房间,那把放在桌上的小提琴很安静地躺着,以及乐谱。
陶夭忽然想起,有个人说过,演奏时A调震动的频率,和人心脏跳动的频率是一样的。
…
订婚举办得很仓促,仓促的负面词是草率。
郝先生不愧是勤俭节约的好男人,给出的理由是,他抽到了那家五星级酒店的优惠券,八折优惠,两个星期内有效。
陶夭换新娘服的时候还想,手上的戒指是不是打折促销时买的。
一起在化妆间的曲欣比她还急还紧张,不停地问,真的想好了吗,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陶夭很冷静,面对她的问题是也冷静地说:“你以前说过,无非嫁给自己喜欢的,那嫁给谁都一样地将就。”
曲欣沉默,停止了叽叽喳喳,被陶母拉开后就老实地换上伴娘服,结果在一堆娘家人里她闹得最凶。
陶夭自始至终很冷静,笑容露出七颗牙齿,短发上多了一层假发,大卷,低头还能闻到护养水的清香。
订婚礼排场很大,农村出来的人讲节约的同时也好面子,周围全摆满了高层蛋糕。
婚礼节奏很快,不知不觉陶夭就换了敬酒服去敬婆家人的酒,耳边喧嚣,她忘记置身所境。
差不多要结束时,看了下有些菜样没动,喝了些酒的陶夭愈看愈觉讽刺,唤来服务员把这些东西打包。
喝得满脸通红的郝先生见此,腆着啤酒肚,嚷嚷推开那个服务员,酒精麻痹的小脑导致踉跄着过来,嗓门扯大的喊:“你们干什么,谁让你们打包的。”
几个服务员受了不小的惊讶,下意识地指了指陶夭,“是准新娘……”
那边的陶夭正在自己拿盒子打包,她做新娘的没吃多少,这时倒是一点也不顾形象地拿筷子夹着虾仁往嘴里送,边把没动的菜样打包。
“臭女人!”
郝先生一声低吼,快步走过来, 抬手就把那些饭盒全扫在地上,“谁让你打包的,丢不丢人啊。”
面对漂亮的陶夭,他还是有些克制的。
“怎么了?”
“这是我们的订婚现场,来的都是近亲,你打包做什么,丢死人了。”
“就因为是近亲。”陶夭顿了顿,笑得理所当然,“才可以打包啊,你不是崇尚节俭吗,我这样做有错吗?”
“行了行了,我不和你扯,你现在赶快住手。”
郝先生伸出手来阻止她,粗茧黏糊陌生的手碰到她的腕,一阵恶心油然而生,陶夭条件反射地缩回去。
心里不由得苦笑,她这是昏了头才嫁给这样的男人,连碰手都觉得是恶心。
陶夭闭了闭眼,又睁开,深呼吸一口气又是坚强的姑娘,她把饭盒从地上捡了起来,“郝……我看我们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