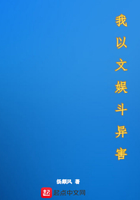那酒杯又细又长,陈泓一点点将酒液灌进去之后,便伏下身子,趴在嫣红身上一点点吸咂起来。
嫣红从来没试过这种,只觉得身子烫得几乎要烧起来了,意识都有些混乱了,只嘴里模糊不清叫唤着:“老爷……嫣红要死了……”
陈泓抬头笑道:“等会子还有更快活的呢!”
这般弄了一阵,陈泓也有些受不住了,火急火燎的脱了袍子,正要直捣禁门,门外传来紫楠的声音:“嫣姨娘!老爷可是在屋里?谢姨娘突然肚子疼,怕是要滑胎,求老爷过去看看罢!”
陈泓一听谢姨娘要滑胎,吓的马上软掉了。翻身从嫣红身上坐起来,一边手忙脚乱的穿袍子,一边大声喊道:“快去请大夫!我马上就来!”
嫣红正在得趣,哪里肯放陈泓走,拉住他的袖子道:“老爷,下午见姐姐还好好的呢!想是夸张了些也有的,您不如……”
话未落音,脸上已经狠狠挨了陈泓一巴掌:“贱人!你下面就痒成这样了?青儿若真落了胎,我马上把你卖到窑子里去!”
说着,理也不理嫣红,转身就走。
一个小小的姨娘,跟谢姨娘肚里陈家的儿子相比,陈泓自然更重视后者。姨娘可以随便挑,儿子可没那么容易得来。
陈泓走后,嫣红也不穿衣服,直接光着身子下了床,呆呆的坐在桌边,看着满桌已经冷掉的饭菜,眼泪缓缓从脸上滴落下来。
谢姨娘真的要滑胎?鬼才相信!她那胎儿宝贵的很,自打知道怀孕了,便整日躺着,人参燕窝不知吃了多少,哪儿那么容易就滑胎了?
不过是看陈泓宿在自己屋里,要争宠夺男人罢了!
身子仍然滚烫,被陈泓挑起的一股邪火无处发泄,嫣红只觉得整个身体都肿胀得快要爆裂了。
她恨恨的揪着桌上铺的锦幔穗子,咬牙切齿道:“银妇!都有身子了还要往屋里抢男人!你若小产了才叫大快人心哩!”
谢姨娘躺在榻上,见紫楠进来了,忙低声道:“如何了?”
紫楠掩口笑道:“成了。奴婢是掐着点进去的。老爷怕是正要入港呢!”
谢姨娘听了,心中又妒忌又有几分满足,果然,女人还是要母凭子贵呀,老爷都到那个份上了,还肯抛下嫣红过来探望她,若不是因为肚里的孩子,想也别想!
正想着,陈泓急匆匆走了进来:“青儿,究竟如何了?大夫过来没有?”
谢姨娘忙皱了眉哀声道:“也不知怎的,方才吃了盅燕窝粥,小腹便有些疼痛起来。婢妾怕有意外,才先遣了紫楠过去请老爷过来。老爷不怪青儿罢?”
陈泓忙坐到榻边挽了她的手道:“我怎会怪你呢?你肚里如今怀着胎儿,自然要多加小心。一会儿大夫来了,叫他好好为你把把脉。”
没过多久,大夫便来了,为谢姨娘把了脉便笑道:“姨娘并无大碍,大约是心情紧张,所以有了腹痛的错觉罢了。我为你开些安胎养神的方子,吃上几日便好了。”
陈泓听说无大碍,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大夫走后,谢姨娘屏退屋里伺候的丫鬟,趁陈泓不注意,将手伸到锦被中,偷偷将身上月白色衫子领口的绦子扯松,故意露出里面一截玫红色的软缎抹胸来。
陈泓见谢姨娘没大碍,劝慰了几句,便准备再回嫣红屋里。
谢姨娘忙坐起身去拉他的手:“老爷,这几日您都是匆匆的来,匆匆的走。青儿想跟老爷说几句贴心话都没机会。您就再陪青儿坐一会子罢!”
谢姨娘胸口薄薄的锦被滑落下来,露出她半敞的衣衫,里面一截玫红软缎,更衬得胸口的肌肤白腻若玉,丰满娇挺。
陈泓的眼神顿时就凝固了一下,不住的朝谢姨娘胸口扫来扫去。
谢姨娘心中得意,脸上却娇羞道:“老爷,您往哪里看呢?”
这分明就是蓄意调笑。偏偏陈泓最吃这一套,听谢姨娘这么问,身子就酥了一半,笑着偎到她枕边,伸手就往她胸口一捏:“自然是看这两枚宝物!”
谢姨娘笑得更加娇媚,将衫子又拉低了些,娇声道:“老爷既要看,就看个痛快罢!青儿的一切都是老爷的!”
陈泓听得极为受用,恨不得马上掀翻了谢姨娘,好好的弄她一番才好。只是顾念她肚里的胎儿,终究不敢放肆。忍了忍方道:“你这狐媚子,好端端的又被你惹出一身火来。偏偏你身子又不方便,想做些什么也不能够。”
谢姨娘娇笑一声,伏在陈鸿耳边轻声道:“身子不方便,别处还是方便的。老爷尽管用就是了!”
陈鸿心中一动,脸上只假装不解:“青儿说的是哪里?”
谢姨娘也不回答,只伸过头,将嘴唇贴在陈鸿的嘴上,陈鸿忙伸出舌头接住,二人厮磨一阵,谢姨娘方轻声道:“老爷,就是这处呀!”
陈鸿大吃一惊,随即又喜出望外!
他在衙门里,也听同僚说过,青楼的女子擅长口技,只一张殷红的小嘴,就能弄的人死去活来。没想到,他在自家府里,今日竟也有这般艳福!
谢姨娘使出浑身的招数,将陈鸿弄的神魂颠倒,连泄了几次,才偃旗息鼓,二人搂抱着睡了。
嫣红在屋里左等右等,等到夜深了也不见陈鸿回来,遣了婆子去打探,婆子回来禀道:“老爷已经在谢姨娘屋里歇下了。”
“不可能罢!老爷方才……”嫣红不由得脱口而出,话说了一半才察觉到自己失言了,脸马上羞红了起来。
那婆子是过来人,自然知道嫣红的意思,走过来鬼鬼祟祟小声道:“听说谢姨娘今日还伺候老爷了。屋里银声浪语的,怕是快活的很呢!”
嫣红听得火冒三丈,扬手便摔碎了手边一个茶盏,怒道:“好个银妇!一身狐媚手段,真真是不要脸!”
婆子挤眉弄眼道:“谢姨娘刚进府的时候并不像今日这般得宠,那时候郑姨娘的宠爱可比她要多的多!后来,她来了个远房表姐,在她院子里住了两个月,等那表姐走了之后,谢姨娘就慢慢开始得宠了。”
嫣红听得莫名其妙,这婆子怎么突然提到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表姐?
便有些不耐烦道:“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比她年轻貌美,争宠竟还争不过她,真真是恼煞人也!”
婆子知道嫣红没听明白,忙道:“老奴之所以提到谢姨娘的表姐,是因为那表姐十分蹊跷,瞧着不像良家的女眷,倒像是青楼过气的花魁。”
嫣红心头一动,惊道:“谢姨娘请了青楼的花魁冒充自己的表姐?”
婆子见话说开了,索性笑道:“当时伺候的老人都说呢,谢姨娘是专门请了花魁来教自己房中术的!”
嫣红一下子全明白了!难怪方才陈泓说谢姨娘喜欢那些招数,原来都是跟花魁学来的!青楼花魁是什么人?就是靠伺候男人为生的!跟她们学了房中术,还愁笼络不了男人的心?
见嫣红恍然大悟的神情,婆子谄媚道:“嫣姨娘,老奴有个侄女,从小被后娘卖进了窑子,好容易从良了,结果刚过了几年好日子,夫君又得病去世了。如今生活无着,十分凄惨。您若是也想学那房中术,我便请了她进府,您只说是来投奔的远亲便是了。您看如何?”
嫣红听了冷笑道:“我说你怎的如此好心,跟我说这么多谢姨娘的阴私。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叫我替你侄女养老呢!”
婆子听了忙跪在地上拼命磕头:“嫣姨娘,您真真冤枉老奴了!您是什么身份,老奴岂敢叫您为我那苦命的侄女养老?不过是想着您也有这个需要,叫她也混口饭吃罢了!”
若自己也学了房中媚术,凭着年轻丰满,定然能将陈鸿哄得服服帖帖的,到时候再生几个儿女,还怕在陈府站不稳脚跟?
嫣红想了想,便转怒为喜道:“做什么下跪?我唬你的呢!快起来罢!”
当晚,嫣红便和婆子商量好了,过两日便叫她那侄女进府,嫣红只推说是远房落难的亲戚,来投奔几个月,待家里灾荒过去了,便要回去。
周氏面软心慈,这般说辞,没有通不过的。
谢姨娘和嫣红的这段公案,当晚便传到慈寿院陈老太太的耳中。
陈老太太听了气得把手中的茶盏往桌上一顿:“嫣红是个蠢的,谢姨娘竟也这般不省心!有了身子还要争宠吃醋,抢着往屋里拉男人!若是肚里的胎儿有了差错,我定然饶不了她!”
姚妈妈劝道:“老太太看开些罢!谢姨娘把自己肚里的胎儿看得十分金贵,料想也不会太过孟浪。”
陈老太太怒道:“她肚里的孩子是我陈家的子嗣!我如何不紧张!本来还想着,她若能生下个儿子,便将她的月银再加二十两,现在看来,她果然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狐媚子!”
说着,又落起泪来:“谢姨娘如此狐媚轻浮,泓儿整天和她呆在一处,如何能有出息?我要赶快想办法除了周氏,为陈家娶个精明能干的嫡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