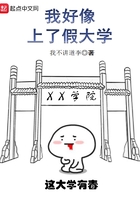这么闹腾了一出,陈宜菡再也睡不着了,屋子里和院子里似乎都有些奇怪的响动,窸窸窣窣的,听上去阴森而诡异。叫人打了灯笼去看,却又没看见什么异样。
虽是暑天,陈宜菡却浑身冰凉,她总觉得窗外有一只血红的眼睛在盯着她,随时都有可能闯进来要了她的性命。
陈宜菡躺在锦被下,紧紧握住凝霜的手,整个人都僵硬了。她就这么睁着眼睛熬到天亮。
等到早上,凝霜为陈宜菡梳洗时才发现,陈宜菡昔日白皙清丽的容颜憔悴不堪,眼底下两团青黑的眼圈,便是用厚厚的脂粉也遮掩不住。
陈宜菡见凝霜面色有异,忙朝镜子中看去,镜子中的女人,也瞪着两只失神的大眼睛看着她。
陈宜菡满面怒气,拿起水粉描花的胭脂缸子,“砰”的一声,狠狠砸在铜镜上!
“姑娘!不过是没睡好,气色差了些罢,好好歇息两日便好了,您的容貌向来是极美的!”凝霜忙放下手中犀牛角梳,边帮陈宜菡揉捏着后颈,边好言安抚道。
陈宜菡却咬牙道:“不是已经请过高僧作法么?为何夜里院子中还有莫名的响动?”
凝霜笑道:“是姑娘多心了罢,奴婢就睡在姑娘旁边,并不曾听到什么响动。姑娘,您且放宽心,方才我倒院子里瞧了,也没再见到血脚印,想必那不干净的东西已经被驱走了!”
陈宜菡细细看着凝霜的脸色,见她笑容坦荡,不似作伪,心里才慢慢安定下来。
静悲大师乃当今得道高僧,想必不会连只恶鬼都镇不住罢?
凝霜用兰花露揉开香膏,在掌心捂化了,细细帮陈宜菡涂在面上,又用丝茧子沾了官粉,将她眼下的青黑眼圈一点点遮了。再调了胭脂,染了娥眉,整个妆上完之后,陈宜菡的面色果然好了很多。
凝霜又从箱笼里拿了一件淡紫色木槿暗花的鲛纱收腰、月白色文锦镶边的长褙子,和一条姜黄滚银线马面裙,给陈宜菡换上。
又为挽一个望月髻,佩戴了一只赤金嵌五彩宝石的蝴蝶簪,那蝴蝶的触须用了两根细如发丝的金丝做成,顶上缀两只指头大小的珍珠,走动起来触须不停颤动,带得两颗珍珠也晃动不已,煞是灵巧可爱。
打扮好之后,陈宜菡面上虽还有憔悴之色,但容貌也恢复了七八分,颇看得过去了。
陈宜菡满意的看着镜子中娇滴滴的女子,对凝霜笑道:“你果真是个手巧的。这样妆扮起来,谁也看不出端倪。若顶着两只青黑的眼圈出去,被陈宜宁和陈宜月那两个贱人看见,只怕又要取笑于我。”
凝霜笑着奉承道:“姑娘的容貌,便是憔悴了也比她们好看。”
主仆二人说笑几句,陈宜菡便带着凝霜到周氏屋里去请安。
陈宜宁和陈宜月已经先到了。正站在周氏身边,准备和丫鬟一起服侍周氏用早膳。
陈宜菡强作笑颜,走过去向周氏行了礼,又朝陈宜宁和陈宜月福了福身:“二位姐姐也来了。”
陈宜宁只淡淡点了点头算是回礼。陈宜月却笑道:“妹妹如今就住在荣华斋隔壁,怎的也起这么晚?”
陈宜菡心中暗暗恼怒,脸上就带出了几分,她看着陈宜月身上素淡的蜜合色褙子,冷笑道:“菡儿资质粗陋,自然要在装扮上多花些功夫。不像姐姐,随便穿件褙子,便到正房来给嫡母请安了。”
在大齐,为了表示敬重和礼仪,贵族小姐在见长辈时是需要认真装扮一番的,越是重要的场合,越应该打扮得隆重。
陈宜月本想刺陈宜菡几句,不提防她竟会回嘴,一时倒愣住了。
她素日本也是爱打扮之人,在衣饰上极其用心。只是见陈宜宁家常只穿些素净的罗裙,也不耐烦带金钗玉簪,打扮的极是清雅,她有心讨好陈宜宁,便也学了她,专捡些素净的衣衫来穿。
不想今日竟被陈宜菡拿来说嘴。
陈宜宁把一只玉色的琉璃碗摆在周氏面前,又用乌木嵌银头的筷子帮她夹了一块茯苓糕,方道:“三妹妹多虑了,母亲不是那挑剔刻薄之人,穿什么衣衫过来请安倒在其次,关键是真的有孝心。再说,姐姐天生丽质,便是穿件素白的衫子,也如梨花映月,清雅贵气。”
说着,又淡声道:“三妹妹,你是该认真打扮一下,我瞧着你气色不太好,眼圈也有些青紫,莫非是昨夜没睡好?”
陈宜菡心中大怒,知道陈宜宁是在看她的笑话,却碍于周氏在场,也不敢太过嚣张,只好勉强笑道:“姐姐说笑了,妹妹昨夜睡的很好。今日早起,凝霜还夸我气色好呢!”
陈宜宁心中暗暗好笑,陈宜菡这要强好面子的性子,这辈子定然是改不了了!昨夜撕心裂肺地尖叫了半天,如今又说自己睡的很好。
好罢,既然屋子里放老鼠进去吓不到她,那今天便改毒蛇好了。
陈宜宁也不跟她争嘴,只微笑着服侍周氏用早膳。
周氏瞟陈宜菡一眼道:“三丫头,你不是日日早起去慈寿院伺候老太太进早膳么?既已请过安,便过去罢。恐怕老太太还在等你呢!”
很明显,周氏是在下逐客令了。陈宜菡心中愤恨,不情不愿的对周氏行了礼,竟然理也不理两个姐姐,便带着凝霜等走了。
自从陈老太太吩咐了周氏和陈宜宁等不用日日过去请安,陈宜宁也乐得清闲,在周氏这里蹭了顿早膳后,便带了绿桑和琥珀回了自己的院子。
回到秋爽斋,陈宜宁命琥珀将廊下的竹帘放下来,又搬了贵妃榻到窗边,便偎在榻上看起医书来。
早上去荣华斋请安之前,绿桑命婆子将瓜果桃李放在水晶盆子里,又用吊桶放到井里湃着。
回来之后便喊婆子把吊桶拿出来。将瓜果切成小块,又用银签子扎了,放在一只白底缠枝莲花遍地金的大盘子里,笑着放到贵妃榻边的小几上。
“姑娘,吃些瓜果罢,刚从井里取出来的,正好消消暑气!”绿桑边说着,边把榻边的冰盆子稍微挪远一点。
琥珀就是耳根子软,姑娘说什么便是什么,姑娘贪凉,冰盆子快放榻上了,琥珀也听她的!若是招了凉气可如何使得!
绿桑在心里嘀咕着,听着陈宜宁一声不吭,竟似没听见她的话一般。忙扭过头去看陈宜宁,只见她全神贯注的盯着手中的医书,眼睛都不眨一下。
绿桑笑着摇摇头,姑娘一看起书来,竟比爷们还要用心呢,若是男儿身,怕考个状元也不难的!
正想着,陈宜宁突然眉眼一展,扔了书哈哈大笑起来:“终于被我参破了!原来解药就在书里!”
绿桑也不理,仍由她疯疯魔魔的喜笑颜开,只拿银签子扎了块西瓜放到她的嘴边:“姑娘,快吃块西瓜罢,正凉着呢!”
陈宜宁咬下西瓜,一叠声的唤琥珀道:“琥珀,你让小厮去药店给我买几样药材回来。”
琥珀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跑过来,听陈宜宁一一报了药名。有的药名甚是生僻,琥珀苦了脸道:“姑娘,您且慢些说,奴婢记得慢。”
陈宜宁也不生气,笑着下榻拿了泥金的云纹纸,又命绿桑磨了墨,在纸上一一写得清清楚楚。
琥珀拿起那云纹纸一看,一色的柳体小楷,清劲挺拔,全无半点闺阁的脂粉之气。
琥珀奇道:“姑娘,您抓这些药做什么?”
陈宜宁顽皮一笑,神秘道:“先不告诉你,过几****便知道了!”
琥珀忧心道:“姑娘,你的医术是半路出家,万一开的方子吃死了人,可如何是好?”
陈宜宁听了倒愣了一下,想了想,方点点头道:“还是你考虑的周全。药方抓回来后,须得先试一试,待成功了才好用它。”
绿桑最是机灵,心中隐隐猜到了几分,忙笑着问道:“姑娘,这方子,可是用来对付偏院那个的?”
陈宜宁笑着捏了捏她的耳朵:“小蹄子,莫要乱猜,当心我拿你做药引子!”
傍晚时分,药终于抓回来了。
陈宜宁也不用厨房的婆子,命琥珀在廊下支了小炉子,又亲自挑了个不大不小的瓦罐,一边看着医书,一边小心翼翼的把药材放进瓦罐。
又要把握火候,又要不停地翻搅药材,还要时不时看一眼医书,把陈宜宁弄的手忙脚乱,雪白无暇的脸上也沾了一道黑色的烟灰,看着颇有几分童趣。
绿桑和琥珀在廊下看着她忙碌。陈宜宁不准其他人过去,她们倒乐得清闲。
绿桑拿纨扇掩了嘴笑道:“琥珀,你瞧姑娘那认真的劲儿,便是将来给姑爷做膳食,也不会如此上心罢?”
琥珀也笑了:“姑娘真是孩子心性,这大热天的,烟熏火燎的,她倒受得住!”
绿桑笑道:“只别叫我们试药就好了!姑娘的方子太霸道了,想想那血脚印,我还瘆的慌呢!”
琥珀忙朝周围扫一眼,见四下无人,方去拧绿桑的嘴:“小蹄子,小声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