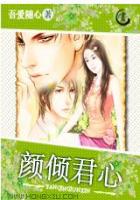没想到婆婆又说起话来:“像你母亲那种人,能教出什么好女儿来。”“婆婆,我是不是破鞋,你儿子最清楚的,我本就是清白身,你们的家人为什么总是故意为难我?”我真后悔和婆婆提起阿熠的事,她也是全心刁难我的。
这个婆婆总是帮着她的儿子,说话含沙射影,怪我不是这样不好就是那样不好,没有照顾好他的儿子,还要我赶快生孩子,要不,就离婚另娶一个。我在这个家,根本就没有地位,小姑那些势利的眼光同样带有轻蔑。
不久,我真的怀孕了,天真的我高兴相信,有了孩子会带来家的快乐,当然阿熠知道了也开心,态度比以前稍好一点,可是好景不长,在一次回乡的路上不小心摔跤引至流产了。
这下大件事啦,我的那个霸道专横的婆婆对着阿熠发怒:“都叫你不要娶她,你总是不听劝告,现在怎样,流产了,在我们乡俗是不好征兆的,这叫娶的人不好,回来会影响风水的,还有村里的人对我都很尊重,和你一起结婚的人都怀上了,有的都生了,你娶这么个老婆怎么不争气,你看某些人都在取笑我呢,叫我怎办?”
也许平时婆婆说话的语气过大,再加上势利的嚣张性格,别人取笑觉得无面子而大发脾气。阿熠对这个母亲也是孝顺子,沉默不语。
可是回来后,就冲着我大骂:“你太失礼了,你把我的面子丢尽了,叫我如何见人”骂得我狗血淋头。我在他的面前不敢哭,只是细细的声音:“我都不想的,医生说,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曾做过人流,叫我以后要小心点,再怀上的话要好好安胎休养。”
我极力忍着自己的悲痛,用颤抖的双手捂着面,跑上二楼的房间门角里,尽量不让他看见我抑住夺眶而出的眼泪,双手抱头无力地坐在地上哭泣:每次总是听到别人说自己如何受苦受累受委屈,可是说出来的苦是苦吗?我的苦呢,怎说?向谁说,说不出的苦才是苦呀,深感能忍受就忍受。
无论我怎样去努力,怎样去付出,对我来讲所有的一切全是徙劳无益的,那绝望的情绪,俞是压迫我心,我心灵充盈这诅咒的情绪却俞是凶狂奋激,我把这个家所有的一切,从我流产开始一一记住深入骨髓。
我并没有把婚后如此惨不忍言告诉母亲家里人,母亲的人生太累了,若然知道我遭遇如此折磨,只会令她更心痛更难过,谁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好,过得幸福快乐,不要像她那样的过去。
我也没有告诉小惠和小珠,她们太懂我了,把所有深深埋藏心里,唯一的苦恼自己去承受。不知情的人们还以为我好好的,表面是小鸟依人,而背地里隐藏多少难言之隐隐,极度凄凉苦闷骨子里是愁。
休息那天,在街市买菜,无意中我看见了同学阿平,正好她下班也是买菜,我忙走了过去:“阿平,这么巧你也在此呀,今天休息吗?”阿平看着我惊异地说:“你怎么瘦了?最近工作得很辛苦吗?还有听说你的爱人当上领导了,有这事吧,好多人都称赞你找了个好老公呢。”
我没有说起自己的事,只是向阿平问起:“有陈子扬的消息吗?算一算这一届的同学大学也应该毕业了吧?子扬有无回来?”阿平还是那样笑了笑:“你就是喜欢打听他,你喜欢他吗?不过听人说他有回来的。”她看着我不好说的表情。
听了阿平的话,我心里想:就算是子扬回来了,自己也不好意思说起什么事来,他还不知道我当年喜欢他,对他一往情深,只是一种朦胧的奇妙,就算是知道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会喜欢你吗?喜欢了又怎样?自己已成家,况且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已经没有印象。
再说他也有自己喜爱的人的幸福,谁会在乎你当年那份天真的朦胧?子扬:真的好想见到你,如果真见到你,我摸着自己的的脸颊,不敢想下去,情绪会如何?我望向天空,唯有真诚地祝福子扬,希望他得到自己的幸福快乐。
我面对着阿平:“以后同学有什么联欢会,记得通知我。”“好的。”我道谢了阿平,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家,阿熠在客厅里,还有几个客户朋友,他看见了我,满面冷若冰霜,充满敌意和憎恨,眼前的情况如此,我遇到的是一堵不可逾越的冷酷而知敌意的障碍。
突然听到:“什么时候了,现在才回来?买个菜也到处乱窜,一点儿都不正经作事,赶快做饭去,不要在这里欠羞。”像这类说话我都习惯了,但是当着众人我堪觉委屈,不觉眼睛滴下泪儿,走进了厨房,免得让人看见。
客人觉得阿熠说话过分,有一位朋友说:“我有事先走了,下次再吃饭,还有,老婆不是用来闹的,骂的,好好对她吧。”这句话我听到了,阿熠不好意思只好叫客户外出吃饭去,走的时候狠狠地瞪眼我。
当晚,阿熠回来后,我又目睹一场战争,只见阿熠对着我大声指责:“你看你是什么样?把我的客人都赶跑了,你就是那么不知趣,怎样?想得别人同情呀,这个可怜贱样看见就讨厌。”
平时爱出风头的阿熠又怎会在你面前认错呢。他望着我红红的眼睛和惶悚的脸容又再发怒:“哭、就知道哭、生成苦瓜干的样子,一点笑容都没有,像个死人般,真是前世欠你了,你这个臭娘和你结婚就是那么倒霉。”在他的语言、脸色与眼神中看到,我吓得目瞪口呆,那种歹毒而冰冷的敌意,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接连着来。
我意识到这不是偶然的,以后还会发生,想到此情景我不寒而栗了,他骂人是如此贪得无厌。我含着一身的屈辱,说不出苦中的艰难,忍气吞声,他自私,忽视了我的需求,只是强调自己的愿望,从来不会给机会去互相之间沟通理解。
特别是流产一事后,他经常在外鬼混,在女人的面前自吹自擂,对他的所作所为我已无权过问,也不可能有任何责问,每次回到家像个陌生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