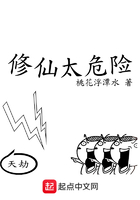汉王朱高煦奉召入京,行至奉天殿外,马煜进殿通报:“陛下,汉王殿下到奉天殿外了。”杨士奇、杨荣正在殿中奏事,听闻汉王前来,便说道:“陛下,臣等先告退。”朱棣说道:“不必,朕忙着呢,此刻没工夫见他。马煜,去东宫告诉太子、太子妃、皇太孙,万安宫告诉赵王、赵王妃。还有,叫上王贵妃,让他们今夜都来奉天殿,朕有家事要处理。”马煜问道:“那汉王?”“褫其冠服,囚在西华门内,今夜再将他带到奉天殿。”“是,陛下。”马煜应着出了奉天殿。朱棣对杨士奇、杨荣说道:“今夜你俩也来奉天殿。”
夜里,待众人都跪倒在了奉天殿上,朱棣说道:“除马煜外,宦官、宫婢们暂且退下。”待众宦官、宫婢纷纷退出,朱棣才说道:“朕有家事需要处理,正好首辅、次辅都在,那朕便直说了。今日奉天殿上都是朕最亲近,最信得过之人,咱们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好?”众人应着:“遵旨。”
朱棣拿出彭旭伪造的诏书,“朕实在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竟想要朕的命,那毒膳朕虽不曾进,可那毒药的滋味却仿佛一直在朕口中不能消退。你们可着实伤了朕的心。朕真是白疼你们了。也罢,这帝王之家本就无父子之亲,是朕太过奢求了。”朱高燧连忙叩头,“请父皇明察,儿臣冤屈,高燧从未有过谋弑父皇之心,高燧只盼着能与如愿相伴一生,父皇万寿无疆,大明国运昌盛。”“朕知道不是你,朕已知道是谁,朕伤心的是自己疼爱多年的儿子竟对朕如此残酷,既然利用朕思怀碽妃之心行谋逆之事,着实可恨。”朱棣说完此话,大殿上一片寂静。过了一会朱棣从案桌上拿起一幅画卷,“马煜,将此画展开给他们看看,仔细着,若弄坏了此画,朕要了你的命。”马煜应了一声“是”,便小心翼翼将画展开。众人看去,画中乃是一女子,那女子宛若天仙、皎似秋月,明眸善睐,风姿绰约。只见她发髻高耸,凤翘双插,白衣白裙外,穿着淡粉色比甲,芊芊素手拈着一束梅花。这窈窕飘逸的仙子,只在画中嫣然一笑,便足以倾倒众生。看过画像,众人不禁侧头看了看如愿,因这画中女子眉眼之间有些像如愿,又见朱棣如此珍视此画像,众人心中便猜到了,这便是碽妃当年留给朱棣的画像。朱棣见了众人反应问道:“高燧,画中女子可美?”高燧答道:“画中女子美极。”朱棣说道:“当年太祖皇帝也如此认为,他认为这画中女子美极,便纳此女子为妾。此女子为太祖皇帝诞育皇四子燕王棣、皇五子周王橚。”朱棣此言一出,众人伏地叩首,“陛下恕罪。”朱棣接着说道:“好了,今日殿上之人皆知碽妃是朕的生母,何止是你们知晓,宫中多人都知道此事,只是无人敢提。朕对碽妃的情义你们都已知道。可最可恨的是......”说道此处,朱棣将案桌上的杯盏一把摔在了地上,大喊道:“最可恨的是利用朕对碽妃的情义行夺嫡之举,这便是死罪。”众人惊恐万分,又是一阵叩首,“陛下恕罪。陛下恕罪。”朱棣猛咳了一阵,接着说道:“如愿上来。”如愿战战兢兢抬头看了看朱棣,朱棣又向她招手,“到父皇这来。”
柳如愿战战兢兢走到龙椅旁,朱棣问道:“看这画像中的碽妃,像不像你?”如愿颤抖着说道:“眉眼之间能有几分似碽奶奶,如愿不甚荣耀。”朱棣问道:“还记不记得那年在士奇的梅园当中你吟的是哪一阙词?”“回父皇,如愿吟的是朱敦儒的《鹧鸪天?西都作》:‘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棣接着问道:“你可喜欢梅花?”“喜欢,人间芳菲之时,它默闻无声;天地冰雪之际,它傲然独放。当真是‘此花不与群花比’。”朱棣听了此话欣然笑了,“碽妃也喜梅花,朕幼年时,碽妃经常与朕在梅树之下玩耍,还曾抱着朕在梅树下哄朕入睡。朕记得那年梅花盛开,母妃带着朕与五儿赏梅,母妃告诉朕,她此生最爱梅之傲骨,教我们习梅的品行。即便身处风雪之中,也要盎然怒放。然后,母妃便教我们吟了那首《鹧鸪天?西都作》:‘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几十年了,朕多少次置身风雪,甚至几番险些丢了性命,才有了今日的皇位,只因朕从不曾忘记母妃对朕的教诲。不想几十年后,又是梅园当中,朕居然又听见有女子吟这首《鹧鸪天》,当这女子回身之时,竟与母妃那般相似,朕当即便决定要赐这女子终身富贵。既然母妃直至殁逝才得了碽妃名分,那朕就偏要让如愿入宫便是贤妃。可不料高燧早就钟情于如愿,那朕便将如愿许给他,朕想着,如愿做了朕的皇媳,朕也可予她富贵。”大殿上一片寂然,朱棣停顿了一会,情绪异常激动地说道:“朕虽贵为天子,可连自己的生母都不能认,如此苦痛你们谁人能知?朕幼年骑射之术乃是与碽妃所学,那日京郊狩猎之时,朕思怀生母,便教了如愿骑射,可竟有人借此生事,意欲谋嫡......高煦,你还有何话说?”朱高煦万分惊恐,叩首说道:“儿臣冤枉,请父皇明察。”朱棣拿着两份“诏书”,走下殿来,行至高煦身前,将那两份“诏书”扔在朱高煦脸上,“冤枉?你作何解释?你谋君弑父,大逆不道。着今日起废为庶人,此生不可入京。”
朱棣说完,转身要走,朱高煦却大喊一声:“父皇。”朱棣听到朱高煦的喊声,回过身来,只见朱高煦一把撕烂自己的衣衫,“父皇请看儿臣身上的伤疤,这都是当年与父皇‘奉天靖难’之时所受,当年建文逼得我燕王府走投无路,我父子同心,齐力作战。父皇请看儿臣胸膛这最大的伤疤,便是在大战浦子口时所受,当年那士兵的长枪再偏离半寸,儿臣便当即毙命。父皇曾言世子多疾,让儿臣勉之,可父皇得了天下,便不疼爱儿臣了吗?只是两份诏书便将儿臣废为庶人,如今父皇得了天下,可不及在燕王府时疼爱儿臣了。父皇的骑射是碽妃所教,可儿臣的骑射却是与父皇所学,父皇难道都忘了吗?”朱棣听了此话,看着朱高煦身上的伤疤,想到了三个儿子年幼之时的情景,又想到了当年“奉天靖难”之时,高煦多次救了他的性命,顿时心软了下来,朱棣默然无语,缓缓走到龙椅处,慢慢坐了下来,长叹一口气,两行清泪顺着脸颊流下来,说道:“削汉王左右两护卫,汉王即日便回乐安。董旺、孟贤、彭旭图谋不轨,大逆不道,凌迟处死。都退下吧。”众人见此情景齐喊了声“万岁”,便退了出去。
众人都退出了奉天殿,只有杨士奇、杨荣起身后对视了一眼,仍旧留在殿上,他二人明白,若不在此时置汉王于死地,日后汉王定会再兴风浪。朱棣向大殿之下看去,“士奇、勉仁,你二人为何还不退下?”杨士奇说道:“陛下,汉王谋反一事,若如此便作罢,恐怕众人不服。”杨荣跟着说道:“陛下,若此事就此了结,恐汉王再图不轨。”朱棣说道:“锦衣卫来报,汉王私选各卫健士,又募兵三千人,不隶籍兵部,兵马指挥徐野驴欲将他不法之事上报朕,他便用铁瓜挝杀了徐野驴。还有,董旺进毒膳那日,汉王府兵士整装待发,只待朕晏驾后,汉王宫变登基。”杨荣甚为不解,“既如此,陛下为何?”朱棣叹了口气,“朕已削了他左右两护卫,且再给他一次机会。朕是大明皇帝,也是一个父亲。请二位肱骨之臣体谅一个父亲的心。”
朱高煦回到乐安,虽平安而返,却被削去了左右护卫,心中大为恼火。汉王府中,韦凤娘问道:“不知此密事是如何泄露出去的?”朱高煦答道:“暂且不知,只知道是那朱瞻基带兵上殿,才坏了大事。”韦凤娘恨恨地说道:“又是朱瞻基那小贼。”朱高煦点点头,“若不是有他在,父皇早便废了太子。早知如此,当初就先除掉他。”韦凤娘说道:“如今父皇削了汉王府左右两卫,咱汉王府只剩中卫了。”“那又何妨?你别忘了,当年父皇八百兵士起事,照样夺了天下。”韦凤娘疾步上前,“殿下如今是如何打算的?”朱高煦将案桌一拍,“王府所剩护卫,严加操练。柳如愿、杨士奇等人绝对留不得,如今柳如愿已有孕,本王知会宫中亲信见机除了她。”“既然着戴原礼安胎,恐怕除之不易。”朱高煦坏一声,“无妨,若十月怀胎都不能置她于死地,待她诞下皇孙,众人皆会放松警惕,那时再取她性命也不晚,除了柳如愿,便可除杨士奇,再静待时机,除了朱瞻基。到时候扳倒太子便易如反掌。”韦凤娘赞道:“殿下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