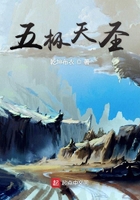第六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情况危在旦夕。
以柳残风的去势,他绝对无法闪过那第二把偷袭的剑。
但对方没有估计到的是,他在闪身躲避第一剑的同时,在半空已经飞快地抽出了自己的剑。
一个就算在睡觉时都抱着剑不放的人,是时时都不会放弃戒备、时时都准备着拔剑的。
残风拔剑,全力迎向第二个行刺的人。
双剑相击,若对方是一把普通的剑,此刻早已断为两截了。
但显然对手不是等闲之辈,用的也不会是等闲的兵器。
对方的剑没有断,且与第一个出剑的人相会合,双剑合璧地再度向残风刺来。
都是剑道高手,而且,一看二人便是惯于合作的,他们使的是互为补足的同一种剑法。
双人剑,是剑法,也是一种阵法。
几乎没有破绽。
残风只觉得眼前的剑光交织成了一张密麻的网,兜头盖脸地向他笼罩过来。
全力迎击,除此之外似乎没有第二条选择。
看对方的样子,是抱着必杀之心,一定要将他置于死地。
何时结了这么大的宿仇?他自己竟不知道。
最高明的剑法也一定会有破绽,他见招拆招,努力寻找着对方的死门。
正在最激烈的时候,突然横空又出现了一把剑。
这把剑出现得极为突兀,将原本全心对付残风的那两人分了心神,只这一分心的时机,残风已经找到了疏漏。
下一剑刺出的时候,听到了对方其中一人的一声惨叫。
紧接着,又传来另一声惨叫。
待一切静止,残风看到自己的剑所料不差地刺在对方一人的心口位置。
而另一人的心口却也同样插了一把剑——正是在打斗中跑出来搅局的那把剑。
剑在一个老者的手中,国字脸,头发枯黄,胡须却是黑中微带着红。
虽是不认识,但对方毕竟帮了自己,残风礼貌地道了声谢:“多谢前辈援手之恩。”
“不敢。”老者却很谦虚地道,“看得出来,就算老朽不出手,少侠亦可以独自应付,只是会比较辛苦一些。”
残风微微挑了挑眉,没有否认。
“在下乃泰昶长公主府上门客,秋苋翁。”老者自报家门。
果然长公主不会轻易放弃他,他的身边不曾断过公主的眼线。
“我家公主对少侠剑艺颇为称道,今日一见,果令老朽大开眼界。”
“前辈谬赞了。”
“我家公主最是识英雄而重英雄,以少侠的身手,若是效命于公主跟前,前途必定无可限量啊。在南陵,长公主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身份地位无可匹敌。”
“只可惜,在下身为浪子,以自由逍遥为乐,向无功名利禄之心,只怕要辜负公主厚爱了。”
残风仍是不卑不亢,婉言相拒。
当初并不知道她是南陵长公主,若是知道她的身份,他说不定未必出手相助了呢,亦省得惹此麻烦。
“少侠以自由逍遥为乐,可知得罪了游魂宫,便再难自由逍遥了呢。”
“游魂宫?”
“游魂宫是南陵国目下最大的江湖神秘组织,素来与朝廷作对。当日行刺公主者,正是游魂宫所派遣的死士,少侠侠义心肠,仗义援手相救公主于危难,纵然你不答应屈居公主府,游魂宫也已把你当成了公主的人。”秋苋翁转身指了指地上的尸身,“此二人便是游魂宫五大杀手之一的黑白双魂。”
“哦?”
残风轻轻蹙眉,看来果然惹上了大麻烦了。
“谁得罪了游魂宫,便好比被冤鬼缠上了身,游魂宫是决计不会再让少侠安宁的,如若少侠想在今后依然过着自由逍遥的日子,除非与公主合作,一同剿灭游魂宫。”
残风轻轻苦笑一声,“这算是变相的威胁吗?”
秋苋翁摇了摇头,“当然不是,互惠互利而已。”
迦延回到宫中,绝口未提这次出宫发生的事情。
但珍河还是知道了。
“听说自报恩寺回程的途中,你与王姐遭遇了游魂宫死士的突袭?”
毫无心理准备的询问,令迦延一时怔愣。
或许是她的表情过于诧异,引得珍河一阵不忿,“如若我不问,你是否打算同王姐一直隐瞒下去?”
迦延轻轻喘了口气,才道:“国主……是从哪里听说的?”
“你和王姐都太小瞧了朕!”珍河这次是真的动了气,迦延尚是第一次看到他情绪如此激动,“多少年了,在她的眼里,朕似乎永远都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
对于此时的珍河,迦延突然感到有点陌生和一些害怕。
“王姐、王姐她对你……很好。”
她想为清河公主辩解,却有些言不成句。
珍河看了她一眼,也看出了她的惶乱,忽而长吁一声,自我调整了一下情绪,再开口时已经平稳了很多,“我知道——知道她是怕我担心。”他的表情转而变得有些低沉,“我亦知道,她在背后为我负担了很多的事,一切都是为了我。自我十二岁即位开始,她恪守先父的遗命,竭全力保我坐稳江山,她很辛苦。”
原来他都知道。迦延眼眶一热,“国主……”
“她心疼我,可知我亦心疼着她。”珍河道,“其实我并没有她想象中那么软弱,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很努力,就算是为了不辜负她的付出,我也一定要做好一个称职的君王。我只是……真的很讨厌她把我当个小孩子般照顾,什么危险都往自己身上扛,什么都瞒着我。”
“国主,我已经劝过王姐,她会为你而小心珍重,她知道你离不开她。”迦延只得如此安慰,“何况,这次我们毫发无伤,也就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了。”
珍河沉默地望着她,过了一会儿,放轻松了表情,“是啊,事情都过去了,所幸毫发无伤,想必你也受了不少惊吓,我却还在这里发莫名其妙的脾气,让你受这夹心气,实在对不起。”
他对她总是这样客气,让外人看来,真正相敬如宾,却不知他和茹佳在一起时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迦延看着他的态度,突然有些情不自禁地揣测。
“听说这次化解危机,全有赖一位青年侠士的相助,是也不是?”珍河突然有如此一问。
连这也都知道?迦延一阵难以扼制的心虚,“……是。”
“我想亲自设宴款待他。”
“……啊?”
“听说王姐已将此人收为门客了。”
什么?
迦延这下真正吃了一惊,他……他不是回绝了吗?
但深知珍河所得到的消息应该不会有错的。为什么又会答应了?难道真的逃不过清河王姐的魅力吗?
“迦延?”珍河见她失神,轻轻唤她。
她连忙回神,“嗯?”
“下月初一是本国的花火大会日,就把宴席摆在公主府好不好?”
迦延怔了一怔,才反应过来是什么宴席,“不、不必劳师动众了吧?”
她不想再见那个人了,不能够再见,她怕再见之后会管不住自己。
“要的。”珍河却坚持道,“他不仅救了王姐,还救了朕的王后,朕该当面道一声谢。”
“国主……”
“到时你也出席。”他又道。
迦延轻轻闭上了嘴,知道已成定局,如若再出言阻拦,说不定反而引起怀疑。
珍河发现,自从公主府回来以后,迦延变得有些异样,似乎总是神不守舍。或许真的被那件事给吓坏了吧。
如此一想,便觉得更为愧疚和怜惜。
他走近她的身边,伸手去摸摸她的脸,“迦延……”
迦延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
珍河的手摸了个空,有些怔愣——她以前从不曾这样。
迦延在躲闪之后亦万分后悔,为什么会突然下意识地抗拒他的亲近?
“迦延,”珍河突然正色地唤她的名字,“你……可是在怨恨我?”
一直以来他都有点自欺欺人地逃避着这个问题——从圆房至今,他没真正碰过她,可却和茹佳生了一个孩子。他一直都不曾给过她任何的解释。
虽然迦延也从未向他要求解释,但心中必定还是有很多的疑问与不甘的吧?
“有些事情,我知道是不可能不了了之的,但是……我一直都想不出该如何向你解释……”
“不要说了。”迦延突然阻止他,“我不想知道……不需要什么解释!”
她觉得,所谓的缘由,无非也就是他不爱她。虽然他亦不是她爱的人,但是,让自己的丈夫亲口告诉自己他不爱她,总是非常损伤自尊心的。她不想他亲口说出来。
可是珍河道:“不,迦延,我必须得要给你一个解释,若不然,对你太不公平了。”
“记得你曾经问过我,为什么选了你?我说因为看到你的第一感觉是似曾相识,你的神韵和我记忆中的明河一模一样——这是真的,我真的在你身上看到了明河的影子,所以才选了你做王后。因为我想让明河回来,回到哥哥的身边。
“对不起,迦延,我想我是太想念我死去的妹妹了,我一直在你的身上寻找着她的影子,渐渐地,我真的把你当成了妹妹了。圆房的那一天,我……我不敢对你产生欲念,我觉得如果我……如果我那么做……会好像在乱伦。
“我不是不爱你的,迦延,相信我,我对你所有的好并不仅仅是为了内疚,为了补偿什么,只是……只是这份爱好像有点走错了方向,变得……变得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但是我也一直都在努力,努力地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正确的位置,像爱妻子一样地爱你……我想,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就能够做得到的。”
珍河发现,当自己在一点一点向她解释的时候,迦延的眼泪已经扑簌簌地开始往下掉了。
当说到最后,她已经哭得难以自持,呜咽着半倚在了床帏之上。
迦延不像茹佳,手上扎了根刺要哭、心爱的鸟儿死了要哭、收到一件喜欢的礼物也要哭。
迦延一向都是很忍抑的。
他只见她流过一次眼泪,就是他向她讲起明河的那一次。
但也只是流了几行泪,淡淡地擦去罢了。
如今这样,可见素日里压抑得太深,全面爆发了。
他就知道,无论怎么解释,这件事对她始终都是不小的伤害。
但是,望着痛哭流涕的迦延,珍河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
觉得以前的迦延虽然不失美貌,但总是面色苍白,神情木讷,谨言微行。说好听一些是端敛沉静,其实是暮气沉沉,仿似大病缠身。
所以,无论是跟清河王姐还是和茹佳站在一起,她都看上去比别人逊色。
但此刻的迦延却很不一样,竟有说不出来的夺人光彩在身上绽放开来,让珍河发现原来木美人也是有心的,只要她有心,便能够拥有绝世的风华。
他想起明河临死时候的样子,大笑大哭之后,苍白的小脸上晕开玫瑰红的色泽,比起任何时候都更为明艳娇丽。
“迦延……”
他忍不住想去拥抱她。
可她轻轻推开了他的手。
“国主,”泪迹未干的女子含着一抹凄苦的笑意凝望他,“迦延想问你一个问题,请你如实回答。”
她的眼睛那样大,那样明媚,波光粼粼的使他意乱神迷。
“好。”他答道。
“你爱茹佳吗?”她这样问。
想起茹佳,他心头蓦然冷静下来。
茹佳啊,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他就被吸引了。
那还是选秀的时候,他至今记得她穿得很素,全然没有想象中将门千金的浓烈张扬,反而清馨雅致,像一朵小白梅。
所有秀女都敛眉修目,却唯有她滴溜溜地在看他。
琉璃色的眼睛里眼神却并不精明,而是天真得像个孩子。
哦,当时她确实还只是一个孩子,才十岁吧。
接触到他的目光之后,她居然还向他笑了一笑,是一种友好的,找到好朋友一样的笑,又带了一些些的爱娇。
他仿佛走在一片花海里,蓦然撞落了一朵小白梅,而它正正地撞在他的心怀里。
如果她不是霍骑的女儿,他必定会颁给她玉如意,封她为后。
茹佳是一个彻头彻尾真性情的女孩,想哭的时候哭,想笑的时候笑,无限信任无限景仰地唤着他“珍河哥哥”,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是轻快的。
爱茹佳吗?爱,当然是爱的。
但对于这个问题他还是在犹豫,犹豫着要不要如实地告诉迦延。
他怕实言相告会使她觉得受伤更深。
但是迎视着她的眼神,他发现她是希望听到真心话的,如果曲意隐瞒的话,说不定反会令她失望吧。
“是的,”他终于还是轻轻点了点头,“我爱茹佳的。”
听到这个回答,迦延的肩膀一松,许久都不说话,仿佛累到虚脱的样子。
“迦延……”
他忍不住还想再说一些话来安慰她。
“够了。”
她开口阻止他再说下去。
他僵住,不知她这“够了”是什么意思,她从来没有顶撞过他,但这句话的语气上又很绵软,不像是在顶撞的样子。
“够了……”她又重复了一遍,放缓了语速,很无力的样子,“只爱一个人,就足够了。”
国主,不要再花任何的心思在我身上,你和茹佳才是两情相悦,迦延从头到尾都是错误地夹在你二人之间的第三者,我已经彻底明白了。
而且,此时此刻,你不知道我多么希望可以变成真正的明河,有你这样一心一意喜爱着我的亲哥哥……
如果我是明河,在面对那个人的时候,会不会比现在好受很多?
九月初一,南陵的花火大会日。
清河公主告诉柳残风,今夜国主会亲自驾临府邸,摆上一桌谢宴。
“不仅仅是为你救了本宫的缘故,”公主道,“你还救了一个对国主来说相当重要的人。”
她卖了一个关子,故意没有确切透露那个人是谁以及到底是什么身份。
但残风立刻联想到了那个曾经在公主府外拦住他的女子。她只要求看一看他的剑,并且自称是已故世的怀怡公主。
一想到这个女子,残风的心就有些莫名其妙的慌乱。
他这个人,虽然有点怕麻烦,但自问不是一个受不起惊吓的人,更不是怕死的人。就算那个什么游魂宫真的盯上他,他也不是紧张得非得回来投靠长公主不可。
他之所以肯回来与长公主谈条件,答应助她灭游魂宫,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那个神秘的女子。
可以肯定她绝不是什么怀怡公主,那她到底是谁?为什么让他产生那样熟悉的感觉?让他觉得那样难以割舍呢?
原本可以直接问清河公主的,但不知为什么,每一次话到嘴边就有迟疑。
直至如今,谜底即将自动揭示了,他突然感到心慌意乱得恨不得逃避。
难道这就是一见钟情吗?
一个以终生浪迹为人生目标的人,也会对一个女子一见钟情吗?他能给予她什么呢?他是如此一无所有。
一个对国主来说相当重要的人——清河公主的话语中所透露的到底是什么信息?他有预感,那女子的真实身份对他来说不会是一个好的答案。
当驾临公主府的时候,迦延和珍河同坐了一辆车。
茹佳亦抱着小公主随行,但她很乖巧地退居其次,同乳母等一行人坐在了其后的车辆中。
同坐一辆车中的帝后默然不交谈。
初见时珍河倒是想逗她说些话,他说:“王后,你的脸色看上去不太好。”
是想表示一些体贴的。
但迦延没有回他的话,只是浅浅地笑了一笑。
那笑容看在珍河眼中仿佛是在说:当我知道你心中一切真正想法之后,我怎么会好?
珍河一下子不知该再说些什么了。
转头,迦延若无其事地和茹佳寒暄了几句,又逗了逗她怀中的孩子。
小公主佳闻才只五个多月,不会说话,但很会笑,不愧她的封号叫做“展颜”。
然后就各按其位地登车上路了。
珍河一路上只是望着迦延,而迦延半垂着眼眸,仿似全然不知道他在看她。
他亦猜不透她心中到底有什么想法。
越临近公主府的时候,他发现她开始流露出些许的不安,凝神,蹙眉,又频繁地绞动双手。
而她的脸色是真正不好看,焦灼倦怠的模样。
忽而,她抬眼望了望他,正巧与他的眼神碰到了,她略有慌张地又垂下目光。
“迦延,”他忍不住问,“你可是哪里不舒服?”
“没有。”她偏过头去。
他迟疑着,伸出手,盖在她的手上。
她轻轻颤了颤,但没有拒绝。她在他面前是习惯顺从的。
他将她的手握住,却发现她的手指冰凉的,满手心都是汗。
“你怎么了?”他是发自内心地关心她。
“我……我不想去赴宴了,行吗?”
她的心里对即将而来的身份揭示突然感到无比恐慌,不顾一切地说了出来。
一点也不觉得身为王后有多么尊贵,相反,自从发觉自己只是存在于珍河和茹佳之间的障碍之后,她只觉得羞耻。
以这样的身份会见哥哥、会见自小梦想要嫁的男子,她觉得羞耻。
“迦延?”珍河不知道她怎么了,她从来没有使过小性子的。
最近的迦延让他觉得有很多无法理解的细节变化,总觉得该有一个诱因,但到底什么才是那个诱因呢?仅仅为了他的坦白吗?
虽然对她的爱走错了方向,但是,他一直是在她身上很用心的。不是很用心的话,看不出那些细微的改变。
“算了,没什么了……”迦延见他疑惑的神情,又退缩了,“也许我真的哪里不舒服,我生病了,我……我头脑昏沉沉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珍河道,“你忍一会儿,我们早些退场,可好?”
他很迁就她。迦延叹了口气,“嗯。”
到达公主府的时候,华灯初上。
为了迎接他们的驾临,安排这场盛宴,公主把门楣重新装点过了,一路进去挂满了花灯,各色花灯,亮如白昼。
公主率领众门客家人在门前接驾。不只是柳残风,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参见国王与王后。
当迦延伴着她的帝王夫君在众目睽睽之下亮相,对于柳残风来说——谜底揭晓了。
一切是意料之中,一切又在意料之外。
她竟然是南陵的王后。
给他诸多微妙感觉的女子,不只是有夫之妇,竟还是一国之后。
比公主更高一层的尊贵身份,连泰昶长公主都得向她跪拜叩首。
残风随大流地跪倒在地上,只觉得自己同那女子的距离如此遥远,她似翱翔九天的彩凤一样高不可攀。
黑压压的一群人,迦延却一眼就感觉得到柳残风的目光,她的背心都渗满了汗,紧咬住了嘴唇。
为什么要这样?早知这样,情愿再也不见。
“瞧,王姐很费心呢,就看在王姐这片心上,我们也不能辜负了这个夜晚。王后,你现在可觉得好些了?”
赦了众人平身。进府的时候,珍河一路都拉着她的手走在最前面,软语温存。
看上去帝后之间的感情好得不得了。
迦延却分神记挂着走在身侧靠后一步的茹佳。
他们才是天造地设真正的一对,可为什么非得是自己与珍河并列而行?
多么虚假,真委屈了茹佳。
此刻,她恨透自己这个身份、这个地位,无比厌恶。最可怕的是,她知道自己永远也无法解脱,就算是死,也得以珍河后妃的身份入葬在孟氏的陵寝。
哥哥,自由自在的生活多么好,你为什么要答应公主,也陷入这凡俗的束缚呢?
坐定,开宴。
“王姐,告诉朕,哪一位是柳残风柳少侠?”
该来的始终要来。珍河非得坚持亲自道谢,显示自己身为国主的平易近人,显示自己的知恩,更显示自己对姐姐和王后的珍爱。
“多谢少侠救了朕的王姐和王后,这二人对朕来说都是重逾性命的。”
这句话一说出来,清河公主亦为之动容。
“国主说哪里话,让臣姐如何担当得起?臣姐性命如何可与国主相提并论?”
公主这么说着,眼眶却是已经有点热了。她相信自己的弟弟对自己这份心是绝对没有虚言夸张的。
迦延也是相信的。虽然他没有把她当成真正的妻子,但他一直都对她好,当成亲妹妹一样。
可她只是略有回避地低下了头。
那个人就站在她的眼前,那样毫无隔阂地彼此相望着,就算他不可能再认得出她,却依然让她感到不知如何自处的尴尬。
耳朵里又开始嗡嗡地灌满了风,几乎什么都听不见了。
直到珍河把一只酒杯塞到她的手里,并且关切地问:“王后,真的很不舒服吗?”
发现底下的人都在看着她,原来珍河让她一同向残风少侠敬酒,但是她表情呆滞得似泥雕木塑般全无反应,珍河轻唤她一声都没有用,直到他把酒杯放到她的手里,冷硬的银制酒器硌到她的手指,才恍然回神的样子。
但回神之后也还是神不守舍,珍河示意举杯她便举杯,珍河示意她说两句话,可是她半句也说不出来。
目光逃避着与残风的注视,眼睛里盈盈然闪着亮光,好似再逼一逼就要哭出来的模样。
连并不善于观察的茹佳都看出了王后姐姐今天的异样,精明的清河公主更是秀眉疑惑地轻颦起来。
底下众门客家臣都静悄悄地望着,恐怕心中亦难免有所腹诽。
站在迦延身后的近身侍婢与内监们则为自己主子的失态而焦急着。
唯有巧榆在看到柳残风站出来的那一刻明白了一切。
怪不得这几日看见王后都心事重重的样子,原来是因为遇到了故人。
虽然未必会想到那一层去,但她也理解迦延同残风当年的感情是如何深浓厚重的,这两个孩子是曾经共过生死的交情啊。
她本站在迦延身侧,不由轻轻伸了一只手去拍了拍她的肩。
王后,榆娘明白你的苦衷了,但请你忍耐着,一定要撑过这个场面再说啊。
“柳……少侠,”迦延终于开口了,“本宫……先干为敬。”
说完,仰首便把自己的杯中酒饮尽了。
珍河愣了愣,随即讪笑着圆场道:“王后是实在的人,心中的感激不知道如何用言语来表达,那么朕也先干为敬了。”
残风心中亦充满了困惑,但他不敢把目光长时间停留在花容月貌的王后身上,低头亦默然干掉了杯中的酒。
再次抬头的时候,眼睛向上抬了一抬,却蓦然看到了王后身边的一个有些年纪的女官。
他的表情亦开始难以掩饰地怔讶起来。
不会吧?
当年与小延分开的情景他一直历历在目,那个女官分明就是当年那好心夫人身边的婢女大娘啊。
难道王后她竟然是……
不顾一切地把目光投注在了迦延的身上,那眉那眼,分明就是啊,分明就是!
她说她叫迦延,她说对他的人和他的剑都似曾相识——怎么早一点没有想到?
迦延——小延!
“你的王后今天怎么了?”
宴后,花火大会开始,大家聚在园中欣赏着百种烟花升空的盛景。
趁着迦延和茹佳离席换衣的工夫,清河抱着小佳闻逗玩着,一边装作若无其事地随口问珍河。
“来的路上就说有些不舒服的。”珍河道。
“看上去有些奇怪。”清河道,一边向周围臣下摆出端和的笑容,过了一会儿,又道:“许是我多心了。”
到底是未婚的女子,抱不惯孩子,幸好孩子在她怀中也不哭。她把孩子交回给奶娘,看到小孩在奶娘的怀中依然好奇地望着天空闪耀的晶彩,格格笑个不住。
“这孩子倒真是喜相,精神也好,还一点不认生。”清河道。
珍河笑看了女儿一眼,道:“这才不愧是朕的展颜公主,将来,她定能像她姑妈一样,设衙开府,也做个威风凛凛贤德辅政的长公主。”
清河只笑了一笑,道:“佳闻她娘怎么还不回来?换个装时间也太长了点吧。”
“迦延也没回来呢。”珍河兴致勃勃地转头看着天空中盛放的火树银花,不以为意地道。
灯火映照下年轻帝王的侧脸是那样俊美无比,笑容是恬静明澈的,眼神像个孩子般干净,心无城府。
“王姐,听说中原有个元宵节,那一天也要挂很多花灯、放烟花,跟我们的花火大会差不多——柳少侠是中原人吧?”
“是,”清河点点头,“你想找他聊聊吗?”
“朕想问问他,咱们南陵的花火会比起中原的元宵节怎么样?”
中原是天朝大邦,南陵历代帝王心里都很仰慕中土文化。尤其还有传说南陵人的血统本出自中土,而且文字都有三分之一的汉字。
其他诸如琴棋书画、衣饰风俗、经典学术,亦有很多是源于中土的。
公主明白他的意思,便向身边一内侍道:“替本宫把柳少侠请来。”
花火会已经不像之前的晚宴那样严谨。
在园子里,除了王室人员,大家都是三三两两席地而坐,观看公主所安排的专人点放烟花。
甚或可以拿出自己上街采买的烟花,寻找空地自己燃放。
到后来,除了王室人员仍然中规中矩地坐着,其他人早都各自三两成群地放自己的焰火去了。
场面这样乱,要找个人实在也很费劲。
内侍去了很久,垂头丧气回来,“禀公主殿下,奴才找了一圈,都没找到柳少侠。”
清河倒也不很生气,只是微斥一声:“蠢奴才。”
“不过,”内侍又道,“奴才在那里看到霍贵妃了,贵妃娘娘和身边的侍婢亦在自己点焰火玩呢。”
珍河一听笑了起来,“我说怎么去了这半日还不回来,敢情是丢下朕自己玩开了。”
清河也笑了,“这霍贵妃,都做娘的人了,还是那么天真烂漫。”
珍河又问:“王后呢?看到王后没有?”
内侍一顿,“倒不曾注意王后娘娘在哪里。”
珍河倒没起什么疑心,只是自语道:“怎么她们没有在一起吗?”
清河的脸色却微微沉了一沉,但很快又笑道:“我就说嘛,王后素来稳重,不会和贵妃那样胡闹的,只不知一个人到哪里躲清静去了。”转脸又向内侍道:“去把贵妃叫回来吧,就说小公主哭起来找娘了。”
待内侍去后,珍河望了一眼身后安安静静的小佳闻,道:“干什么把她哄回来?茹佳生来喜欢热闹,自生了佳闻之后久不出宫,早憋闷坏了,难得有机会痛快玩一次。”
“堂堂一个贵妃,和那些个下人在一起混闹,身边还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男人,成何体统?”清河略为不满地看了弟弟一眼,“国主对自己的后妃都太过溺爱了,会把她们宠上天的。”
“没有那么严重,茹佳有分寸的。”珍河以为她只是针对茹佳,忙护庇着。
哪知清河心里却是在烦恼着迦延,说不出哪里不对劲,却总觉得不对劲。
很快,茹佳和她的侍婢小秧等随着公主的内侍回座。
“贵妃玩得很尽兴吧?”清河公主主动递了一方帕子过去,“瞧你满头大汗,擦擦吧。”
她此时没有露出半分的不快,在茹佳的眼里,全然是一个疼爱的长姐。
“你和王后一起去更衣的,怎么王后没和你一块儿玩耍吗?”清河又很随意地问。
茹佳一怔,看了一眼属于迦延的那个空座位,“我不知道啊,以为姐姐早回来了呢。”
清河的脸色又沉了一沉。
“迦延不爱热闹,”珍河忙道,“许是真到哪里躲清静去了。”
清河转头四下看顾着,发现迦延身边的兰喜竟然在。
“咦?你没跟着你家主子吗?”
“回公主话,”兰喜忙道,“是巧榆大娘跟着去的。”
清河当即笑了一笑,站了起来,“那本宫就亲自去找找,这黑灯瞎火的,王后娘娘对府内的地形又不算熟,别磕着碰着了,回头又让我们国主心疼。”
“王姐说什么笑话呢。”珍河被说得有些脸红了,心里却也隐约感觉到有些说不出来的异样。
迦延换了衣服以后确实躲清静去了。
心很乱,就尤其呆不得繁嚣的地方。
巧榆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却由得她任性一次,竟然没有出言劝阻,只是默默随在身后。
因为她知道,迦延想躲开的不仅仅是一个喧闹的场面,她最想躲开的是某个人——花火大会比起早先的晚宴来可自由了多,打起照面的机会也就更加的多。
此情此境,巧榆认为也唯有躲开方是上策。
迦延身份地位已经起了天差地别的变化,她在被齐府收容以前的身世与经历都属于不堪提及的禁忌,想当年,费了多大的周折才让南陵国的子民放弃计较王后的出身。
在巧榆看来,如今帝后感情非常不错,只要迦延争气点能添个王子,后位就可以稳固了,但如若她与残风相认,总难免产生些不必要的、无法预知的麻烦甚或危机。
为了迦延的前途起见,她并不愿意她去冒这样的险。
原先,以为迦延这孩子会忍不住,毕竟当年他们两个孩子的感情有目共睹是那样深。
可现在看来,她也是知道分寸的。
看她的言行举止、意态神情,分明是强忍着痛苦而不愿去相认。
这样就好,巧榆微微有些放了心。
迦延在曲院回廊间曲曲折折走着。
虽然对于公主府的地形她确实不太熟,但要找个僻静所在却并不难。只要一直向着背光处行走,灯火越暗的地方自然人也就越少。
巧榆默默跟随着,她其实多希望迦延可以把心事向她敞开来聊一聊,虽然她身份低微,没有能力为她解决什么,但多一个人听着,便也多了一个分担啊。
可惜服侍她这么些年来,巧榆知道这孩子素来是个闷葫芦,什么苦楚都只会压在心底自己扛。
这么多年,与国主的感情看上去挺不错,却总不见她有多么快乐,可她从来不找谁诉说。前两天,仿佛听到她与国主犯了口角,还听到了她的哭声。这让巧榆感到一种近乎惶恐的不安,因为从不曾见她这么失控地哭泣过,尤其还在国主的面前。
她生怕发生了什么大事,事后一直问她,可她也不愿回答。
有时候,巧榆想起来也不免有些寒心,总觉得自己掏心掏肺侍候相伴她这么多年,却还是无法获得全盘的信任。
初相识时那个热心热肠的女孩仿佛只是一个错觉,她看了那么多年的迦延,实在是个冷心冷肺的人。
但她还是忍不住要疼惜她,在心里,她早与夫人一样亦将她视如己出。
一路的默默无语,一路的心事重重。
直到走到一个幽静的湖边,湖上有座千回百转的九曲桥,直通到湖心亭子里,迦延方才停下,巧榆便也停下。
“好安静的地方。”迦延宛如喟叹般轻轻地道,“榆娘,我们坐一会儿吧,好不好?”
的确是个好地方,没有人也没有灯,湖水平平静静的,倒映着漫天绚丽的烟花,静中自有动,暗中又自有光。
沿着九曲桥走进湖心亭,巧榆望着天上如星雨一般的华彩,又望了望湖面,道:“娘娘,烟花真漂亮。”
如果能专心欣赏美丽的事物,便会发现这世上原来还是很精彩的,巧榆希望藉此可以让迦延忘却心中的烦恼。
谁知,迦延却道:“我不喜欢烟花,虽然美丽,却是最虚幻最短暂的东西。只灿烂了那么一瞬,便剩下一灰烬。”
似乎反而更深地增添了烦恼,她颦着眉,又道:“为什么这世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得到永恒呢?”
为什么这世上非得有那么多的离合与变迁呢?
回想以前与自己的亲生父母在一起时的天伦之乐,如果日子一直那样过下去,没有飞来横祸,该是多么美妙的人生?
又回想和哥哥在一起的那段艰苦却很知足的日子,如果可以一直与哥哥相依为命着不分散,她也会很快乐的。
还想起了在齐府的那三年以及初次进宫、初次遇见珍河与茹佳时的感觉。
她其实也是喜欢珍河与茹佳的,也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只是不要以如此尴尬的身份。
以前,为了能和哥哥成为恋人而盼着自己快快成长,谁知长大以后会是这样的境遇,彼此之间相见却不能相认。
“娘娘?”她的沉寂让巧榆感到有些说不出来的不安。
天上烟花忽绽忽落,明明灭灭的光线投射在迦延的脸上,她看不清楚她的表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榆娘,”迦延道,“我觉得我面前一片漆黑。”
没有未来,也没有希望,她将在那寂寞宫廷里郁闷老死。说不定,根本也活不到很老的。
“娘娘,你怎么了?”巧榆没法理解她话中的深意,只是不明白地追问着,“眼睛看不见了吗?”
“眼睛没有盲,是心盲了。”迦延幽幽然道。
眼睛瞎了,只是看不到事物,而心瞎了,却再也找不到方向。
“娘娘……”
她一直说着她听不懂的话,巧榆心里渐渐惶恐急了。
想起一些老话,说天黑夜深的时候最好不要到一些特别安静的地方,比如荒野、树林、花丛和水边,都是容易招惹不干净东西的。
“我们离开这里吧。”
这里有一片湖水,此时看起来果然透着几分诡异呢。
“榆娘,”迦延终于忍不住嘤嘤地哭了出来,“你可知道我看见了谁?你可认出那救了我和清河王姐的少年英侠到底是谁?”
巧榆这才明白,原来她还是在为这件事而纠结。
“娘娘……没有办法的,”她叹了口气,道,“现在你是娘娘,没有办法的。”
她是娘娘,可谁都不知道她一直只是枉担着一个虚名而已。什么娘娘,在国主的心里,只有霍茹佳一个娘娘。可偏偏这个身份羁住了她,让她无法飞向自己想飞去的地方。
迦延哭得极为委屈。
这时,岸边传来一声低微却清晰的叹息。
“谁?”巧榆惊咋一声。
天空中此时又爆开一朵又大又亮的花火,照亮了整个湖面,也照亮了岸边的人。
……哥哥?
迦延疾然上前几步,奔到了桥的中央。
哥哥——
他与适才宴会上一样,穿着深青色长衫,束发而戴着冠。
作为公主府的门客,穿着都是很讲究的,尤其今日面见君王,都是刻意修饰过的。
宴会上,她不敢目光与之相触,不敢肆无忌惮地打量他。
此时,定定然地望着对方,觉得他真的好英俊,比起所有道貌岸然的贵族来说都不逊色。
哥……
她泪流满面,恨不得下一秒就直扑进对方的怀抱。
但理智却令她只能硬生生止住脚步,无助而无奈地望着他哭泣。
柳残风亦缓缓走上了桥,在与她相隔五步的时候止住。
“小延……你……是不是小延?”
他只想寻求一个答案,他只想确认一下。
迦延没有回答,只是哭着,不停地哭着,泣不成声地哭着。
果真是小延啊,这样的哭声,与他梦里的一模一样呢。
“小延……”他又轻唤了一声,哽咽住。
*本文版权所有,未经“花季文化”授权,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