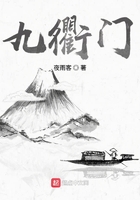转眼间半个月过去了,叶府发生了两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一件是众人听闻叶御史要纳两房据说是貌美如花的年轻妾室,另一件是叶府一个婢女在消息传出当日自尽身亡。
茶余饭后人们就爱唠唠闲话,久之街坊巷里传出好几种说法,其中最被人们认可的有两种:一种是说那婢女跟了叶御史,可是眼见他要纳妾也不给她一个名分,心里不甘,便自尽了。还有一种是说将进的两房妾室脾气不好,不知打哪听到了消息,未进门就对那婢女百般刁难,婢女受不了便自尽了。总之结果就是那婢女化为鬼魂日日游荡,人们经过坟墓周围都给她烧一沓纸钱,乞求她不要缠上自己。
这日叶琉涟正在街上闲逛,看到一茶馆有个说书的,想也逛累了便凑过去喝口茶歇歇脚。
这说书人正讲到兴头上,手里的纸扇有模有样地挥舞着:“只见漫天飞沙,那壮士也没了之前的气势,总感觉一阵阵的阴风在身后乱窜,突然!”
说到这里说书的停了一下,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引发众人不满,有拍桌子的闹:“突然什么啊,这时候喝什么茶啊,一会再喝!”
“嘿嘿,客官别急啊,且听我慢慢道来。”说书的笑了笑突然板起脸,众人因他表情骤变心里惊了一惊,又聚精会神地听了起来。
茶客压低了声音:“突然,传来一阵女子的哭声,十分的幽怨,也说不出是哪个方位传来的。壮士只觉那声音在自己身边围绕,突然想起了那位老山客的话‘那女子带着怨气下葬,死后无法升天,化为厉鬼,终日在生前住所周围游荡,专夺男子性命’顿时一阵腿软,手里的斧头乱挥。”
叶琉涟听着听着进入情境中,不自觉得紧了紧手中的杯子。
茶客继续道:“那哭声似乎被斧头割破了一般,变的喑哑起来,宛如怪兽的嘶吼。壮士斗着胆子凑上前去,只见桃树下隐约一人影,衣襟飘飞,那恐怖的嘶吼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嘀嗒,嘀嗒’不明的透明液体自壮士的头顶上滴落,壮士伸手摸去,这一摸可不得了,触碰到那透明液体的四指都不受自己控制了,难以动弹。壮士震惊下抬头,只见一绿眼怪兽张着血盆大口正蹲在树上望着他,那怪兽口中滴滴答答流下的口水,正是让他触碰后指头就不受自己控制了的透明液体!壮士吓的大叫一声,慌忙逃窜,正好撞上前面桃树下的人影,他反射性地抬头看去,只见那人没有五官,头发下一张惨白的脸,上面还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符文。这之后他便什么都不知了,等到醒来时人已经在站在闹市街头,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是场梦。然而,他发现他的手指依旧动弹不得,慌忙回到家中,闭门不出,过了两日手指才恢复自如。此后他逢人就道叶府后院有那个死去婢女的幽魂,带了鬼兽在那飘荡。”
茶客最后将“飘荡”两字拖得极长还带着颤音,众人皆眼珠瞪的大大的仿佛真的看到了那个死去的婢女和鬼兽。
叶琉涟本来听的很认真,到尾时听到叶府后院突然跳戏,然后回想之前茶客讲的的细节,越想越不对。
茶客此时已端坐在位上:“众人休当我胡说,这可是我听来的真实的事情,那壮士便是西街的屠夫。”
然听到此话叶琉涟已然憋不住笑了似的,拉着绿裳跑到街上,这才笑出声。
绿裳不解:“小姐你笑甚,我都吓死了,被那说书的讲的我都不敢再去后院后面的桃林了。”
叶琉涟继续笑,笑的快岔气了才缓了下来:“你傻啦,那说书的讲的不就是我们嘛。”
“啊?”路上反应半天突然恍然大悟,“啊!是是……”
叶琉涟使劲点了一下头:“就是那样的。”
绿裳哭笑不得。
说到这个还得从叶御史要纳妾的消息传出前日说起。
叶琉清找到了偷听他谈话的婢女,开始那婢女一直不认,后来将搜集的证据列在她面前,她就想逃跑,被叶琉涟用一手刀打晕了。由于第二日还有喜事,便暂时关在柴房,等喜礼结束再行盘问。没想到等到第二日就被安排给她送饭的人发现她吊死在柴房里了,此事追查无果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个婢女还是自小跟着叶琉涟的那个,性格懦弱,陈厨娘日日与她相处也没发觉异样,更没人发现她会轻功。当日绿裳歇息后,她扮作绿裳的模样去偷听。叶琉涟出房门时门口无人唯有树叶无风飘动,然叶琉清在房内的镜子上正好看到了那人逃走时一闪而过的模样,便误解绿裳便是那偷听之人。后来还亲自给绿裳道了歉,叶琉涟虽然没有明说,但心里也曾是怀疑过绿裳的,一度待她比较冷淡,遂也道了歉。绿裳摇头言怪她自己来的太巧了,也难为被怀疑。
叶琉涟终觉心有愧疚,见绿裳听自己箫曲时一脸的羡慕,便言教她吹可好,绿裳大喜。可是绿裳的对于乐器的天分实在是不敢恭维,为免荼毒其他人的耳朵,二人便常常在夜幕时分在叶府院后面僻静无人的桃树林里练习,那说书人说屠夫说的听到的哭声和怪兽嘶吼声正是绿裳的箫音。
那时叶琉涟正坐在树上做风筝,绿裳靠着旁边的桃树轻轻地吹着箫,声音小又怪异听的她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示意绿裳吹大点声,期间不小心把自己手边自制的简易强力沾胶碰倒了,整个撒到风筝面上,她忙把挪动风筝防止胶水沾到自己身上。刚挪开就听到树下一人大叫一声,她和绿裳皆闻声望去。
绿裳靠着桃树的方向本是顺风,一转过来,手里擎着的乐谱被风吹的扑到了她的脸上。那屠夫一看就大叫着就跑开了,等绿裳拿开脸上的乐谱问她时,她也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敢情那屠夫是把绿裳当做幽女,乐谱看成无脸符文,而她手里未成型的风筝则被看作鬼兽了啊。
回到府里,她跑去苏子衾那把这事讲给他听,苏子衾还没什么反应,她倒把自己又讲笑了。
苏子衾一脸无语地看着眼前笑的跟疯子一样的叶琉涟。
“唔,笑死我了,你说,哈哈哈,那人怎么能把风筝看成鬼兽,哇哈哈哈,哎哟,不行了不行了,笑的我肚子痛。”叶琉涟一手叉着腰一手捂着肚子,笑的前俯后仰。
苏子衾不紧不慢地浇花:“很正常,我从来就没认出你风筝做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是艺术品,抽象的艺术,不懂别乱说。叶琉涟这才勉强停下笑来纠正道。
“是是是,我不懂。”苏子衾指着桌上那一堆问,“既然你都有做艺术品的造诣了,这又是何意?”
叶琉涟干笑:“嘿嘿,我的艺术别人欣赏不了嘛,所以我还是投入大众的怀抱吧。”
“所以?”苏子衾放下花壶双手交叉叠在胸前看她。
叶琉涟立刻讨好地上前给他捏捏胳膊:“所以帮我做个风筝吧。”
“嗯哼?”苏子衾笑,“我没听错吧,曾经你可是多少次拿了你那所谓的艺术品跟我炫耀来着。”
叶琉涟没想到他还记仇呢:“哎呀,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别取笑我了,明知道我的风筝飞不起来,以前不能出门,又没外人会看见。这次可不一样,风筝节耶,我再像以前那样岂不是丢大人了。”
“没外人看见,我不算外人吗?”苏子衾听到这句话莫名心情愉悦。
“你要是外人我还有内人吗!”叶琉涟一看有戏,忙去桌上将枝条纸糊摆摆好。
苏子衾笑:“内人明明是指妻子,你居然这样滥用词语,也不怕闹了笑话。”言语间还是坐下了准备给她扎风筝。
叶琉涟也不在乎:“反正你也没少看过我笑话,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啦,这里这里,我要在这里画一只小蜜蜂,尾巴要长……”一边说着一边指给苏子衾看,苏子衾拍开她的手要按自己的扎法做,笑闹声中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而美好。
此时的皇宫却不那么平静。
“梁岂国君还真是好样的,依爱卿之意吾当如何?”御书房中,一只茶盏磕破了半边,碎片凌乱地铺在撒到地上的茶渍上。
慕太尉、苏丞相和叶御史皆跪在地上,皇帝坐在椅上,单手抵着额头看着三人。
“陛下,依我看就打,我泱泱大国还怕了他梁岂不成?”慕太尉首先发言道。
叶御史立马否决他的意见:“此举不妥,依微臣所见,梁岂国君此乃孤注一掷的做法。梁岂小国,如今南面受敌,若是能与我朝联姻,敌方自不敢妄动。若我朝拒绝,梁岂位于我国正南方位,战火一开难免殃及南方百姓,敌军若攻下梁岂,也难言不会乘兴攻打我国。”
慕太尉不满:“怕这怕那还能做什么,不管何方来人,来一万我打一万来百万我打百万。”
“慕太尉好大的口气,军队不要粮草吗,天灾刚过,粮食尚未完全恢复生产,许多百姓至今仍餐食不饱,你就要打仗,你拿什么打!”叶御史回击道。
“行了行了。”皇帝喊停二人的争执:“吾快马让人把你们请来不是听你们争论的,梁岂公主现在就在城郊了,明早即可进城,吾总不能把人拒之门外吧。”
慕太尉和叶御史沉默了下来。
“这会怎么不说话了,嗯?”皇帝气的一拍桌子,“苏爱卿,你说。”
苏丞相这才不紧不慢地回答:“原本梁岂是派使者前来,可如今使者刚走,公主就已经送了来,可见原本就是如此周划的,必是看准了我国正处于休养生息的阶段,不敢轻易与人硬碰硬。何况若真起战事,如叶御史所言,只能将百姓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皇帝道:“梁岂这是在逼吾联姻呐。”
苏丞相继续道:“想来梁岂国君也是别无他法了,如此行事倒也情有可原,不然等两国商议完毕,再将公主送来,路途遥远还不知会生何变故,而且商议结果也不一定令人满意。梁岂土地肥沃粮食充足,但是男丁少,兵力很弱,与我国正好互补。梁岂既将公主送来,为保险起见,定然会开出优厚的条件,陛下不妨等他们说出条件之后再同朝臣商议。”
皇帝道:“如卿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