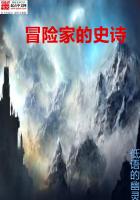九江码头,一笑酒楼。
“掌柜的,行行好……”门口出现好些瘦脱了形的脸孔,连声地哀求,“我们是从湖南来的,湘西大旱您也该听说了……求您行行好,赏口饭吃,我们全家都为您烧香拜佛……”
店小二拿了些桌上的剩饭给他们,“快去去去!别在门口挡着!我们家掌柜心肠好,也不求你们烧香拜佛的回报。”回过身来,摇了摇头,“湘西怕是旱了一整个春天,湖南的难民都到九江府来了。”
一时间,酒楼上嘈杂声渐起,都是讨论着湘西大旱一事。甚至还有人说,为了这旱情,湘西寒衣教要把傩神大祭的日子提前,为百姓求雨。
酒楼一角,青衣男子举袖遮住了面目,将杯中残酒一饮而尽,正要站起付账,门口又进来了十几个黑衣劲装的武人,个个腰间挎刀,却都神情收敛,一言不发。青衣男子桃花眼微微一抬,便又坐回椅子上,透过酒杯静静看向那边。
“江统领,”黑衣人中一位小眼睛的矮个子一坐定就四下忙活,一边为首领倒酒一边挤眉弄眼地低声道,“咱兄弟们私底下都说,您是庄主跟前的大红人,往后咱们可少不了托您照拂哪!”
姓江的身材魁梧,面色深沉,一言不发地端着酒杯,似乎并不想理他。
矮个子接着道:“也不知那姓风的小妮子什么来头,让庄主这般……弟兄们私底下都猜,她难道是——”声音又压低几许,“天涯第一剑的什么亲属?江统领,您怎么看?”
江统领面无表情地道:“我看你们私底下的讨论也未免太多了些。”
矮个子被噎了回去,当下竟没人敢说话了。就这样在寂静中用过酒饭,仅花了一盏茶工夫,这一队黑衣人便整齐有序地离开。
酒楼角落的青衣男子这才站起身来,手里掂着折扇挠了挠颈背,嘴边浅浅地笑了。
夜已深了,郁轻尘从琴边坐起,走到窗前,望了一眼窗外密密匝匝的暗林,挡住了天空中的淡月繁星。她从小就知道这扇窗是没有风景的,而且她从小就知道自己的一生只能与这扇窗相伴,直到正常或不正常的老死。这是她的命。
如果不是曾经有一个人在这片密林里那样不屈不挠地呼唤,仿佛天际一抹她从未触及过的云,她想她也不会感觉到这扇窗竟然是那么面目可憎。她深深吸一口气,仿佛又听见那个人的声音……
他叫她什么?“玉儿”?不,那不是她。玉倾城只是红尘中一具抹着金粉的骷髅,一道凝定浮光的幻影。玉倾城只是她短暂生命中唯一一次狂欢,而在这唯一一次狂欢中,她还用欺骗葬送了她自己。
姑姑已来告诉她,傩神大祭的时日提到了清明节,也就是三天之后。从古至今,从没有在清明节祭傩神的先例,但姑姑仿佛等不及了一般。等不及了要她去死。
姑姑已经向西域去信,要从罗刹王宫接回她哥哥,以备来日继承教主之位。她从来都是多余的那一个,从来都是可以随意牺牲掉的那一个。她的使命就是牺牲。
她闭上眼睛,暮春的风飒飒拂过树梢,仿佛是在她耳边温柔地呢喃:
“玉儿——玉儿——”
那么焦灼,那么卑微,那么遥不可及——
她忽然睁开了眼。
那呼唤声仍在:“玉儿——”
段平凉来了。
她眸中神光一闪,一个纵身飞出窗去。
夜色昏沉,目不见物,段平凉只能闻出她身上淡淡的茶香。并不似十二年前的浓香那般勾魂,而反有了种苍凉的绮丽。
“这一次,你总算没有躲起来不见我。”他双臂抱胸,斜倚着一棵树闲闲地立着,嘴角一撇,直入主题,“阿雪在哪里?”
郁轻尘袖中的手在轻微地颤抖,而面上依然是冷定的,“你要带她走,除非杀了我。”
段平凉睨她一眼,“你明明知道……这也不是办不到的事情。”
“我不管!”郁轻尘突然大叫一声,泪水不觉流了满脸,夜色下并看不分明,“她必须跟我一起死!”
段平凉审视地看着她,虽然只有反射着月光的泪水是真切入眼的,“谁知道你会活多久?”他慢悠悠地吐出一口气,“他们都说,好人不长命,祸——”
郁轻尘忽然冷笑了一下。在这寂静的密林中格外清晰,却又太清晰了,仿佛是梦境的返照。
“我们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么,段郎?”她说,“你死我活,是不是?”
段平凉摇了摇头,“这只是你一己执念罢了,我可不要跟你鱼死网破,我划不来的。”
“那我们做一笔交易如何?”郁轻尘的眸光终于慢慢暗了下去。
段平凉笑了,“这个我喜欢,明码标价,愿赌服输。”
“你在寒衣教乖乖住上三天,然后我自然将风离雪放了,让你带走她。”
段平凉警觉起来,“你怎会如此慷慨?”
“这几天教中有大事。”郁轻尘坦然道,“你也知道湘西大旱,有许多事务要处理,这三天,你不许扰乱生事。”
“想不到郁圣女还有这样的菩萨心肠。”段平凉笑得双眼眯成一条缝,如一条狐狸。
“成交?”
“成交。”
郁轻尘冷冷地扫他一眼,空气忽然尴尬了几分,她不知道还能再说些什么,便径自转身欲回。他却突然伸手来拉住了她——
她的呼吸都停了。
她仔细地感受着他掌心的温度,看来他已久不使刀了,虎口的茧子都快磨平了,但指间却生了厚厚的茧,想是长年以扇为刀所致。她瞬间又想到了她从他身边偷走的那八把宝刀,她还记得每一把的独特样式,还记得在那些过去的昏黄的光阴里,当他擦拭那些刀时眉眼里的宁定与温和。那个时候的他多年轻呀,才十七岁;那个时候的他多温柔呀,好像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会吃人的,是会逼得人吃人的。
仿佛只是一闪念间,她却已经恍惚想了这许多。然而他却还抓着她的手不放,明亮的双眸定定地看着她,忽然他一用力,把她抱入怀中——
她的泪水拂上了他的衣襟。她完全混乱了,只有将脸深深埋在他怀里,双手停滞了片刻,便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腰。
他的唇轻轻掠过她长发,而后轻轻吐出一口气。“玉儿,”他安静地道,“到底出什么事了?”
他感觉到怀里的人儿绵绵的带着哽咽的呼吸,但却没料到她那倔强的答复:“没事。”
她抬起脸,这时恰是月上中天,一点点清晰地照映出她的轮廓。苍白,削瘦,美艳,凉薄。她颤抖着双唇,小心翼翼地迎上前,吻了他一下。这个吻出乎他的意料,他有点呆住,忘了收回抱紧她的手。那一个刹那,两人都想起了很多很多陈旧的往事,不尽相同的往事,像月色下翩飞的落叶,渐渐地终是归于永恒的泥土。
段平凉说,本少爷一向是个信守承诺的人。
于是他真的乖乖在寒衣教住下了。
第一日,段平凉在寒衣教上上下下走动一遍,将三四百号的教众认了个七八成,称兄道弟,喝酒行令,吵嚷喧哗,热火朝天。一日过后,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位段公子乃是栖凰圣女的旧情人,圣女邀他来赏祭傩大典,也有那么些些……嗯,再续前缘的意思。
第二日,段平凉在郁轻尘的阁楼里待了一整天,正在全教上下都犯起了嘀咕的时候,段公子却摔门而出,拂袖而去,留郁圣女一个人在阁楼里低低哀泣了一整夜。
第三日,段平凉不见了。
段平凉不见了,自然是去找人了。他已打听清楚寒衣教中的三十六铁牢,他要一间一间地搜过去,如果有人告诉他他必须铲掉湘西大山的每一寸土地,他也会这么做的。
昨日,他追问郁轻尘终究无果,郁轻尘却反问了他一句:“你是不是爱上她了?”
他有一点恍惚。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他,然而却都是女人。他从来不知道如何去回答女人这样的问题。也许是因为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心,也许是因为他其实根本无心,偏偏要像有心的人那样去爱,这就是不对的,是不容于他自己的。
但是昨日,他恍惚过后,竟然说:“是的。”
他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回答过一个问题。认真得好像是面对着自己的整个人生,认真得好像……好像阿雪就在旁边看着一样。
一生,二休,三无,四禁,五疑……他一处一处铁牢闯将过去,惊起无数守卫,虽然都被他击昏了,但他也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寒衣教藏于深山,地道、密室、暗门、深洞简直无穷无尽,让段平凉头疼得要死,直将这个由女人一手操持的鬼魔教骂了一路。然而到了第二十二牢,他终于遇见了一个比魔教的所有女人加在一起还要令他头疼的人。
一个男人,一个他根本不知道应该披挂怎样表情去面对的男人。
“小子,你可算来救我了!”老七抓着铁栏,哭丧着脸贴了上去。